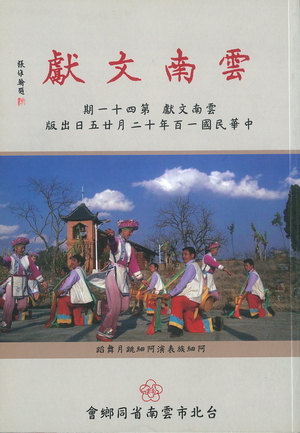世界公路奇跡的營造者──記白族道路工程專家段緯
作者/段之棟
滇緬公路從下關到畹町這一段全長548公里的路程,是滇西十個民族的二十萬築路民工在抗戰緊要關頭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次年八月,僅用短短的九個月時間趕修出來的。那麼,主持搶修這一段當年被稱為「滇緬公路西段(下段)」的總工程師、全線工程總指揮和技術上的最高決策人又是誰呢?他就是著名的道路工程專家、當時的雲南省公路總局技監(即總工程師)段緯。
段緯,宇黼堂,白族,一八八九年生於雲南省蒙化縣(今巍山縣)。段緯幼年就學私塾,勤敏好學,一九○八年由縣選送入昆明「方言學堂」(雲南最早的官辦外語學校),習英、法文,作出國留學之準備。一九一三年,段緯懷著「科學救國」的壯志,以優異成績考取公派赴德國留學,先送往青島學德語,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軍攻佔青島,段緯改入上海同濟大學(德國人創辦)繼續學業。一九一六年,德語學習結業,因當時歐戰方熾,赴德無法成行,段緯被改派赴美國留學。他先入普渡大學學土木工程。一九二○年畢業,實習一年後,一九二一年又入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科修業,學飛機製造,之後轉赴法國里昂大學進修,獲土木工程碩士學位,一九二三年再赴德國學飛機駕駛技術,兩年後畢業於老特飛行學校(這是歐洲—所著名的航校,二戰中德國空軍的飛行員大多畢業于此),出國深造近十年。一九二五年,他學成回國返滇,受聘為東陸大學(雲南大學前身)土木工程系教授,為雲南籍的第一個專職土木工程教授。翌年,唐繼堯委任段緯擔任雲南航空大隊副大隊長,後又升任隊長,同時兼任雲南航空學校校長和飛行教官,參與培訓雲南航校的第一、二期學員。他親自教學生駕駛飛機和汽車,上課或實習時,每次都和學員一起架機升空,示範或指導學生駕駛飛機。段緯是經過國外著名航校正規培訓,系「科班」出身的第一個滇籍飛行員和飛行教官,也是雲南航空事業的開拓者之一。
1927年5月唐繼堯病逝後,滇系軍閥中各實力人物為爭奪省的最高統治權又起戰端。龍雲部與胡若愚、張汝驥部曾激戰于曲靖一帶。為了削弱對方的力量,控制省城的龍雲命令段緯從昆明駕機轟炸被圍困于曲靖城內的胡、張部隊。段緯不敢違抗軍令,又不忍塗炭生靈,經再三考慮,心生一計,於起飛前就將炸彈的引信秘密拆除,當飛機飛臨曲靖上空時,為了做到萬無一失,又故意避開人口和房屋密集的縣城,而把炸彈投擲在遠離城區的荒山上,使曲靖城內的軍民避免了一次來自空中的劫難。
經過這次行動,段緯不願捲入軍閥混戰,遂向龍雲提出辭呈,要求調到公路部門去工作,其時,雲南航校第一期學員已畢業了一年,可以勝任現職工作,龍雲當時又把修築公路列為「要政」,遂准段緯所請。
一九二八年,段緯調任雲南道路工程學校校長和汽車駕駛人員訓練班的教練(一九三五年又兼任雲南縣道人員訓練班的校長),為雲南培訓出第一批公路技術人才和汽車駕駛人員,他是雲南籍的第一個專職的汽車駕駛教練。同年底,雲南全省公路總局成立,他擔任該局技監(即總工程師),成為省公路總局的最高技術負責人之一,也是雲南籍的第一代高級土木工程師。從一九二九年伊始,他主持修築我省連通內地的第一條省際公路──滇黔公路昆(明)盤(貴州盤縣)段,他親自率領技術人員測量了昆明至曲靖、踏勘了平彝(今富源)至盤縣兩段路程。這條由昆明當時的汽車東站(今海棠飯店一帶)一直修到盤縣的公路,於一九三七年四月竣工通車,與貴州方面從貴陽修至盤縣的公路相接。這一段公路受到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隨即派來考察的「京滇公路周覽團」的好評,該團的專家們認為,昆(明)盤(縣)段公路品質甚高,「除湘省外無出其右者」。自此,雲南與貴州及全國的公路正式連網通車,成為「京滇公路」(南京至昆明)的最後一段,它結束了從雲南去內地要先出國經越南、再從海路繞道香港的歷史,也擺脫了法國人控制雲南對外交通的局面。在此路修通三個月後爆發的抗日戰爭中,我國沿海城市相繼淪陷,滇越鐵路中斷,雲南與內地的交通主要靠此路連接。同時,此路劃為國道。滇黔公路連接貴陽以至戰時陪都重慶,也可經貴陽折向東南,沿黔桂公路至廣西金城江(今河池),與當時通車到那裏的湘桂鐵路相連,戰時滇緬公路進口的軍用物資,大部分經此路運往內地,它對抗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還須一提的是,滇黔公路的修通對抗日戰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它修通在前,才使抗戰初期搶通滇緬公路有了必要和可能性;若無此路,即使外援物資運抵昆明,也無法輸往內地抗日前線。在此期間,段緯還親自設計並主持修建了滇東馬過河大橋(位於馬龍縣境內,系滇黔公路滇段的關鍵工程)及民國時期雲南最長的公路石拱大橋──宜良匯東橋。匯東橋迄今已經歷了七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依然屹立在南盤江上,見證歷史的滄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段緯奉派參與了勘定滇緬鐵路西段路線,自祥雲起,經彌渡、景東、雲縣、緬寧(今臨滄)至孟定,歷時三個月,越過深山峽谷、瘴癘地區,渡過兩岸險峻的瀾滄江,為後來修築這條鐵路掌握了第一手資料。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隨著戰局的急劇變化,我國沿海港埠相繼淪陷。國民政府為打破日寇的封鎖,急需修通滇緬公路西段(從下關至畹町),以連接緬甸仰光港的國際運輸線,史稱「搶修滇緬公路」,即指西段而言。至於東段(昆明至下關),雖已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修通至下關,但路面當時只鋪設到祿豐,從祿豐到下關308公里的路程還是土路,晴通雨阻,且整段路程路基寬度不夠,尚待改善;西段548公里則全須新修。為趕修這段公路,一九三八年一月,省公路總局在保山設立「滇緬公路總工程處」,委派段緯為處長,駐保山主持這項重大工程。段緯受命於危難之際,負責指揮管理九個工程分處,擔任總工程師、全線工程總指揮和技術上的最高決策人,因此工作十分緊張、繁忙。他的任務雖然是駐保山總工程處指揮築路,但實際上大多數時間都深入到工地上。他精心籌畫,妥善部署,翻山越嶺,走遍了全路線,深入現場,具體指導,廢寢忘食,日夜操勞,從踏勘、測量到設計、施工,事事過向。指揮、指導這樣一支二十萬人的築路大軍和人數眾多的工程技術人員(其中還包括交通部派來協助工作的徐以枋、郭增望等幾位工程師),可謂艱辛備嘗!這段路程須翻越碧羅雪山、高黎貢山等六座大山,須跨越瀾滄江、怒江等五條大江,整段路程基本上是穿越有名的橫斷山系中的縱谷區,經歷世界聞名的西南大峽谷,可謂高山大河連續不斷,懸岩峭壁到處皆是,工程浩大艱巨,且氣候複雜、惡劣,怒江兩岸及其以西的許多地段,惡性瘧疾蔓延,這一帶地區,每年雨季長達六個月,經常暴雨成災,凡此種種,都給施工增加了很大的困難。
段緯主持總工程處的工作後,首先考慮到的就是如何解決跨瀾滄江和怒江兩座大橋的建橋問題。為了求得答案,他會同交通部派來雲南協助工作的工程師徐以枋、郭增望等到實地進行考察,看到兩條江的江面寬闊,水流湍急,號稱天險,要在短期內修建橋墩,建橋通車,實無此可能。經過大家分析、研討後,決定瀾滄江上的功果橋,在舊有鐵鏈橋的上游八米處,利用原橋護岸作橋臺,新建一座鋼索木面柔性吊橋;怒江上的惠通橋則利用原通行人馬的新式懸索橋加以改建,建為可通汽車的鋼索木面柔性吊橋,當時,這在全國也是一種創舉。意見統一後,由段緯當場拍板,並代表總工程處委託徐以枋負責兩橋的設計,郭增望指導施工。
在築路方面,由於施工任務緊迫,段緯決定全線鋪開,邊踏勘、邊測量、邊設計、邊施工,路基、橋涵、路面同時進展,並採取「先求通,後求好」的方針,即先開出半幅路基四至五米,然後逐步加寬。這樣,從昆明至畹町展開了一條近千里的長龍陣,蔚為壯觀。施工中,由於缺乏築路機械,民工們使用的是鋤頭、扁擔、鐵鏟、竹箕、草繩、鎯頭、鑽子、大錘、炮杆、橇棍、十字鎬、黑火藥等原始的工具,就連鋪路也是用石碾子分層滾壓,民工和工程技術人員們,幾乎是想盡了當時條件下的一切辦法,以求快速修通。
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功果橋竣工,它是雲南,也是全國的第一座可供汽車通行的鋼索木面柔性吊橋。舉行通車典禮那天,段緯專程趕來到此檢查、驗收。當時,停在岸邊等候過江的車隊駕駛員們,看著寬闊的江面,江中的急流和滾滾波濤,都十分膽怯,沒有一個人敢率先開車過江。因段緯會開汽車並且當時汽車駕駛教練,便果敢地站出來對駕駛員們說:「今天我先開一輛車過江,如果我不幸掉進江中,就算我為抗日捐軀,你們就不要過江了;如果我平安抵達對岸,你們就跟著開車過來。」說完,他征得駕駛員的同意,就鑽進一輛卡車的駕駛室,開著車緩緩駛上橋面,橋面微微有些晃動和起伏,岸邊觀看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心臟隨著車輪的滾動蹦蹦直跳,但一見車子安全駛抵對岸時,於是一輛又一輛的車子便開過了對岸,功果橋宣告正式建成通車。事後段緯對人說起此事時說:「開車過鋼索吊橋,這在全國是頭一次,其實,我當時也沒有絕對的把握,但是作為總工程師和工程總指揮,自己不身先士卒,你叫誰先過呢?言教不如身教,大不了為國獻身!修路也和打仗一樣,是要死人的。」
在築路施工期間,一是工作極其緊張繁忙,二是生活十分艱苦,段緯不搞特殊,總是和工程技術人員同甘共苦,白天奔忙於工地,一日三餐吃工地炊事員做的野炊,晚上住簡陋甚漏雨的工棚,當時他已年近5旬,且患有高血壓病,他在怒江以西的一些路段上指導工作時,又幾次染上了瘧疾,有幾次血壓高得驚人,幾乎危及生命,但都堅持就地醫治,抱病工作,不離職守,為了抗日,置個人生死於度外。
搶修這段548公里的浩大、艱巨工程,英、美專家估計至少要三年,國民政府鑒於軍事形勢的緊迫,決定限期一年修通,而以龍雲為首的雲南省政府不顧主客觀條件急於求成,加碼為限期4個月通車,這完全是脫離實際,一廂情願的主觀決定,後來雖不得已延期至六個月、七個月,這也是不可能的。這期間,一位軍界出身並兼有軍職的督工大員,竟用管理軍隊的那一套辦法來管理施工隊伍,動輒用手槍威逼各級工程負責人和技術人員,聲稱如不按省政府規定的限期完工,要按貽誤軍機「軍法從事」。段緯面對著這位大員不懂工程技術,不調查具體困難的官員,不計個人安危,多次據理反駁,指出各級工程負責人和技術人員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是真正的出力者和有功者,不僅不應受到處分和責難,而是應該受到嘉獎。一次,段緯的逆耳忠言竟然激怒了這位大員,他悍然用手槍的實彈射擊來恐嚇段緯。當時,段緯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也不肯示弱,大聲吼道:「你開槍吧!我當過航空大隊長,我也當過軍人,我為抗日就不怕死,打死了我,看你找誰來主持修路!」這位大員原來只是想恐嚇一下,用手槍和子彈來維護自己的權威,卻遇上了軟硬不吃的段緯,弄得十分尷尬,只好在眾人勸解下草草場。不僅如此,在築路期間,為了早日完工通車,段緯真正做到了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任勞任怨。面對著龍雲對逾期未完工的種種指責乃至懲罰,他仍然忘我工作,安之若素,頂日冒雨,風餐露宿,一心撲在修路上。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苦幹實幹的精神和高超的築路指揮技能,贏得了全路職工的欽佩和好評。
經過緊張的施工,一九三八年七月廿八日可以全線通車了。八月二日,段緯發電向省政府報捷。但是自然界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七、八月份正是雨量最大、最集中的日子,不幸得很,電報才發出,暴雨即至,許多地段路基坍塌,橋涵毀損,多處不通,段緯又被追究「謊報完工」。面對著通車在望的工程,段緯不計個人得失,寵辱不驚,百折不撓,迎難而上,立即率領各級工程負責人、技術人員和民工們,風裏來雨裏去,清除坍方,排險導流,減免沖刷,與暴風雨和洪水作鬥爭,奮戰了1個多月,終於在八月三十一日修復了各項水毀工程,可以通車了。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當時的《雲南日報》發表了「滇緬公路工竣通車」的報導。省政府向總工程處和各工程分處發了「嘉慰」電。至此,搶修階段基本上告一段落。
搶修滇緬公路西段的工程,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開工,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底通車,施工時間僅九個月,全賴人力,用近乎原始的工具材料和施工方法,戰勝了橫斷山系中的高山大河,新修548公里的幹道公路,改善、鋪設東段(昆明至下關)路面400餘公里,全線共鋪泥結碎石路面900多公里,僅西段就完成土方1100多萬立方米,石方110多萬立方米,修建各種橋涵2032座(道),這是雲南各族人民對抗日戰爭的重大貢獻。消息傳出後,震驚了全世界,被美國總統羅斯福、各國專家和新聞媒體視為世界公路修築史上的一大奇跡。各國新聞媒體竟相報導該路的修築情況,發表文章和圖片,其中,英國《泰晤士報》連續三天發表文章,指出:「只有中國人民才能在這樣短短的時間內做得到」。當時,有位元記者寫道:「那麼多的崇山峻嶺,那麼多的長江大河,即使是徒手遊歷,也需要幾個月的跋涉」。有的媒體認為,滇緬公路是中國大地上繼萬里長城、運河之後又一項令全世界折服的巨大工程。英、美外交官和各國記者,「國聯」專家來華考察了滇緬公路後,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向羅斯福報告說,這條公路的工程,可同巴拿馬運河媲美。著名作家、記者肖乾曾經高度評價和熱情禮贊這條公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條公路同一個民族的命運如此息息相關了。40年代,當沿海半壁河山淪陷後,敵人以為這下可掐斷我們的喉嚨。那時,滇緬公路就是我國對外聯繫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不僅僅是一條公路,它是咱們的命根子。」
滇緬公路在抗日戰爭的關鍵時刻修通,它與滇黔公路和後來修通的川滇東路、滇黔南路等幾條公路連接起來,成為當時從國外運進盟國援華軍事、經濟物資,從國內運出外貿物資的我國唯一的出海通道和國際交通運輸線,被譽為抗日戰爭的「輸血線」、「生命線」和「鋼鐵運輸線」,對抗戰貢獻極大。
鑒於段緯在主持修建這條公路中所立下的特殊功勳,國民政府交通部特授予他一枚金質獎章。
一九三九年,段緯應聘兼任敘(敘府,今四川宜賓)昆(明)鐵路顧問,並參與了該路昆(明)沾(益)段的設計工作,他對確定路線走向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次年,段緯又參加了滇越公路的修建,任工程處總工程師,並親自踏勘了該路蒙(自)河(口)段。
抗戰勝利後,段緯調任滇越鐵路滇段管理處副處長,主持修復滇越鐵路碧(色寨)河(口)段的籌畫和施工工作。這段鐵路是我方為防備日寇從越南入侵於一九四○年拆毀、破壞的。一九四六年初修復工程開始後,雖略有進展,後因內戰爆發,資金短缺,向國外訂購的鋼軌、鋼樑落空,故被迫於次年五月停工。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交通部決定滇越鐵路滇段管理處與川滇(敘昆)鐵路公司合併,組建「昆明區鐵路管理局」,統一管理雲南全省米軌鐵路,段緯任副局長,主管工務(工程技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後任代理局長。一九五一年,他奉調到省人民政府擔任顧問、參事。同年,他不顧年高體弱,親赴滇西參加了鶴慶、劍川等地震災區的抗震救災工作。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因腦溢血病逝于昆明,終年六十七歲。
段緯一生勤奮好學,精通英、法、德三國外語。在他的書架上,擺滿了各種外交專業書籍,他經常手不釋卷,直到晚年依然如此。他的國學根底深厚,並酷愛中國的民族文化,經、史、子、集皆喜涉獵,能背誦不少古詩、古詞、古文,他對一些著名的古典文學作品十分喜愛,對《西廂記》、《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聊齋志異》、《今古奇觀》等名著百讀不厭,讚不絕口。他喜練書法,寫得一手好毛筆字,還是個京戲和滇戲迷,除到劇場看戲外,還經常到清唱茶館聽戲。
生活上,他雖然飄洋過海(出國期間他乘海輪先後橫渡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3個大洋),到過東京、紐約、華盛頓、倫敦、巴黎、里昂、柏林、羅馬等世界名城,見過不少世面,但回國後從不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他衣著簡樸,除參加外事活動時西裝革履外,平時喜穿大褂(長衫)、著布鞋,家居時喜歡脫去大褂,穿中式對襟襯衣和中式長襯褲,掛懷錶。他積極參加熊慶來、繆雲台等組織的歐美同學會的各項活動,經常出席該會舉辦的「星六聚餐會」。段緯一生平易近人,從來不擺專家學者的架子。抗戰期間,駐昆的美國空軍「飛虎隊員」上街買東西、問路,因語言不通,經常發生困難,只要段緯碰上,都主動為他們充當翻譯。那個時期,段緯全家疏散在昆明西山腳下蘇家村,他休假回家時,常去鄉村茶館裏喝茶,與農民聊天,還在自家的住宅旁開了一塊菜地,有空就親自挑水澆灌,以勞動為榮。他潔身自愛,生活崇高,為了學業和事業,直到三十八歲才結婚成家。段緯一生無黨無派,為人剛直不阿,在工作和待人接物中,他嚴於律已,寬於待人,生活節儉,廉潔奉公,為同行和後輩所景仰。
段緯把畢生的精力都奉獻給我省的交通事業,足跡遍及三迤大地,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了記載他的功績,《雲南省志‧人物志》、《雲南公路史‧人物傳略》、《成都鐵路局志‧人物》、《昆明鐵路局志‧人物》等史志都為他立了傳,《雲南省志‧交通志》雖已把人物部分統一集中到《人物志》,但在相關章節也記述了他的業績和貢獻,還有《雲南辭典‧人物》中也開列了他的條目,先生如果九泉有知,定會感到欣慰。
參考文獻資料:《雲南省志‧人物志》《雲南省志‧交通志》、《雲南公路史》、《成都鐵路局志》、《昆明鐵路局志》、《雲南辭典》等。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1期;民國100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