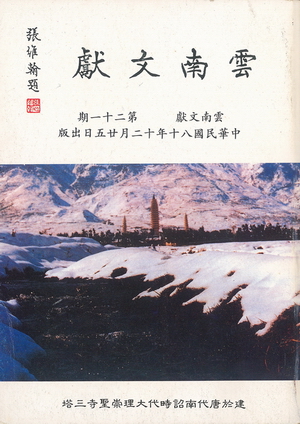另一條絲綢古道
作者/劉春明
提起中印公路,我們就會聯想到它的前身──那條悠久而古老的絲綢之路。遠在漢唐以前,我們的祖先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先後開闢了兩條主要的古代商道:一條是從長安出發到達敦煌,然後進入歐洲和西域西北絲綢之路;另一條就是從四川經雲南進入緬北到達印度而貫通整個歐亞的南方絲綢古道。然而,南方古道早於北方古道,這是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勢所決定的。漢唐以前,中國的政治中心多在黃河以南,所謂北塞南疆,這就是說,北方自然氣候惡劣,風沙冰雪險阻,且當地民族強悍,部落紛立,長期處於阻塞狀態;南方雖處於橫斷山脈的眾山峻巖之中,然因地理氣候宜人,自然資源豐富,生產條件良多,民族雖處於原始部族狀態,然習性較為純和,黃帝軍威可達,疆制較有基礎。在相對穩定的社會條件下,這裡的邊民由原始的自給性生產,逐步形成以物易物的邊民互市,這種以餘補缺的交換方式逐步促成對方缺貨的短途販運,而這種短途販運的連鎖反應,就是這條古道形成的最早的歷史因素和社會因素。
隨著歷史長河的流展,一條起於我國四川宜賓,經過雲南的大理、永平、永昌而到達騰衝,再由騰衝分南北兩線而進入緬甸、印度、阿富汗等國的商道早於西漢之前就已逐步形成。漢以後,這裡已不是原始的互市和短途販運,取而代之的是雙方的商賈從事早期的國際貿易。貨商以人肩馬馱將大宗的生絲及黃銅、石磺、水銀、朱砂、鐵鍋、銅器、錫、鉛、明礬、金、銀、絲綢、天鵝絨、酒精、果乾、紙張、扇子、衣鞋、藥材等一百多種商品由各地運往騰衝,再由騰衝衝分運至緬北的密支那、八莫一帶。一些西洋商人又將來自中國的商品轉運到仰光及加爾各答再銷往南亞及歐洲各國。貨商運入中國的商品除以棉花為大宗外(每年約一千四百萬磅),還有象牙、犀角、燕窩、鹿茸、翠玉、琥珀、紅藍寶石、名貴蛇紋石等,這些高貴商品均由印緬運入騰衝,再轉運內地。有的商品如花紗、玉石等則多在騰衝織染、加工、雕琢再轉口內外。從公元初期的鹽棉交易,到十五世紀後的絲棉貿易,騰衝始終是這條商道重要的集散地到十九世紀中期。這裡的進出口貿易額高達四十萬英磅以上,經常有上萬匹馱馬在這條古道上穿梭不息。這種貿易規模,除了少數新興海運港口之外,國內沒有一條陸路商道可以相提並論。優越的商貿條件,大大促進了騰衝工商業的發展和繁榮。這裡商號林立,加工作坊布及城鄉,從事商務的騰衝人幾乎充斥南亞各地,有的商號開始專門從事對外貿易,在許多國際市場建立商業機構,從而形成有一定實力的跨國公司。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這些以貿易起家的進出口商,又在國外大量投資,像工礦業、金融業方向拓展,成了雲南對外投資辦企業的先驅。就以騰衝的「洪盛祥」為例,這個商號以騰衝為組部,分別在國內的保山、昆明、嘉定、重慶、廣州、香港、上海和國外的仰光、曼得勒、臘戍、八莫、加爾各答、哥倫堡等遍設機構,從事大規模的跨國貿易活動。隨後又在下關投資辦「石磺有限公司」向緬甸和印度市場大量銷售石磺平均每年出口石磺一萬五千馱以上。同時還經營茶葉、製革加工傾銷國外,像這樣的大商號何此一家,諸如:「福春恆」、「永茂和」、「茂恒」、「萬通」、「廣義」等都是活躍於國際市場的大戶。同時,全國許多省也紛紛在騰衝設立會館、貨棧等商務機構,正像《騰越廳志》中所言「十八省之人雲集」而名不虛傳。
由於騰衝在這條古道上的商業地位,加之騰衝有著豐富的自然資順,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為此而垂涎三尺,他們利用各種借口,都想把自己的勢力伸向這塊寶地,先後於清末明初在這裡設立海關、稅務司、教堂、醫院,以至領事館等機構。紛繁的社會結構,給騰衝帶來了各種文化層次,這裡有商業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華僑文化、西洋文化和東方文化等等都注入這塊領地,構成騰衝極為活躍的思想基礎,以至在這裡發生了舉世聞名的「馬嘉里事件」、「甘種地戰爭」、「騰越辛亥起義」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鬥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寇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南亞地區客觀地成為了中國戰場的大後方,這條南絲綢古道便成為當時唯一的後方軍運路線。為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依靠滇西民眾,沿這條古道相繼搶修了中緬、中印公路。中緬公路由下關經保山、龍陵、潞西、畹町而到達南坎,聯通緬甸的鐵道幹線。中印公路即由保山經騰衝至緬北的密支那,聯通印度的利多,與利多鐵道溝通。因中印公路由美國史迪威將軍督修,故後人稱之為史迪威公路。這兩條軍運公路的疏通,給中國戰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大量的抗戰物資日以繼夜地由這裡運往前線,有力地打擊了日寇的侵略,迫使日寇不得不分兵南進而困死南疆,最後遭到徹底的失敗。侵略者真沒想到中國南方古道上的邊城騰衝竟是徹底埋葬他們的墳墓。
抗戰勝利以後,中緬、中印公路再度成為中國對南亞貿易的重要商道。進出口額遠遠超過人背馬馱的時代。四九年以後,由於國內外諸多因素,這條通道被整整關閉了四十多年,然而,盡管在那閉關自守的年代,兩國人民的邊民互市仍然一直保持,互通有無,相互依存。直到改革開放的春風又給這裡帶來了生機,邊境貿易額日趨擴大,兩國人民的傳統友情又在復甦,他們深深懂得閉關自守是最愚蠢的,只有打開中緬的大門,恢復中、印、緬以至整個南亞的交往,才能奮起直追,趕上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朋友!你如果對這條神秘的古道有興趣的話,我們歡迎你到這裡來觀光旅遊,這裡的天是藍的,地是綠的,山是空的,水是熱的,有雲南山茶的發祥地,也有大樹杜鵑花王的活標本,正像中國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在這條古道上寫下了萬言珍本遊記,留傳後世;也正像英國植物學家弗里士到這裡摘下一片大樹杜鵑標本,至今還保存在皇家博物館一樣珍重。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1期;民國80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