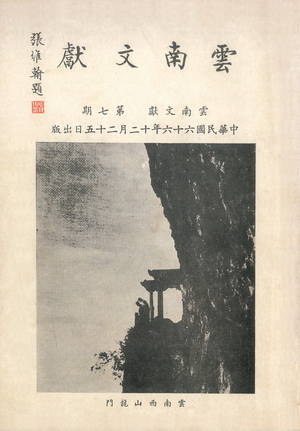鮮花獻給雲南弟兄
作者/李放南
慶璧兄惠鑒:
茲將廣東友人所寫「鮮花獻給雲南兄弟」一文獻上,作者為表對我滇人之敬愛,特托弟請兄審閱修改,若可請將此文發表於「雲南文獻」。順頌
府安
弟 雨蒼 五月廿日上
六十三年冬,在中國大陸,上演著「批林批孔」的吵耳鬧劇。廣州軍區調來了一支四十七軍湖南兵,加強警戒從廣州到香港、澳門各邊防線。投奔港澳的大陸難胞,不論跑東線,西線或中線,大多數一「起」就「跌」了,而僥倖到邊的,也被「湖南」鷹犬任意開槍殺害,情況十分嚴重。
根據形勢的發展,我們研究了全國綜合的情報,打開地圖計議:全國各省人民,在毛共猖狂血腥鎮壓下,為著生存和爭取海外反共力量的支持,都紛紛向外逃亡。尤以雲南省,地處邊疆,連接中南半島,山高林密,國界線很長,地理上是一個理想的逃亡跳板。更加為甚是,雲南人民從毛共建立統治第一天起,就開始了反毛共的自發鬪爭,從共黨的對外「通報」和對內「參考消息」透露,雲南是反毛共組織最多,隱蔽最好,給毛共打擊最大的,最突出的一省。震驚全國的是,毛酋發動文革的妖風鬼火,引導了雲南人民的反毛武裝鬪爭,雲南的「砲派」所發動的「1130戰役」「滇西挺進縱隊」更是如同驚雷一樣,給毛共致命的打擊,鼓舞了全國人民鬪爭的信心,指出了反毛共必須自力更生為主,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用革命的暴力,摧毀毛家皇朝反革命的鎮壓,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而根據毛婆江青的「國內外形勢」秘密報告,我們已經知道,雲南的反毛共組織,已和海外有了聯繫,所以,雲南在政治上也給我們提供了外逃的條件,更主要的是,若把滇粵兩省的自由戰士聯合起來,就像祖國南方的兩隻鐵拳,指向毛共封建法西斯政權,因此,大家決定把光榮又沉重的任務交給我:先去雲南「闖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給我送行的人中,有潛伏在偽廣東省公安局×處的老趙同志,他給我一套老二(軍服)的黃狗皮制服,和到昆明出差的證明,我收拾了必要的用具,就出發了。
雲南,對於我們廣東人來說:是充滿神秘感的地方,據說,三國時諸葛武侯,就在那裏七擒孟獲;美麗的西雙版納密林,更令人遐想連篇。前程一片茫茫,舉目無親,但毛共的暴行激怒了我,下定決心,一定要不負組織的委託,不負廣東同志的期望,要找到滇省反毛組織,一定要在專制暴政的黑暗中找到光明,讓滇粵兩省人民成為反毛共的一體。
我從廣州坐「曙光」花尾渡船到江門,轉坐汽車到湛江,再坐火車經廣西黎塘到柳州,然後,坐上了開往昆明的列車。車廂裏擠滿了各式各樣的人,除了少數幾個吃公糧的毛幹外,大都是襤褸衣衫的鄉下人,一張張饑黃而疲癆的臉孔,古板得毫無表情,間或傳來雲貴口音的咀咒聲,打破沉默。
列車在傍晚時,停在貴州省的安順車站。有十多個蓬頭銑足,衣衫襤襤的小鬼,像一串被綑縛的青蛙一樣,么喊著湧上車來,一前一後押著他們的是兩個猩猩一樣的老二,「青蛙」們一長串地被安置坐在車廂中間的通道上,在微弱的燈光下,看出都是十來歲到廿多歲的青少年,一張張飽經折磨而早熟的臉孔,一雙雙眼睛發射著憤滿的光。人們在水泄不通的車廂裏,透若令人窒息的悶氣,火車在黑夜中嘩拉嘩拉著向雲南境飛奔。
我在車廂中間的位置上。腳下那個被反綁著手的青年,不時用眼尾打量我,他的平頭裝頭發下面的兩隻眼睛,發出炯炯的光。他開始碰我的腳,一下,兩下,我不動聲色,他就說:
「大哥,可有煙?」操的是雲南口音。
我遞給他一支點燃了的廣州「豐收」牌,放到他的嘴角上,他不用手也能吐霧自如,我問:
「為什麼被縛?」
「他娘的!碰上一日三次大掃蕩,沒有證件在身的就抓,把老子送回原籍昆明受審,」他說時,氣憤地把香煙吐在地上。
「幹麼到安順?」我很有興趣地問。
「他們是流浪,找吃,而我……」他帶住了,望我一眼,改口問:
「同志,你是從廣東來昆明出差?」
「不!」我第一個同這樣的雲南青年接觸,決定大膽地靠攏他,我裝著撿起丟在地板上的煙頭,俯身對他輕聲說:
「為了自由!」
我發覺他驚疑的眼光過後,接著是會心的微笑。
「我要殺掉那狗教育局長,他奶奶的,『芋頭』掉進他的狗窩,炸死了他的老婆,卻被老狗跑掉了……」他悻悻地訴說:「我到安順找苗山,不妨在飯店碰上老二來查證明,……幸好他們還不知道我。」
我沉思著,從這個青年的身上,嗅出了雲南戰鬪的火藥味。
「大哥,請救我!」這低低的聲音,卻是對我完全信賴的聲音。
我瞄了一眼車廂兩頭的兩隻可惡的猩猩,正張著四隻散光眼。
「放心」我給青年以堅定的目光。
「你到昆明,去找金碧路香油巷九號×大哥,暗號五九五(吾救吾,諧音)我姓黎。」
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我用心地記著,一陣沉默。
天剛朦朧,我們坐的快車,已將抵昆明的藍窰火車站了。人們經過一夜的沉悶,開始喧嘩起來,紛紛把架上亂七八糟的行李取下來。我趁著擁擠,迅速把綁在小黎身上的繩索割斷,並把小刀和一件裝上糧票,錢的衣服塞給他。然後舉起行李袋迅速擠向車門口猩猩的身旁,阻住他們的視線。列車一到站,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小黎幾下動作,割斷了幾位難友的繩索,一個個奪窗而出,四散無踪。老二見亂,急得亂喊!「不准跑!不准跑!」但車上的旅客,卻像見到難得一見的快事一樣,有些還指點著小鬼說:「快跑!往那裏跑!」
當我隨著人流行出車站。只見那兩條氣急敗壞的黃狗皮,像兩隻毒蜘蛛捕著蒼蠅,押著兩個才只有十二、三歲沒有逃掉的獵物,荷槍實彈地一路往市內走去,路人搖著頭,深深地嘆息著。
昆明,這座全國聞名,風景宜人,四季如春的古城,這時卻濃雲密布,捲入眼帘的,是一遍血雨腥風的恐怖氣氛。東風路,正義路,南屏街等各大馬路,到處是垃圾和蒼蠅,間或有一輛門窗和坐塾俱被毀爛的公共汽車,倉徨揚塵而去。街道兩旁的牆壁上,貼滿了大字報和標語:
「血!血!血!血淚的控訴。」
「向殺害和鎮壓滇西挺進縱隊的劊子手討還血債!」
「砲兵團要平反!「八二三」一小撮是林彪死黨。」
……
每行十多步,就見一張昆明市公檢法軍管小組的殺人告示,但見:
「罪犯李其昌,男二十歲,昆明市人,查該犯收藏匕首等殺人武器,收聽外國反動電臺,散發謠言,攻擊偉大領袖毛××和江青同志,破壞批林批孔運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罪犯陸偉明,男廿八歲,保山人,捕前是保山運輸公司職工。查該犯陰謀組織偷渡外國集團,在邊境兩次為我邊防軍捕獲,思想反動,屢教不改,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罪犯周志光,男十二歲,家庭出身地主,捕前是春城小學學生,查周犯自幼思想反動,曾於一九七○年參加反動組織「兒童黨」,高叫「要吃肉」「要衣穿」「要讀書」曾被判街道管制二年。但該犯毫不悔改,更加惡毒的是於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用大頭針刺壞我偉大領袖毛××畫像的雙眼部分,並在廁所塗寫「尾大領袖萬臭無香」的反動標語,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保衛毛××革命路線,特判處周志光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
我長長地呵了一口氣,所殺十二個「政治犯」中,那些「莫須有」的罪名,那一條是該死的呢?而且都是年輕人。可見封建暴君在雲南的代理人,簡直是法西斯殺人魔鬼了,這裏血腥恐怖的政治氣氛,真是毛婆江青造下「紅色恐怖」的典型,比廣州嚴重百倍,如果說廣州市是用大字報作武器,則雲南是用血肉來作長城了。
此時此地,我完全無心瀏覽昆明的名勝風光了。走進一家像樣些的「刷羊肉」飯館子裏,希望能吃一頓好的飯菜,館子裏擠滿了人,首先排隊買飯菜牌,然後排隊領菜,再排隊領飯:館子桌找不到一張凳子,大家站著吃。我好容易買了牌子,領了一碟「青菜豬肉」放在桌子上,然後去領飯,飯領回來,菜卻不翼而飛了。我才發覺,每個桌子旁邊都守著幾個饑餓的叫化子;我才明白要是一個人在這樣的館子裏吃飯,是不可能的,何況還要顧著背包和錢包,我乾脆把飯也給饑民吃了。
我到一間賣豆漿的店裏,要買兩個麵包吃。那個姑娘看我一眼說:「沒有」,我十分委屈地說:「大姐,我來昆明大半天還未找得到吃。」
我講的是典型的粵語音的國語,這位大姐才仔細打量我,像發現了什麼連忙招呼我坐下,從廚房裏端出熱氣騰騰的豆漿和包子來。
我惱悔裏打滿密圈,一路蹣跚,找到了金碧路香油巷九號門牌,敲門無人應,門虛掩著,我便推門進去,一踏入門檻,不妨霹靂一聲,一塊大黑袋蓋將下來,跟著我被四隻有力的手抓住,把我帶了好一段路,然後,聽到一洪渾的喝聲:
「哪一路。」
「廣州。」
「幹什麼。」
「五九五找×同志。」
沉默之後,我很快被揭開布袋,眼前一遍光明,聲音洪渾的高個子迎上前,微笑握著我雙手說:「對不起,我們的環境複雜呵!廣東同志,我們盼望很久了!」
我們一見如故,首先講了在火車見著小黎的事情,然後介紹廣州的情況,和此來的目的。我說:「如果路線打通就是把我們滇粵兩股力量,從香港到中南半島聯合起來。」
「好!一定成功!」
我從談話中,才知道剛才在街上吃不到東西,是因我穿著老二服裝引起的,老×說:
「這裏的老百姓最恨穿黃狗皮衣的傢伙!」
我被熱情招呼住下,老×說:
「請休息兩天,我們送你上路。」
我住在那簡陋的房間裏,桌上擺著一大堆文件和傳單,足可以消磨我兩天的時間,在我眼前,出現了整個雲南省如火如荼的反毛抗暴鬪爭大好形勢。
「大同黨聲明:毛林江本是一丘之貉,……互相爭權,轉移鬪爭矛盾……」
「工人黨告全國人民書,毛江批孔揚秦,加強鎮壓人民,早已走上封建法西斯道路。」
怒江風雷:「游擊隊活躍在橫斷山脈,滅共懲奸,屢建奇功。」
「……燈光球場『批林批孔』大會會場爆炸,好得很!殺死共幹和黃狗皮五人,大快人心,誰還再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召開此類荒謬大會,當心腦袋開花……」
「誰騎在雲南人民頭上,誰就象閻紅顏,譚甫仁一樣的下場。……」
……
我深深佩服雲南同志的鬪爭;組織嚴密,旗幟鮮明,藝術高超,值得我們廣東同志學習。我便用暗語寫了一封信回廣州,建議速派人來取經。
第二天晚上,×大哥遞給我一份蓋有「雲南省外貿局」印鑑的證明,分咐我以外貿人員的身份到邊境,又囑咐我到芒市之後找一位詹伯,×同志說:
「自從文革以來,我們的鬪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少數頭頭變節接受招安,我們大多數的同志經受了殘酷的鎮壓,活下來的鬪爭有了新的境界,我們一位傑出的同志已經帶了一支隊伍轉戰在緬甸山區,並在中南半島札穩了根,你到了那邊,很可能會見到他們,我們的鬪爭,已不再為一己之仇,也不單是為了雲南,我們要為著全民族,全中國乃至內世界的前途而鬪爭。……」
我懷著對雲南人民的敬佩和深情厚誼,坐上奔赴前程的汽車。
當我到達昆明,萬傾晴沙一片良田,有雄偉的山,有秀麗的水,有悲壯的歌,有善良的人。真是:「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毛共統治血淚滔滔,」昆明呵!昆明,您真太美了!滇池呵!滇池,妳碧波蕩漾的湖水,真是神話中「西山睡美人」滴下的淚水嗎?還是現實人民滴下的血淚呵!你是如此扣人心弦,又使人為你痛苦地哀傷!「江山如此多嬌!」只可恨豺狼當道,魔鬼掌權,……別了!災難深重的昆明!
汽車在重山雲霧之中,盤旋了五天,經一平浪,楚雄,下關,瓦窰,保山到了芒市邊境,在一平浪,我在車上憑吊了被毛共殺害的滇西挺進縱隊的烈士英靈,在下關我看了巍峩白雲的蒼山,呵!蒼山!你是雲南人民英武雄偉的象徵,我向你表示深深的敬意!
在這邊境重鎮芒市,黃狗和便衣四出流梳。入夜,我到了團結路找到詹伯家,按暗號敲門。門開,一個十五六歲的擺夷小姑娘出來。
「找誰?」
「拜上詹伯!」
「請!」姑娘把手一擺。
我隨她穿過一塊園圃,進入草堂,一位頭髮花白兩鬢如霜的老人,正把火炭一塊一塊地夾進火盆裏,起身迎接我的是一位擺夷中年的婦人和一個小男孩。姑娘給我們擺上了香茶,老人招呼我坐下來烘火,我恭敬地說:
「×大哥分咐我拜上你老人家」。
「好!不用客氣!」
我就把自己的經過和來意講了,老人不斷點頭,我們喝著茶,拉起家常。原來詹伯在十五歲時即參加唐公繼堯領導的重建共和的護國起義,隨蔡鍔率領的第一軍入川討袁,抗戰時又參加了高黎貢山抗日戰爭,痛殺日寇,後來負傷退伍,落籍芒市。娶一擺夷女為妻,生兒育女,兒子原是保山郵電局職工,文革後被打成「反革命」跑到外邊去了,剩下孫子及兒媳一家四口生活。
老人又在盆中加上炭,沉思說:
「此去緬甸,只有一條路好走,但需要有人帶路。」
一直坐在旁邊不發一語的小娟姑娘說:
「爺爺年老,媽媽又不懂漢話,就讓我完成這個任務吧!」老人沉思良久,微笑著說:
「好!也是你應該辦事的時候了。」
翌晨,詹伯和大媽把我們送出門外,在小娟的手袋裏,放了足夠我們吃兩天的雞蛋。小娟所持的是一張表姐來探親留下的證明。
車子一直在滇緬邊境上跑,經過遮放,畹町,又走過了麗江橋。
我們在各站分別經過了鷹犬們的檢查。到了芒林,我跟著小娟下車,到了她外祖父的家。我的話語不通,只感到老少一堂,熱情洋溢於臉。
晚上,一羣青少年男女,在大青樹下圍著火盆唱起了她們擺夷的情歌。小娟唱得很好聽,她紅著臉,翻譯給我聽:
「高黎貢山呵!高又陡呀!」
「瑞麗江水呵!深又長呀!」
「奴送哥去遠方呵!奔自由呀!」
「哥為奴家呵!毋忘情呀!」
歌詞雖簡樸,但卻真摯感人。然而,我是一個負有使命的人,前路茫茫,還有多少艱苦奮鬪啊!歌聲只給我片刻的歡樂。
第二天,我跟小娟也穿上擺夷服裝。但見小娟穿上粉紅側紐短衣,下圍著天藍色沙龍,一束秀髮垂肩,翠玉似的小耳扣襯著紅潤的瓜子臉,秀眉下閃著一雙明眸,天生一副玲瓏身材,使我下意識地多瞄幾眼。我穿著十足民初時,男人唐裝衣褲,不過質料是麻布,米黃色。大搖大擺地跟在小娟後面,穿過荒涼的小徑,中午到瑞麗,我們夾著趕集的人羣,混進了瑞麗江邊的一個寨子,到了姨媽的家裏,我被強制用棉被蓋在床上,屏息著氣,只知道表姐出去了一會又回來。
半夜蒙朧,小娟拉我起來,二話不說,拖著我往外走,黑夜裏,不知高低,穿過了樹林,前面就是江邊,小娟指示方向說:
「對面就是木姐,上了岸,你只管往那個園子走去就有我們的人了。」
我向前望,在冬至前的半邊明月下,瑞麗江水金光淹映,對面是一遍黑漆似的密林。傾刻,我就要離開偉大的淪喪在魔鬼蹂躪下的祖國了,離開小娟他們,戰鬪在天南地北的同志了,我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只是用力地握緊小娟的雙手。
突然,響起了狗吠般的喊聲,「什麼人,站住!」
我們一驚!
「是黃狗,我引開他,你趕快過江,」小娟邊說,已經跑到月光下,飛也似的沿江岸跑。後面兩個邊防共軍,跑過我的面前,朝著她尾後追去,槍聲響起來了,槍聲去遠了。我發步往江裡樸,杖著從珠江裏鍛煉出來的游泳本領,很快就到了對面。正要踏過一片濘沿地,卻聽到喊聲,分明是聽不懂的老緬兵的話。跟著又是槍聲,我拼命跑,跌跌撞撞,跑到了樹林邊,後面老緬兵追來,我不敢進園裏,直往斜坡上跑,不知那裏是應跑的路,眼看成了甕中之鱉。忽然,一聲咳嗽,輕輕的中國話叫道:「不要跑」我回頭驚疑未定,一個大個子一手拉著我,閃進了樹林,也不知穿過了多少叢林,槍聲停止了,我們在一棵樹腳坐下來。
「不怕了,」大個子拉著我的肩說。
我這時才看出他,四十開外的年紀,濃眉大眼,腰上別了傢伙。
「我姓詹,兩個鐘頭前我們已經知道有一位廣東同志來了,現在就跟我走吧!」
「啊!」我激動地握著詹大哥的手,立刻想起了小娟。
「呵!不知小娟怎樣了!」
……
東方吐白,一輪朝陽噴薄而出,我深深地呼吸著異邦的空氣。我回頭一望,祖國的山河浸沉在一片白色的濃霧中,我痛切肺腑,祖國,我的母親啊!何時再回到你的懷抱!
在一座園林後面的房子裏,我握著一位負責人×××的手,熱淚盈眶,這位飽經風霜的同志說:
「滇粵人民心連心,我們戰鬪在同一條戰線上,文革時的鬪爭,只是序曲,我們要把全國各省各族人民的鬪爭聯結起來,把國內和海外的鬪爭聯結起來,為重建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新中國而奮鬪。」
不久,我就在這些朋友和同志的精心安排下,沖破老緬軍重重關卡,到了新的地方,終於會到了,日夜想念的,曾震動雲南,家喻戶曉的×××同志。
但從×××同志的熱情而不沉寂的臉上,我想到一絲納悶。
這位同志的經驗之談,語重情深,他說:「在大陸毛共如此專制兇殘,我們無所畏懼,是由於我們像魚一樣,有千千萬萬如水一樣的人民,鼓舞我們,支持我們,掩護我們,但在海外,我們不但缺『水』了,而且還要防避一些『魚』也會來吃我們。因為,多數人是不分是非,唯利是圖的,他們不理解大陸人民的真實心聲,和鬪爭精神,一些有權勢的人,甚至當了毛共的海外黨兵。而另有一些高唱『反共』調子的善男信女,卻是『阿Q正傳』裏的『偽洋鬼子』,他們連『革命』兩個字都不願聽,更不准別人革命了。他們對真正的自由戰士,動輒以大紅帽子『共特』、『赤色份子』、『大陸份子』等名堂,加以岐視,甚至殺害,總之,左的,右的,都往往成為毛共借刀殺人的幫兇,這是多麼嚴峻的現實呵!」
生活,不斷使我體會上述的真理。
今天,真正的反共鬪士是在中國大陸,而推翻毛共統治的,也只能是大陸九億人民,現在,一把推翻毛共封建社會法西斯主義暴政的革命聖火,已在祖國大陸熊熊燃燒。
為了留得「青山」在,去看祖國明天的山河,我唯有埋頭做工,用自己一技之長去謀衣食。
然而,每當自己還要分食雲南窮朋友的盤中羹的時候,就更勾起往事的回想,對於雲南人民前仆後繼,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愛憎分明的立場,耿直浮樸的作風,爽朗而溫和的性格,四海豪情的胸懷,這些優秀民氣,是永遠值得我們中華民族發揚光大的。(六六、五)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七期;民國66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