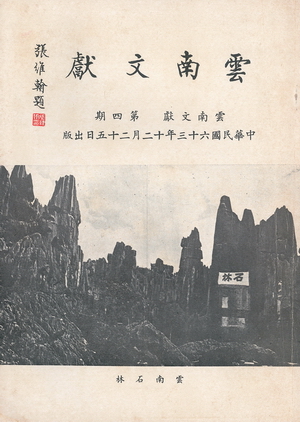雲南人的新方向
作者/林子
筆者在「雲南文獻」的「創刊號」中撰寫了「新史學觀點論中國近(現)代史中有關雲南的兩個問題;接著在第二期撰寫了「論雲南人的性格」;第三期「外省人『論』雲南」。如今卻提筆來寫「雲南人的方向」。此一系列的文章,都期望有助於雲南人的「自我分析」與「瞭解」。當然也同時期望增加別人對雲南入的瞭解。
在「論雲南人的性格」一文中,我會指出:『值得特別重視的是;明清兩代,中原與江南地區大批軍民的「南征」移民,他們便是現代雲南漢民族的主要來源。這些在中國文化下產生的標準中國人,他們轉戰或遠走千萬里。自必具備或鍛練成一種特殊的氣質與毅力,才能夠征服和開拓新的環境,他們具有北方人的豪邁(如滇西保山縣居民的口吻極似山東人)和南方人的柔和(如昆明附近「玉溪」縣的口音便似南京人)』。
這種兼具有南方與北方人性格的特點,有剛與柔,正是一種理想的性格,但多山地區以及交通的不便,卻又在雲南入的性格中可能齊生另一個問題。
因此,我在「外省人『論』雲南人」一文中又指出:『對於「雲南人」來言,仍然是以淳厚古樸的讚語為多。然而筆者在此卻想提出兩個問題,即是這種「淳厚古樸」的特性。如何來「現代化」──來適應今天這一個複雜而變動迅速的時代與社會。──性格富有彈性,不故步自封,可以接受新思想、新觀念。』
『所謂「氣度狹窄」來言。可說是任何一個多山地區居民們的共同「問題」,各自處在山巒的懷抱中,往往在潛意識中固守著『自己的獨立王國』,缺乏大力幫助別人,提拔後進的胸襟。也難以向外作大的發展和開拓。但所謂「見大量大」,可用「後天」的多讀書,多「體驗」來改變,身為雲南人者,對此實值得特別警惕。』
再進一步言:臺灣的社會,已日趨向工業化邁進。許多農業社會的思想,觀念都需要修正或改變,才能適應此一動變的時代。我在「古今談」(一○二期)和「新知識」(七四期)的「林子專欄」中,曾經以「知識份子的新方向」指出:『中國歷史上的優秀知識份子,大多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因為他們追求理想,奉獻自己,期求歷史生命的輝煌,漠視現實,蔑規權勢,為堅持信仰,可不為五斗米折腰,面對奸邪與醜惡,或是犧牲生命,或是辭官退隱,或是遨遊天下,或是讀書講學,不與汙暗的現實合流,保持其獨立和清白的人格,為人間保留正氣,為社會立下楷模。因而勿論是亂世與治世,總有一些知識份子屹立不搖,如冰雪中的梅花,為人間留下一絲芬芳。這些知識份子,其所以能保持獨立的人格,最低限度有一塊「安身立命之地」,最低能夠維持基本的生存與生活,才能夠『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所獨善自養。』
然而,時代的變更,知識份子欲求一立身隱居之地,幾乎成為了「狂想」,知識份子都不能夠在經濟上獨立,因而只能成為別人的『附庸』,在經濟生活的「困擾」中,往往影響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一切畏首畏尾,不能言,也不敢行,知識份子不能維護社會正義,「正義女神」也只得「黯然」而去。
今天中國知識份子應開創一個新的方向,保持傳統知識份子「憂天下」的理想,但「方法」上卻要突破傳統觀念。用知識與智慧來建立獨立的人格和經濟基礎。進而創辦文化、出版、大眾傳播事業,才能雊「行理想」、「爭正義」。
這些個人的見解,不僅期望供獻於中國知識份子,更特別期望供獻於雲南知識份子及全體雲南省胞。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四期;民國63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