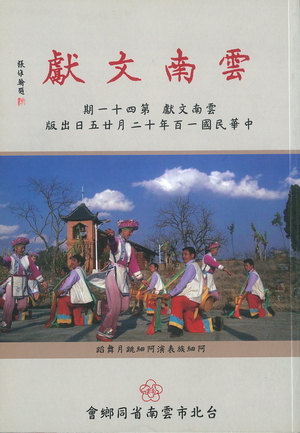滇人風範
作者/楊蓁
有人說,雲南人有點「二氣」,這是句對人負面的貶詞。
也有人說,滇人像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
大部份人認為,滇人有,「憨」氣,並認為滑千是愚,憨是雄,浮現了滇人的個性與風骨。
蔣故總統中正巡視講武堂軍官學校時,形容滇人是「敦厚篤實」,道盡了對雲南人的深入認知。
好,我們先從一般小老百姓的觀念,認知滇人的敦厚篤實的憨氣在那兒。
在過去,或者現在的鄉村,給客人狎飯,是滇人心態的一個典型;切肉時,主人會對廚子一再提醒:「伙子,肉不可以切太薄,要一指厚,可曉得,別讓客人說:小氣」。開席前,主人先夾給每位吃三片火腿肉,再「恩」(白族話喝)一大碗酒,才算開席。現在道來,不可思議,但我們是在這種氣氛中長大的。
我父親不識字,除了家教,沒有文化,他一生只講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上下左右幾個字,靠一只墨斗,蓋房子時,只有他的墨斗線一彈,木匠師父們才敢動手,他成了雲龍一帶最好的建築師;他不但養活了我們九個兄弟姐妹,而且在他家規的戒尺下,把我們都規範成中規中矩,板板札札的老實人。
同村有位大理州教育委員楊作楫,每到我們這些上新學堂的學生放假時期,把我們集中起來,免費供吃供住,但他嚴格到每人無每必須熟背一篇古文,一首詩,做不到,通知父母領回打完屁股再送來,兩年高小,三年初中,我們都在城隍廟前的山坡或田埂上高聲朗讀。夜間,在小油燈下聽他老夫子式的講解,那時,大家在他背後總是說三道四,說他吃飽了撐著,等我們入了社會,才後悔當初不能認認真真多讀點書,也才瞭解楊委員對村中年青人的那份敦厚篤實的「憨」教。
前幾天,在昆明「老土豆」惜別宴時,也講到了現代人的「滇」氣。
通海河西有位李氏婦人,被指為右派而被掃地出門,連小孩的書包也被搜走,李氏奮不顧身搶回書包,叱咤:「這是未來的國家主人,讀書不會革命,也不犯法,要老身的命可以,書包留下」。鄉人尊奉為師,由於她常對鄉人諄諄教誨,在河西一帶保持著特有的民族精神與傳統。去逝時,其子戴忠清雖貴為廳級主官,但一切依鄉中規矩入葬,該跪就跪,該叩頭就叩頭,一反現代官僚習氣,令鄉人更為尊敬。
同根一命的馮勉中告知,永勝習老有個兒子,小學畢業後,因習老氣為舊社會教育家被打入大牢,待處死刑,其子不能再讀書,也不能就業。之後,勉強得到一個「必死無疑」的工作,讓一個十四歲的習建國,從岩頂上攀繩下去,在岩石上鑿孔,裝炸藥,點火爆破,從小學會謹慎面對一切,很多同伴犧牲之後,他活了下來,最後成了一位工程師。在任內,他提出一條極其艱鉅的公路預算,省認為天價不可行而提報中央,因預算太大,中央召集了多位名師核算,結果跟他的預算等平,一個小學生二十來歲邊區工程師從此揚名。這位小哥在林業公司總經理任內,遇到公司改制為民營,萬餘員工陷于困境,生活無著,他毅然承包了一個看不見代價的昆靖高速工程段,代價是路修好後以車輛過路費作為補償,誰敢取?滇省憨者敢。收費兩年後,還為林業公司結餘了兩億多元,他被選為先進企業家,勞動模範,學院院長,副廳長。
勉中兄提到當年麗江有位何姓學者,甚得各方器重與尊敬,為此扣上了天條大罪遭處決,子彈穿胸,雖死而面帶微笑,他笑什麼?他笑「滑千者愚也」。這位使我想起八十年×一次還鄉時,想回報恩師而招同學在石門虎頭山小宴,結果只來了兩位老師,雖問而無答,事後,有同學告訴我,有七位老師在文革中遭處決,在石門河壩子裡一字排開,每人三槍而不倒地,為什麼?因為他們憨而雄,代表了文人的骨氣。
近來,共產黨人大力表揚與學習農民出身的保山人—楊善洲。且不去探究宣傳的含義為啥!楊善洲卻充分體現了雲南人的憨氣。此公退休後,拒絕住省府的幹休所,拒絕保山市委書記的禮遇,拿著退休金在涼山上搭了個小茅棚—種樹,在淒風苦雨中種植了三十年。我想他一定基於一個感恩—前人種樹;也捧著一種期許「後人乘涼」。臨終前,把整座綠油油的山,產值數十億,全數捐給了政府。
這種「憨滇之氣」,是從前人傳承下來的,看看前人。
明朝天順年間,滇人楊 昇為御史,一生「追求正義,不附權勢,不貪利祿」人謂其難。正德年間建水王 璟為御史,宦官劉 瑾為專權,大臣不敢言,他「抗疏力詆成為朝中真御史」。鄧川人楊南金弘治年間進士,授江西泰和縣令,由於高節苦行,善政惠民,擢為御史;時左都御史,挾劉 瑾威勢,淩辱十三道,獨楊南金見而不跪,左都欲縛之,南金解冠服曰:「不做此官便了,豈可屈于權奸」,滿堂失色,掛冠而去;民眾贊他「三不動」,刁詐脅不動,財利惑不動,權豪撼不動。
大理國因段氏不振,相國高升泰被民委以攝國事,臨終前得知段氏有後隱于保山,囑其子高泰明迎回段正淳,讓國歸位,成為佳話。高氏子孫高奣映,清代數次從土同知擢升為官,但不求聞達,中年即辭官往姚安結璘山,專事著作與對下一代的教育,真可謂「薪火傳承」。
清末有位嵩明的老項生王正南,此翁儒學深厚,滿腹經倫,他以「誘掖後進」,傾注于後生的培養教育,有天發現學生中有位小趙 伸,才華出眾,拒絕其再來聽課,並催促他家人,速送趙 伸去省理深造。後來趙 伸留學子日本,投身革命,建立民國,但因拒絕直系軍閥曹 錕的賄選,憤而辭官回到老家,當起水利局局長,專治雲南水忠。有次在宴會上,看劉老師王正南,手拿一根長煙桿,主人趙 伸,恭恭敬敬地彎腰低頭為老師點煙,這就是不忘本,尊師重道的雲南人。
雲南重九起義到討袁護國,滇軍中很多將領及革命志士,可歌可泣,犧牲奉獻,無私無我的精神,現在讀來。感嘆萬千。
外地人怎麼看雲南人,清人余慶遠說:「天地異而人異,人異而物亦異」,他認為雲南的地理環境和民族文化,塑造了雲南人的性格和精神。清人吳大勛更贊揚雲南人說:「滇中民風淳樸,不尚浮華,士人尤敦龐純,實無子矜佻達之習,其中琢磨成器者,類皆貞正自守,剛直不撓,而又不作矯激怪遷之行以炫耀于世!鳴呼!士習如滇者,庶幾首四民而無愧者歟」!這個評論是極高而準確的。
有人說,雲南人很傳統,是的,在道德倫理行為與思想上,我們的確很保守,很守舊。但在另一方面,這說法不對,雲南人在儒、釋、道以及民族文化融和方面,是相當積極的,雖地處邊陲,但孕育了光輝燦爛的古滇文化、六詔、大理文化,你能說「不」嗎?
雲南人的精神,這一概念閳釋並統一表達的是李根源先生,民初,李出任陝西省長時,督軍陳樹市與其他省督軍聯合倒黎元洪,要脅李省長簽署後發通告倒黎,陳逼甚緊,李根源當面提筆直書曰:「×年×月×日督軍張樹市要求簽字倒黎,本人不從,張樹市殺之」!結果張無奈,找了一個連的兵力,把李根源押出陝西境外。之後,他在抗戰勝利三週年時,發表了「雲南人的真精神」,總結為三項:一是追求自由光明、反抗強暴的精神。二是堅毅剛強、不屈不撓的精神。三是精誠團結、奮發向上的精神。並呼籲傳承和發揚這些精神。是的,這種滇人精神與風範,就像雲南的三江併流,永不停息,更像雲南的每座山,永不撼動。
我以古滇老雲南人為榮!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1期;民國100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