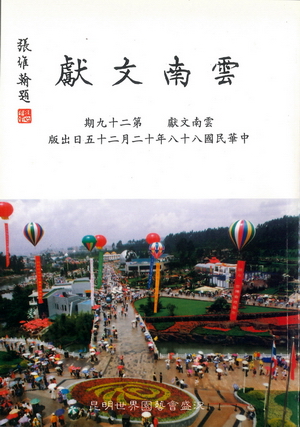雲南陸軍講武學堂(學校)的沿革和教育
作者/胡以時
清末,政治腐敗,列強交侵,民困國弱,反帝制革命風起雲湧,清政權搖搖欲墜。清廷為挽救將傾的統治,敕令全國編練「新軍」三十六個鎮(師),並先後創立一系列軍事學校,以新的武力支柱而作垂死掙扎。雲南陸軍講武堂,就是其中著名軍校之一。然而,洽與清廷願望相反,講武堂卻被辦成革命軍的搖籃,培養了一大批封建帝制的掘墓人。
一、講武堂的沿革
十九世紀末,雲南地處英殖民地緬甸、法殖民地越南間,英法帝國主義垂涎已久,累犯我主權國疆,加之雲南人民的反清革命,此起彼伏。故清廷特將第十九鎮建立於雲南,以備國防及鎮壓革命。但是,第十九鎮新建,亟需新型軍官,而原有的武備學堂、陸軍小學、陸軍速成學堂及第十九鎮隨營學堂,均規模小、師資缺、裝備差,難以培訓。故護理雲貴總督兼雲南藩台沈秉堃經奏准,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籌辦雲南陸軍講武堂。選校址於昆明翠湖畔原明朝沐國公練兵處,取「明恥教戰」之意。校址位於昆明承華圃,東隔洗馬河與翠湖相望,南對洪化橋,西至錢局街,北抵西倉坡,占地七萬餘平方米。舊址現列為國家一級文物保護單位。
宣統元年(一九○九)八月十五日,雲南陸軍講武堂正式開學。雲貴總督沈秉堃委原武備學堂總辦高爾登任總辦,李根源任監督。年末,高爾登他調,李根源繼任總辦,沈汪度任監督,張關儒任提調。李根源一改高爾登因襲武備學堂之陳規陋習,銳意改革,講武堂面目一新。增聘一批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任教。如唐繼堯、李烈鈞、羅佩金、顧品珍、庾恩賜(後改名恩暘)等。這批人在日本留學時,就已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反帝反封建革命,他們任教後,與學生朝夕相處,灌輸革命思想,發展了一批同盟會員,朱德就是以學生身份加入同盟會。
講武堂設甲、乙、丙三個班。甲班主任李伯庚,學員選調第十九鎮隊官、(連長)督隊官(副營長)、管帶(營長)中文化較高者復訓。分步、騎、炮、輜重四兵科兩個期。第一期六十六名,第二期四十九名,共一一五名。時,丙班帶隊官缺人,乃由甲班第一期調學員辛丞貴、章斐然、孫必芳等十人擔任。朱德就分在章斐然的第二隊就學。
乙班主任趙康時,學員選調巡防營中具有《功名》如監生、貢生、武舉等並經考試合格者,入堂復訓。亦分兩個期,第一期六十一名,第二期三十三名,共九十四名。全為步科。
丙班主任方聲濤,除接收武學堂、隨營學堂併入的學生二○○名外,對外招考具有中等學堂學歷且體檢合格青年,共錄取一四二名,入校後
與前者合併編為兩個隊。第一隊一八七名,第二隊一五五名,共三四二名。丙班與甲、乙班復訓軍官不同,接受的是『養成教育」即隊列兵、軍士到軍官全面而系統的教育。時方廢科舉,興「新學」,科技知識尚不普及,而科技知識又為新型軍官所不可或缺的。故丙班生需先受數、理、化、外語(英、法兩種之一),等普通課教育。考試合格後,分發至第十九鎮各部受入伍生新兵教育,期滿回堂受軍士、軍官教育。嗣後的講武學校、黃埔軍校,均沿此規,學生必先受入伍期新兵教育,但僅在校內而不下部隊,也不先受普通課教育。
為適應新軍各部下級軍官的迫切需要,學堂創辦特別班(亦稱附班),以提前分科和畢業。但因標准甚高,錄取者僅胡瑛、楊蓁等二十七名,難以編隊,遂由丙班中擇優補充為百人。朱德、朱培德、盧燾、李雁賓、金漢鼎、范石生等一批名將,就是提升入特別班的。宣統二年庚戍(一九一○)二月開班受訓。
一九一○年,甲、乙班學員畢業,回原部隊服務。翌年(一九一一),特別班學生提前畢業,分發至第十九鎮任見習官。朱德分至該鎮第三十七協(旅)蔡鍔協統(旅長)部的第七十四標(團)劉存厚營任司務長。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講武堂畢業生數百名,掌握了大量兵力,並將革命種子分播於巡防營及第十九鎮各部。為武裝起義創造了有利條件。農曆九月九日,以蔡鍔為首,以講武堂師生為核心所領導的革命軍,經一晝夜激戰,取得勝利,推翻了雲南清政府,成立了滇軍都督府。
雲南光復後,李根源、唐繼堯、羅佩金等大批講武堂教官,多調軍府任要職。都督蔡鍔委張毅、劉祖武先後任講武堂校長,撒去總辦稱號。一九一二年,蔡下令改校名為雲南陸軍講武學校。但世人迄今仍習慣地稱講武堂。
學校將甲、乙班和特別班學員生列為第一二、三期,准免回校復訓。丙班生雖參加起義戰鬥,以學業未滿,仍回校續訓,改稱甲班,送調各部軍官,經考試合格,入校復訓稱乙班,胡若愚、龍雲、盧漢等即為乙班學員。招考青年學生入校稱丙班。乙、丙丙班學員生共一八○名,畢業後,甲班生列為第四期,乙、丙兩班生均列為第五期。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蔡鍔調京,唐繼堯繼任都督,曾短期自兼校長,旋委張子貞、韓鳳樓先後繼任。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張、韓他調,改委顧品珍為校長,唐繼堯一貫主張:「非練兵不足以禦外,非練將不足以強兵」。對講武學校的教育建設十分重視,故聘任一批後來均成為名將的軍事人才任教。如軍事學家楊杰,靖國第一軍軍長趙復祥等。教育訓練水準日趨提高,此階段可謂講武學校的發展期。
顧品珍任內,培訓學員四個期(未招學生),因滇重九起義後,組軍援川、黔、藏,擴軍甚速,不少行伍出身軍官,需受正規軍事教育,始可勝任建軍需要,故將一批有戰功而無學籍的軍官,選考入校復訓,稱為將校隊(第一屆),共辦兩期。一期學員一一九名(如一九二六年任學校將校隊(第二屆)中將總隊附的陳維庚,就是滇軍援黔時,曾任貴州軍警局諜查科科長的)。該期畢業後,列為第六期;二期學員一三○名,畢業後列為第七期。另調選雲南陸軍測量局學員一五○名復訓,畢業後列為第八期,省警察局選送學員五十名入校,畢業後列為第九期。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袁世凱竊國稱帝,滇首舉義旗,組護國軍出師討伐,為利作戰,唐繼堯將不少講武學校管教官員如顧品珍、趙復祥等調往護國軍任高級將校,調升生徒隊(學生隊)隊長吳和宣繼任校長,為補充前線下級軍官之亟需,學校擴大了招生範圍,且僅強化培訓半年即提前畢業,奔赴前線參戰,計畢業了三個隊共計一一九名,列為第十期。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鄭開文繼吳和宣任校長,戴作楫任教育長,主辦第十一期,一九一八年結業。各兵科畢業生二一六名,期間,唐繼堯為提高滇軍素質,學習軍事強國經驗,派唐繼虞赴日本考察軍事。
一九一九年初,唐繼虞考察歸國,接任校長,根據考察心得,結合滇軍及學校實際,對教育、訓練、管理和設備,均有很大改進,減少兼職教官,增加大批學有所長的專職教官,一時人才蒼萃,號稱得人。當時,愛國華僑為學校捐獻大量經費,得以改建和擴建校舍,並引進更新武器及裝備。更因護國、護法諸役,講武師生戰績輝煌,學校聲譽日隆,名聲遠揚,使鄰省鄰國不少愛國青年和華僑生紛紛來報考求學。據不完全統計,從第十一期至第十七期,朝鮮、越南來留學的青年達二○○餘名。(實際遠超此數,因朝鮮生懼日本統治者迫害,多改用中國姓名)。朝鮮崔庸鍵大將,即為第十七期畢業,越南武元甲大將亦畢業於講武學校,華僑學生葉劍英為第十二期畢業。
唐繼虞校長主持校務共三期,第十二期畢業生一四一名,第十三期二四五名,第十四期三七五名。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顧品珍舉兵反唐繼堯,唐流亡香港,唐繼虞亦辭校長職,顧以省長兼滇軍總司令執滇政,任學校前教育長戢翼翹代校長,主辦第十五期。翌年(一九二二),唐繼堯由廣西反攻,顧品珍戰歿,唐重執滇政,改委韓建鐸任校長,續辦第十五期,雖政變而學校教學不綴,培訓學生三八一名。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劉國棟接任校長,主持第十六至第十八期,以王柏齡任教育長,胡昭功任學生監。第十六期畢業生三五二名,第十七畢業生二四四名。第十八期時,改委劉對揚為教育長,外語課除英、法文外,增設日文。畢業生三一四名,一度因受政變影響的學校,聲名重振,故回川靖國軍但怒剛、石青陽兩師長,委托在昆明代辦軍官速成班兩期,講武學校為川軍培訓軍官四○○名。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唐繼堯為培養高級將校及參謀,在講武學校內創立雲南陸軍高等軍事學校,以之抗衡北洋系所控制的,全國唯一的陸軍大學。其學制、教育均仿照中、日陸軍大學。任劉國棟兼校長,蔣政泉、戴作楫先後任教育長,聘早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及陸大、講武前期畢業生任教,並聘日本陸軍上校苫米地四樓(別號北洲)主授高等兵學、兵棋、參謀旅行等課目,日本陸軍中校鈴木兵一郎主授兵器學、築城及交通學,該員又曾兼講武學校劈刺教官,學員則「擇其曾著勞勛,志趣向上者,入校肆業(唐繼堯《同學錄》語)。共辦兩期,於一九二四年因故結束。先後培訓學員六十五名。
唐繼堯認為:培養高級將校及參謀,為建設滇軍不可或缺的大事,故高等軍事學校停辦後,於一九二五年,又在講武學校內創設雲南陸軍將校隊,自兼總隊長,委胡瑛為總隊附。後因唐擴充『建國聯軍』,調胡瑛任佽飛軍第四軍軍長兼雲南憲兵司令,改任陳維庚為總隊附。後又因滇西羅樹昌叛變,巨匪張良為患,陳維庚被調任滇西剿匪總司令,組隊征剿。乃任將校隊精神教育中將教官李雁賓為總隊附。劉國棟任中將戰術教官。至一九二七年該隊因雲南政變而停辦為止,共培訓十個區隊,畢業學員八○五名。
在辦將校隊的同時,唐繼堯又在講武學校內,建立預科入伍生隊。委高向春為主任,陶汝賓為大隊附,文俊逸為學生監,設四個區隊,招生二○七名。錄取標准甚高,擬畢業後直接考升入將校隊。但亦因政變而停辦。學生全部併入講武學校第十八期。
自第十一期至第十八期,學校的規模、建設逐步擴大;教育、軍訓日趨系統化、正規化;裝備、武器相對現代化,學員生素質和學績有很大提高。前期畢業生中名將輩出,戰功輝煌的將級軍官大有人在。學校又先後在貴陽、瀘州、韶州(關)、廣州、徐州等地設立過分校,創國內軍事學校在省外設立分校的先河,國內外青年爭相來報考,聲譽和影響之大,可謂講武學校的鼎盛期。
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唐繼堯部下胡若愚、龍雲、張汝驥、李選廷四個軍長兼各地區鎮守使發動反唐繼堯政變,唐失權,五月二十三日憤懣病歿。胡、龍輪任省主席。胡若愚自兼校長,主持第十九期,六月十四日,四軍長內訌,胡、張、李三軍聯合攻龍雲,龍被囚。七月,胡瑛在滇西重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擊潰胡、張、李三軍,胡瑛兼代省主席,龍雲被釋後,胡將軍政兩權交龍,龍以省主席兼校長。後因滇省內戰不息,龍無暇兼顧校務,乃於翌年委吳和宣繼任校長,戴作楫任教育長。第十九期雖三易校長,而學校教育運行如故,學生五八九名,於一九二九年畢業。
到擬招考第二十期時,國民政府下令各省、各軍不得自辦軍校。雲南以實際需要,組辦軍官團,時值中原大戰(蔣、馮、閻大戰)爆發,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響應馮玉祥、閻錫山反蔣介石。蔣為避免兩線作戰,任命龍雲為討逆軍第十三路總指揮,出兵攻廣西,龍藉此正式將雲南陸軍軍官區改稱為國民革命第十三路軍軍官團。委那其仁任團長,王炳章、華封治二人任團附。管教官員均為原講武學校班子,為培養軍民兩用人才,特設養殖、路工(公路建設)等項課程。全團培訓學員生四○○餘名,後因軍官考升陸軍大學,必具正規軍校畢業資格,經呈准該團被列為講武學校第十九期。
一九三○年,以盧漢為前敵總指揮的第十三路軍敗北,開至羅里整編。番號也改為討逆軍第十路軍,為整編羅里編余軍官並招訓新生,以充實滇軍,龍雲成立討逆軍第十路軍教導團,龍自兼團長,高蔭槐、唐繼鏻同任副團長,董鴻勛任教授部主任,王秉章任訓練部主任。除步、騎、砲、工四兵科外,增設憲兵、經理、交通三個區隊,以培養專業軍官。第一期學員生一一二○名,於一九三一年畢業。該期又設軍士大隊兩個,培訓軍士二九五名,該期團訓是「忠勇誠樸」。
第二期副團長高蔭槐、周宗濂,改教授部為教授處,處長葉成森,訓練處長王秉章,新設學生監督,以李文漢任之。憲兵、經理、交通三專業科停辦。於一九三二年六月結業,畢業生六六○名,該期團訓「公忠仁勇」。
第三期高、周兩副團長均他調,重以唐繼鏻為副團長,帥崇興任教育長兼工兵科長,楊遠新任總隊長兼步兵科主任,繆嘉琦任教授部主任,趙士俊任砲科主任。增設國際法及講授「三民主義」的「黨義」課目。並調黃埔軍校第八期畢業生龍澤匯、朱家璧、費炳等十餘名任教。一九三四年底結業,畢業生五一一名,受訓期間選拔學生二十八名,保送入雲南航空學校深造學飛行。第三期團訓「智信勤嚴」。為使各期畢業軍官具備報考陸軍大學資格,後經呈准,教導團第一二、三期,被列為講武學校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期。從而結束了雲南陸軍講武學校。
自宣統元年《一九○九》講武堂創校時,《雲南陸軍講武堂改訂章程》明文規定:「……不再續招(十九)鎮陸軍軍官及巡防營軍官為甲、乙班學員,丙班學生普通學課,(應)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六月期滿,回校再授軍事學,預定宣統四年(一九一二)十二月畢業,以學員階級發(十九)鎮後差,講武堂即行停辦,不再續辦。」然而宣統三年清朝就被推翻,講武堂(學校)卻由只准辦三年而辦了二十六年,由四個期(含特別班)卻辦了二十二期。
二、講武學校的教育
講武堂的創辦伊始,就制定了《章程》。施行後,又根據得失,總結經驗,增刪訂出《雲南陸軍講武堂改訂章程》。學堂更名為講武學校後,經增補修訂,則更臻完備,遂成為「軍令」,有法可循,依法治校。各級管教官員、學員生必須嚴格遵守。
《章程》規定:「總辦(校長)必須對訓育之得失,軍風紀之馳張,經理(財務、後勤)及內務之良否,均以身任其責」。對監督、提調、各兵科科長及教官,均有明細具體的職責規定。要求他們「奉公守法,自為模範,力任其責」。施行「精選良師以從教,給予高薪以養廉」的方針。教官皆一時俊杰,後不少人成為名將。薪俸是教官月薪一○○兩紋銀,科長以上高達一二○兩。故官員均能以身作則,身體力行,而無貪污腐化行為在他們嚴以律己,言傳身教的教育和影響下,學生受到嚴格教育,故畢業生中,可謂人才濟濟,名將輩出。
學校除復訓軍官外,學制訂為三年,入學生必具高中畢業資格,入校後兼習文、理、外語各科,與美國西點、日本士官、法國聖希爾等軍校相同。故應列為大專級學院,而高等軍事學校與第二屆將校隊,則名符其實的應是陸軍大學。
㈠軍事教育
講武學校實行從列兵、軍士到軍官的階段系統教育,在分兵科前,均為步兵教育。被稱為四大教程的《戰術》、《筑城》、《兵器》、《地形》及三小教程《步兵操典》、《射擊教程》、《陣中勤務令》各科均學。分科(稱升學)後,則專攻本課操典及相關課目,從而將學生培養成一專多能的軍官,甚至輜重兵均能獨立作戰。例如護國戰爭中的敘瀘戰役時,工兵連長胡岳奉命率工兵增援田鐘谷部死守在龍頭山,該連抗擊數倍頑敵,全連壯烈犧牲而陣地巍然不動,未失守土。戰後打掃戰場發現,全部死傷官兵之著裝包括「風紀扣」(領扣)、綁腿、彈帶等,全如平時操場訓練一樣,完全合規定,這種臨危不懼不亂的表現,充分說明官兵素質之高,訓練之嚴。講武學校的軍訓,強調從實戰出發,理論緊密聯系實際,課堂學理論;操場演實戰,故有「三操兩講武」之諺。時譽滇軍為「強兵強將,能征慣戰」。究其實,滇軍之強兵,來自強將的嚴格訓練;強將來自講武學校的嚴格教育。
㈡精神教育
講武堂創校之日,即反清革命醞釀之時,從總辦李根源到各級官員,絕大多數是同盟會員,他們不斷向學員生灌輸革命道理,揭櫫「明恥教戰」、「智、信、仁、勇、嚴」、「還我河山」等精神,各期所提訓示雖有不同,而愛國主義的精神則始終如一。「推翻帝制,打倒列強,富國強兵」,成為了學員生的奮鬥目標和誓言。
軍歌教唱,為講武精神教育重要內容之一。拿破倫曾謂:「一曲《馬賽歌》(現為法國國歌),可抵十萬毛瑟槍。」法國人民高唱著《馬賽歌》攻破巴士底監獄,推翻了波旁王朝,可見軍歌對鼓舞士氣之重要,講武堂從開始就重視軍歌教唱,李根源的《雲南陸軍講武堂軍歌》(即校歌),詞是:「風潮滾滾,感覺那黃獅一夢醒(拿破倫稱中國為睡獅),同胞四萬萬,互相奮起作長城,神州大陸奇男子,攜手去從軍,但憑著團結力旋轉新乾坤,哪怕它歐風美雨來勢凶狠,練鐵肩,擔重任,壯哉中國民!正當中!」。其二:「中華男兒,要憑那雙手撐蒼穹,睡獅昨天,醒獅今日,一夫振臂萬夫雄,長江大河,翹首昆侖,風虎雲龍,泱泱大國取多宏,黃帝之裔,天驕子,紅日中國民!正當中!」。在每天升降軍旗、開會、校閱時,全體員生均齊聲高唱。使「練鐵肩,擔重任,旋轉新乾坤」的講武精神,永銘學員生心中。中法之戰,中國取得軍事勝利,清廷卻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條約》,滇人李燮義譜寫了《雲南大紀念》一歌,頌揚滇軍將領楊玉科率領滇軍英勇戰鬥,擊斃法軍統領孤拔,取得勝利,最後壯烈犧牲。詞中有「……滇軍真勇絕,班師詔,真痛惜,到而今,金馬碧雞己非昔(金馬、碧雞兩坊為雲南象徵),……鎮南關(今廣西友誼關)為國血流紅,名譽戰死雄,招國魂,誰作主,法路已修通(滇越鐵路),鐵血外,無主義,竟生存,人人當學武愍公(楊玉科謐封號)。」在歌唱的同時,培養了學員生不惜「為國血流紅」的壯志和決心。
雲南人民抗議法帝國主義強修滇越鐵路時,學校教唱《雲南男兒》一歌。詞是:「勉哉雲南男兒,汽笛一聲,金碧變色,大好河山誰是主?倒挽狂瀾,中流砥柱,好男兒,磨礪以須,興亡責,共相負。」(第二段略),在滇越鐵路舉行通車典禮之時;「汽笛一聲,金碧變色」之際,李根源總辦,帶領學生,不顧禁令,到車站高唱《雲南男兒》,高呼愛國口號以抗議,使法侵略者為之震驚變色。上兩首歌及《打倒列強》一首,時譽為「滇人豪歌」。此外如以岳飛詞《滿江紅》譜寫的愛國等歌曲,學員生經常歌唱,響徹校園。特別是學員生隊列經過市區時,沿街軍歌嘹亮,步伐整齊,軍威雄壯,不但培養了學員生作為愛國軍人的壯志豪情,也激發了市民的愛國思想。
講武堂(學校)精神教育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軍紀嚴格。「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成為每一學員生的座右銘。凡「應、對、進、退」均必合規炬,內務、著裝、軍容一絲不苟,要求對百姓和善禮貌,嚴禁驚擾,公買公賣。因而護國戰爭時期,滇軍到處,人民自動作響導,抬擔架,壺食簞漿以迎。人民的擁護愛戴,是護國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也是講武精神教育的結果。『……護國戰爭使滇軍享譽中外,甚至到一九二一年還有一位法國觀察家在《香港時報》評譽說:「他見過的中國軍隊中,滇軍戰鬥力最強,特別是滇軍軍官要比廣西廣東的顯然要高明得多。……滇軍素質上優越的原因,是軍官們在講武學校受過嚴格的訓練,他們在學校學習炮術、識圖、認真進行夜間演習,……。」(載《香港時報》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版)。這就是外國人對講武學校教育客觀的評價。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9期;民國88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