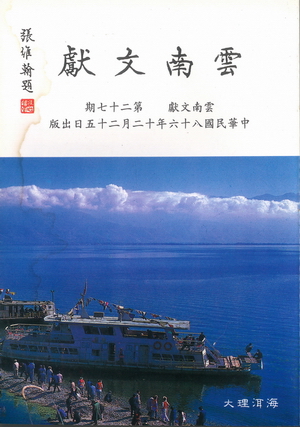「卡細先瑪麻」族屬探析
──歷史上曾活躍在西雙版納的一個族群
作者/朱德普
傣語「卡細先瑪麻」,又名「卡三西雙歡瑪麻」,它們自五十年代以來出現在西雙版納多個猛的社會歷史調查報告中,前者,多譯為「四十萬馬鞍的部落(或民族)」,後者僅出現景訥(景糯)報告中(1),譯為「三十二個馬鞍子的部落」,頗費解。八十年代,筆者返回西雙版納考察傣族神靈崇拜,時而又觸及到「卡細先瑪麻」,在猛龍有的老人或巫師對「細先」還解釋為是「四個首領」,並非「四十萬」。那麼,「四個首領」為誰?還有那景訥「三十二個馬鞍子的部落」又在何處?所有這些,對答不一,令人迷惘。宜到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至二十五日,在猛養、景洪兩地,筆者先後和未曾親政的猛養末代士司召孟教,猛養士司後裔現為州體委退休幹部的刀學良,以及原為猛養頭人現任省政協委員刀正樂等諸位先生求教「卡細先瑪麻」底蘊時,才得解多年留在學界的謎底。他們都不約而同對我相告:「桑西雙歡」就是「卡細先瑪麻」。並認為「卡」是歷史上傣族對山區民族的貶稱;如果譯「細先」為「四個首領」,難免有附會之嫌;有人將「細先」譯為「四千」則更欠妥,還是譯「四十萬」較貼切。「細先瑪麻」就是「四十萬馬鞍」,但並非確數,只是個概數,言其人馬眾多的一個族群罷了。若言其為部落則並非一個,應當是說「桑西雙歡」才確切。傣語「桑西雙」是「三十二」,「歡」就是部落。「卡細先瑪麻」族群曾擁有過三十二個部落即「桑西雙歡」傳說,頗有幾分神秘色彩,有些問題一時還難以解釋,難免存訛,但決不能一概視為是無稽之談。因為傳說中的三十二個部落,至今還有若干遺跡可尋,仍不失為是探討西雙版納古代傣族和土著「卡細先瑪麻」族群關係史的珍貴資料。故而試作此文,意在探析「卡細先瑪麻」族屬,以明究竟。
一、「桑西雙歡」盛衰的傳說
傳說古時候西雙版納的猛養、景訥(整糯)一帶,有一個強大的土著族群,稱之為「卡細先瑪麻」。他們善於騎馬,長於騎射,強悍善戰,首領名召法細達(傣語,即「四眼天王」)。傳說他頭前頭後各有一雙眼,因此英勇過人,本領高強。召法細達的部屬中有不少勇猛的戰將,如召補溫、召補哇、召法龍那哼、召法龍那達、召龍景啊、召龍景很等。也有傳說上述六位戰將和召法細達是七弟兄,召法細達為長兄。他們共同建立了以歡滿為中心的「桑西雙歡」,即三十二個部落,如後:
1.歡滿,又譯為「昆滿」是召法細達統帥之地,是「桑西雙歡」的政治軍事中心,現屬景洪市猛養鄉西北的大河邊村,與景訥鄉相鄰,寨居森林保護區,全寨均為布朗族,僅七戶,四十五人(2)。相傳召法細達曾在此建街市,在長約二○○米的「街」兩旁置有長石,遺址仍可尋,當地人稱「鬼街」。
2.歡罕。這個部落專工架火煮飯。現有昆罕寨,二十四戶,一三六人;昆罕小寨十二戶,七十八人,都是布朗族,今屬景洪市大渡崗鄉。「昆」為「歡」的異譯,以下同,均不注。
3.歡洛。與前述歡滿相近,相傳這個部落專事採集芭蕉葉,用作包飯食便於輸送。今大渡崗鄉有「約六平方公里,海拔一四一三米」的昆洛山,「昆洛即昆人中名洛的部落名」,山以部落名(3)。
4.歡歇。相傳這個部落也是專事做飯。
5.歡養。相傳這個部落故地在猛養山區。今猛養鄉猛養河邊有「歡養」寨,並非原「歡養」部落所在地,而是古代「桑西雙歡」戰敗後剩餘之人所建的寨子,傣語「養」有剩餘之意。
6.歡餓。相傳這個部落為「卡戈允」,是愛尼(哈尼)族的城堡。
7.歡島。相傳這個部落守護著三道大門。
8.歡佤。相傳這個部落是保管武器,後裔即為佤族。
9.歡阿。不詳。
10.歡羅。其故地在景訥至思茅之間的途中。傳說這個部落有個金盆破了一半,留下在歡罕。
11.歡扁。不詳。
12.歡安。故地在今猛養鄉西北有「昆安梁子」山,「昆安即昆人中的名安的部落名」。「山住過昆安寨,山以村名,約四平方公里,海拔一一七六米」。(4)
13.歡格。今猛養鄉東北有昆格村,全村一七八戶,一一三六人,其中有一○七戶,六四七人為未定族稱的「昆」人,他們分布在以下五寨:納板二十三戶,一一三人;四家寨六戶,三十六人;納回帕四十一戶,二六三人;曼壩約十三戶,八十七人;曼戈龍二十四戶,一四八人。
14.歡布瓏。故地與歡格相近。
15.歡涅。故地靠近猛養南回河,曾發現過出土的「犁頭」。
16.歡咪,亦譯「歡滅」。其故地有兩說,一說在允景洪鎮三達山上,有曼咪大寨,為布朗族聚居,共三十六戶,一八四人;還有「從曼咪帶名」分出的曼咪小寨,仍為布朗族聚居,有四十二戶,二一一人。另一說其故地在今景洪市與猛海縣毗鄰的嘎棟鄉山區,當地有曼咪戈牛和曼播賀哈兩寨是布朗族聚居寨,共六十一戶,三二九人。持此說的刀正樂先生還特別強調:「歡咪的地界一直延伸到猛海縣布朗族聚居的老寨曼峨一帶。
17.歡壩。故地在猛養南養河兩岸。
18.歡冷。故地在景洪市猛龍鄉西北部山區,今有帕冷二隊、三隊,「原村在一個傾斜的岩石旁,後分出為二隊」,共四十七戶。
19.歡舊。故地在大渡崗鄉西南的大荒壩與關平之間。
20.歡西定。故地在猛海縣西定鄉一帶,今為布朗族在西雙版納主要聚居地。
21.歡先。故地在允景洪鎮三達山曼外辦事處,接近曼咪,該地有六家寨共三十三戶,一六○人,都是布朗族。
22.歡色。故地在景訥至猛養的山間。
23.歡溫。故地在歡格相近的「回南溫」(傣語地名:「山箐里的熱水塘」。)
24.歡呂。故地在猛海縣猛宋鄉的布朗族寨大曼呂,一直延伸到景洪市嘎棟鄉納板一帶。
25.歡糯。故地與歡呂相鄰,就在景洪市納板、曼火猛一帶。
26.歡稿。故地在景訥、猛養大山中間。
27.歡播。故地在允景洪鎮曼德寨後山上。
28.歡莫。歡莫和下述歡累、歡裴的故地均在景洪市猛罕鄉、曼洪鄉一帶。
29.歡累。
30.歡裴。
31.歡蚌。故地在景訥鄉的上龍潭。
32.歡南。故地在景訥鄉山間名為回賀龐地方,前些年曾發現有石磨等遺物。
上述「桑西雙歡」各部落,以景洪市景訥鄉、猛養鄉之間的大山為中心,分布於瀾滄江兩岸。其幅圓大體包括今景洪市、猛海縣以及與之相毗鄰的緬甸邊境地域。
相傳「卡細先瑪麻」首領召法細達和傣族首領召片領之間是對立的。起初,召法細達勢力很大。養有不少土蜂,放這些土蜂到處飛,遠到今天緬甸境的猛艮(景棟),都有召法細達的土蜂飛到,丸土蜂所到之處,把能吃的莊稼、食品都吃光了。召片領致函召法細達,要求他把土蜂管好,惹怒了召法細達,引起了戰爭。召法細達的弩子很厲害,七棵樹破出七支弩才有一支弩合用;這支弩射出去百發百中,弩子射中敵人後又會重新飛回到召法細達的手上。
召片領打不贏戰爭,就想計策謀害召法細達,他選了傣族的美女,又準備了一頂金帽子,帽的襯布是用婦女穿過的筒裙布。要把美女獻給召法細達,召片領暗中先囑咐美女,伺機要把金帽戴給他。美女趁作樂時,把金帽戴在了召法細達頭上;果然,召法細達的頭暈了,透身都軟了,再不能打仗了。這時,景洪召片領命曼莫的巫師占卜也得知金帽戴上了,應當趕快獻白水牛。於是,召片領在巫師相助下鏢殺了白水牛,以此獻於召法細達。並向其禱告:尊您為猛神,按期祭您。這樣,召法細達就死了。還有一說是:召片領鏢殺白水牛後,召法細達只是眼瞎了,再也打不贏召片領,召法細達的部隊只好向猛勇(今屬緬甸境)方向撤去,七天七夜才過完瀾滄江。召法細達退到了猛勇,又有傣族首領召公滿和他敵對(有人說召公滿是召片領之子,受命去開闢猛勇)。召公滿為了徹底消滅召沃細達,假意和好,在「濃先巴」(大魚塘)畔設宴,燒魚擺酒,宴請召法細達及其部屬戰將。召公滿備下三種酒,一是烈性酒,二是麻醉藥酒,三是淡酒。當召法細達領著部屬前來赴宴時,召公滿說:「我們是和好求團結一心,大家都身帶著刀弩喝酒,這還像話嗎?」於是把傣家戰將武器收攏捆好。召法細達及其部屬也就照著做了。這時,召公滿令人上酒,先讓召法細達喝烈性酒,自己斟淡酒喝;待召法細達微醉後,再讓他們喝麻藥酒,趁召法細達及其部屬酣睡之際把他們都殺了,「卡細先瑪麻」最終歸於失敗。
二、歡滿的召法細達神宮及其祭祀拾零
今景洪市猛養鄉大河邊村的森林保護區內的歡滿老寨,傳說是「卡細先瑪麻」首領召法細達的統治中心,在傣族戰勝「卡細先瑪麻」後,景洪召片領即在此立其首領召法細達神位。如今,在歡滿密林深處,依然有供奉召法細達的「伙色」。「伙色」為傣語,意即「神宮」。
召法細達神宮有一大篷花,名叫「洛梅細則」意謂四色花,有的又叫它七色花,「四」或「七」均為概數,言其能開紫、藍、紅、黃各色花朵。在花蓬後有道柵門,門上掛有驅邪除魔的竹編神器「達寮」,其門名曰「巴都綱滿」,即「歡滿中心神門」;在傣語里「巴都」是「門」,「綱滿」指立神宮處是「歡滿的中心」。神宮為約五米見方的「干欄」樓房,草排覆頂,樓下空曠,樓上以竹片木板相圍,面南設神案,正中置袖珍式白布被墊為神位標誌,其前常年供有米飯,茶、酒和淨水。
歷史上西雙版納最高統治者召片領,將歡南附近的布朗族共六寨(如今有的寨已不存),列入封建等級「滾很召」,即「召片領的家奴」。這六個寨與其相鄰的猛養和景訥土司都無權管轄,無權對他們派伕派糧派款,他們受召片領委託常年供奉召法細達,並在每年傣歷六月按期祭祀,主要獻牲是一頭黑豬。豬不用刀殺,而用木棒活活敲死,架火燒烤刮毛,開膛後供獻。此外,每年的傣曆新年和九月十五(關門節)、十二月十五日(開門節)這三大節日,歡滿都要派出頭人、百姓代表去景洪「穌瑪召」就是去向召片領致意祝福,要帶兩三斤馬鹿和麂子肉干巴,還有蜂蛹和用竹筒裝的蜂蜜作為敬獻的供品。
在歡滿,專職供奉召法細達的巫師叫艾色,「艾」是冠於傣族男性名字前的專用詞,西雙版納布朗族皆通用;「色」在傣語里其意為神,艾色,意即「神的侍者」,其職世襲相傳。一九八八年在任的艾色已年過古稀,他有個兒子還是猛養鄉大河邊村村長,這身為村長父親的艾色供奉召法細達依然十分虔誠。人們說艾色是代表召片領供猛神召法細達,他每天都要在召法細達神位前點燃兩柱自製的線香,獻米飯和茶水。意想不到這位艾色還懷念著召片領,曾向刀正樂先生打听「小召片領(指末代召片領刀世勛先生)在哪兒?想吃蜂蜜嗎?想吃蜂蛹嗎?人們知道:油炸蜂蛹是傣族、布朗族共有的美味佳肴。
西雙版納的布朗族多信仰佛教,村寨有佛寺,但是受召片領委託奉猛神召法細達的歡滿等六寨,至今沒有皈依佛門,老輩人解釋:「佛祖是在召法細達成神後才有的。」不過,信佛教的地區仍然供奉召法細達。歡滿的艾色就知道召法細達還有一座神宮,也像歡滿一樣是有專職艾色常年供奉的,其地在今猛海縣猛宋鄉的布朗族寨子大曼呂。還有,在景洪、猛海、猛遮、猛龍、猛混、猛罕等地的傣族都尊奉召法細達為猛神之一,祭祀猛神時都要呼喚其名,迎其神駕,請其接受供獻。
三、「卡細先瑪麻」是孟高棉語族的先民
「桑西雙歡」就是「卡細先瑪麻」,它為我們初步揭開了「卡細先瑪麻」費解之謎。在傣文史料中「卡細先瑪麻」,又稱「卡維腊」、「卡腊」,前文說過「卡」有貶意;或以雅語相稱:「達比腊」、「達咩腊」,有尊為長者之意。「卡細先瑪麻」傳說和上述三十二個部落分布的地或相應,在今西雙版納景洪市的猛養、猛龍、猛景洪、猛罕、景訥、猛旺、猛海縣的猛海、猛混、猛宋、猛遮、猛往、猛康、猛阿、猛板、景洛,以及與上述縣市毗鄰的緬甸撣族地區。這些地區的傣文抄本中,都把「卡細先瑪麻」描述為是個十分強大、善於騎射、勇猛善戰,頗有幾分神出鬼沒色彩的族群。在上述很多地方的山區往昔用於防守的壕溝遺跡至今可見,在景洪的隴南山附近,還發現過在丘陵地帶「高處開溝、低處築牆,形成山寨式的防衛」城防文化遺跡。該城遺址稱為「允景維」,「分內城與外城,沒有城牆,而是開壕溝為界」;「外城溝一般面寬七──八米,底寬四米,深五──八米不等」。六○年代實地考察的邱宣充先生著文稱:內城住的是「卡細先瑪麻」的王族和頭人,外城住的「百姓有的養馬,有的做飯、有的打仗、有的送鬼、傳話」。「這裡居住著四千個人,有四千匹馬」。其「特徵是:養很多馬,善於騎射,驍勇善戰」(5)。
多年以來,在研究西雙版納的一些同仁中,對「卡細先瑪麻」的族屬有過各種推度和解釋,有的學者就「百越與百濮」、「孟語(孟高棉語)族」、「撣與緬人」、「彝語族」都和「卡細先瑪麻」的文化遺存進行比較作過「可能性」的分析。(6)但是都沒有結論,這可以理解。而近年尤為風傳的是將「卡細先瑪麻」推度為元朝的斗瞬軍隊。因為、元史裡不僅一次有過征「八百媳婦」國和「車里」(今景洪)的記載,更何況「蒙古人至今還是不離馬鞍的民族」等等,所言頗有幾分「鑿鑿有據」之態。但如果審慎考慮,則疑點自生。元朝發兵征「八百媳婦」也罷,征車里也罷,何至於如前述要築城防?何至於形成部落?何至於開挖工程浩大的壕溝散布廣大山林間?至今在猛養、猛景洪、景訥、猛阿、猛往等地山區遺存的被稱之為「卡細先瑪麻」壕溝以及在這些有壕溝的地方發現的陶器、陶片等,實在難以和元朝發兵征車里或「八百媳婦」聯繫起來。「卡細先瑪麻」為「蒙古軍」之說,可謂所言不著邊際,難以置信。
那麼「卡細先瑪麻」族屬究竟是誰?
筆者認為:「卡細先瑪麻」──即和傣族首領召片領曾經處於敵對,有過戰事的「桑西雙歡」首領召法細達及其所屬──其族屬乃是今日操孟高棉語佤德語支(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其後裔在今天的西雙版納主要是布朗族和佤族以及未定族稱的「昆格(歡格、空格)」人等。
傳說中「卡細先瑪麻」的突出特色,是精於騎射、勇猛善戰者,在雲南史乘中我們可以追尋到他們的蹤跡。元代李京撰《雲南志略》載:「蒲蠻,一名扑子蠻,在瀾滄江迤西。性勇捷,長為盜賊。騎馬不用鞍,跌足,衣短甲,腔膝皆露。善用槍弩,首插雉尾,馳突如飛」。蒲蠻,是今日布朗族的古稱,這是早為學界公認的。上述記載棄其貶辭,正是精於騎射、勇猛善戰的「卡細先瑪麻」的具體形象。近人作《雲南志校釋》就上述記載曾作如下分析:「《志略》所述頗不類扑子蠻情狀,而與望直蠻全同,疑京(李京)有誤」(7)。所言「望苴蠻」多認為是今天佤族先民。而佤和布朗、德昂等民族先民均為盂高棉語族,其族屬淵源關係密切;直至今天這些民族的自稱和他稱在不少地區都有相通者。因此,漢文史籍中將佤族和布朗族先民混雜相稱,就更應當可以理解了。至此,不禁想起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一日,筆者在西雙版納訪問孟海縣文化局布朗族幹部岩香蘭時,他告知筆者:「老輩人說布朗和佤族就是一家」。正是這樣,所以如今猛海、瀾滄、思茅一帶的布朗族,不僅仍和附近佤族一樣仍自稱「腊佤」,甚至瀾滄打崗一帶的布朗族對「腊佤」還自出新意解釋「意鳥心腸好的人」(8)。通過上述表明,我們無意於在「卡細先瑪麻」和布朗族之間劃上個等號,那既不科學也是不必要的。但可以肯定地說「卡西先瑪麻」的族屬是今日操孟高棉語佤德語支的布朗族和佤族的先民。
上文曾言及的如今在西雙版納景洪市、猛海縣一些山區,仍可見到昔日「卡細先瑪麻」城寨防衛的壕溝。一九八八年,筆者在地處景洪壩西南端丘陵地帶的曼播訪問,實地看到景洪農場十一分場的膠林里仍存昔日「卡西先瑪麻」的壕溝殘段。這依山勢延伸的壕溝溝面最寬處達五六米,深約三米、底寬一米餘;故而曼播人至今對「卡細先瑪麻」曾扎營建寨的後山奉若神明。古代「卡細先瑪麻」開挖壕溝作為防衛的文化標誌,直到現代仍可在某些地區的布朗族、佤族村規寨見到,尤其以佤族聚居的腹心地區最為典型。一九三五年,學界先賢方國瑜「以研究雲南史地之興趣,參加滇緬界務交涉」之機遇,在當時耿馬傣族士司罕富廷陪同下深入佤族地區考察,對其寨址外貌有過如下描述:佤族「所住寨,聚數十百家而居,四周掘深溝,環如馬蹄形,有至二三重者,溝寬七八尺,深五六尺,溝內外密種荊棘護以竹籬,即雞犬亦不能穿入,其堅固猶勝於城垣。寨門亦深溝入,溝外種密棘覆其上,深丈許,寬不過五六尺,有長十餘丈者,設門數重,門用厚板,關之壯夫不能入也」(9)。讀至此,對照前文所述六○年代在景洪發現的「卡細先瑪麻」遺址,令人遐思無限。
還有,傳說中「卡細先瑪麻」首領「召法細達養有不少土蜂,這些土蜂到處飛,能把吃的食品、莊稼都吃完了」,由此才引起和傣族首領召片領的戰爭。傳說神奇近乎荒誕,卻耐人尋味,不禁使人聯想到召真悍在景真戰勝大黑蜂勝利建猛的故事。召真悍被視為是傣族歷史英雄人物,他最後是深入大黑蜂蜂穴,奪取了「蜂寶」,於是戰勝土著「卡悶」,才在景真定居建猛。召真悍奪取「蜂寶」之地,如今演變為佛門聖跡,就是西雙版納著名旅遊勝地景真八角亭。(10)大黑土蜂何以如此厲害?有類似傳說,筆者在德宏傣族地區考察時還曾听過,講的是有大土蜂能飛百里之外叮人致死,引起若干紛爭,養蜂的是德昂族先民。那大土蜂窩所在地是在今畹町市名曰「奪香」的寨子,傣語「奪香」就是蜂寶之意。無獨有偶,這畹町市的奪香佛寺也是德宏洲著名的佛門聖地,每到春種秋收季節,不僅畹町、瑞麗、潞西幾個縣市乃至緬甸境相鄰的傣(撣)族皆來朝拜,因為奪香佛寺裡供奉著敢於和佛祖釋迦牟尼鬥智的谷魂奶奶(雅歡毫)偶像。令人驚嘆的是,該寨至今聚居的仍為德昂族。至此,不由人推度這大黑蜂或說土蜂是否曾是孟高棉語族先民的圖騰呢?曾任雲南民族學院傣語教師的岩喊先生,也曾這樣寫信告知筆者:「土蜂」可能曾是布朗族的圖騰。但又談及傣族以為蜜蜂是尊貴的,至今亦然;傣族先民或者以此將敵對者喻為「土蜂」,含有貶意,就難以斷言了。最近,我們還注意到一位佤族學者在《濮人與古代馬來半島文化》一文中,專設一節談「大黑蜂崇拜」問題。文稱:「黑蜂,又叫大黑土蜂和黑土蜂和黑胡蜂,佤語稱之為ong(《佤漢簡明詞典》,「ong」條),黑蜂也是佤族及德昂族崇拜的動物。「該文談到今天分布在我國雲南省西盟、孟連兩縣的佤族中的支系「羅佤人」(Luva)至今仍有崇拜黑蜂的文化孑遺,該文寫道:「羅佤人在婦孺皆知的《安桂故事》中,傳說女始祖安桂死後,人們讓大黑蜂守她的墳墓。布饒人唱輓歌時,反覆地唱道:「靈魂啊,回去吧,沿著黑蜂飛走的山梁回去;靈魂啊,回去吧,渡過蜥蜴創造的湖泊回去!」蜥蜴也是佤族崇拜的神物。羅佤人之所以崇拜黑蜂,可能與他們的王或王的某件事跡有聯系,他們常常用黑蜂比喻英雄或君王。另外,王者的稱呼vong與黑蜂ong音很相近,也許諧音關係,使黑蜂成了民族英雄的象徵」(11)。至此,推度大黑土蜂或說大土蜂曾可能是孟高棉語族先民的神聖圖騰不至於是胡言白道吧!
最後,西雙版納歷史上傣族召片領戰勝「卡細先瑪麻」王召法細達後,尊奉其為猛神,這無疑是實現其政治統治對被征服者給以慰藉的精神興奮劑,這種歷史的明智和愚昧的交合,令人玩味深思!惟其如此,使我們能借助凝聚於神靈間、祭壇上的歷史之斑痕,審視它、辨析它,試作此文,以明「卡細先瑪麻」的族屬,並借此探析到古代西雙版納傣族和孟高棉語族中的布朗族、佤族先民之間的微妙關係。
注釋
(1)《傣族社會歷史調查》(西雙版納之七),一頁,雲南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2)(3)(4)《雲南省景洪縣地名志》,景洪縣人民政府編,一九八五年印行。本節所引各寨戶口數均見該書,不一一具注。
(5)(6)詳見邱宣充:《景洪允景維遺址調查》一文,載《雲南民族文物調查》,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7)趙占甫:《雲南志校釋》一六四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8)思茅行署民族事務委員會編:《布朗族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9)方國瑜:《卡佤山聞見記》。轉摘自《永昌府文征》記載卷三十二。
(10)參見拙著《傣族神靈崇拜覓蹤》一書中《景真建猛傳說和猛神崇拜》,雲南民族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11)尼嘎:《濮人與古代馬來半島文化:從色曼人習俗看古羅佤人文化在馬來半島的影響》,載《雲南民族學院學報》一九九五年二期。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7期;民國86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