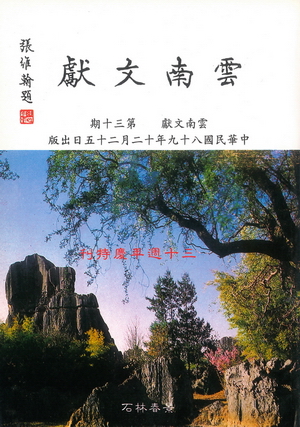昆明大觀樓長聯與孫髯翁的千古胸懷
作者/鄭千山
出昆明城西三公里,與太華山隔水相望的近華浦,在明末還是一片美景,徐霞客在其《遊太華山記》中描述這裡的景緻時寫道:「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兩岸平疇夾水。十里田盡,崔葦滿澤,舟行深綠間,不復知為滇池巨流,是為草海。草間舟道甚狹,遙望西山繞壁東出,削崖排空……」的確有幾分「野趣大觀」的味道,於是因景會綠,近華浦上誕生了一座日後成為了中國「四大名樓」之一的昆明大觀樓(另外三座為湖南岳陽樓、湖北黃鶴樓及江西滕王閣)。
大觀樓初建於清康熙年間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年)湖北籍僧人乾印(一說為明人)初建觀音寺,其「講《妙法蓮花經》,聽者常千人」。二十九年(一六九○年),一代名宦王繼文(雲南巡撫)見此地「遠浦遙岑,風帆煙樹,擅湖山之勝」。乃建成樓閣一群,有華嚴閣、涌月亭、催耕館、觀稼堂等,其中以大觀樓為最顯,「一幅湖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從此,大觀樓成為昆明的一處名勝。
正如岳陽樓、黃鶴樓、滕王閣分別以范仲淹《岳陽樓記》、崔籲《黃鶴樓》詩、王勃《滕王閣序》顯名一樣,大觀樓的聞名天下,乃是有了一個寒士孫髯翁的《大觀樓長聯》,這一幅煌煌長聯,撰成於清乾隆年間,其超越時空的深刻感悟,可以曹雪芹的《紅樓夢》媲美,從長聯與《紅樓》的思想來看,受佛家「性起緣空」「諸法無常」等的影響是一脈相承的,由於悟性高,其作品所顯現的境界,自非時代的「俗唱」可以比況的,曹雪芹如此,孫髯翁也如此。
現今大觀樓已成為一座名聞遐邇的名樓,其長聯的著作權也由「早已定論」成為了「可以一論」的了,近年來,先有趙宏逵等人在有關報刊上提出質疑,將長聯作者說成曲靖的孫璚,僅僅是同姓(孫髯,字髯翁,號頤庵,晚年自號蛟台老人;孫璚,字蘊石,號耕塢,晚年又號鶴髯老人)就欲一爭此「光榮」,近年來更是在新出版的《新編曲靖風物志》中將孫璚幾定於長聯作者,這已足可看出人們對長聯的重視(本文暫且不談有關二孫著作權之爭的有關話題)。
一聯既出,俗唱紛逃,這可算是昆明大觀樓長聯橫空出世以來出現的奇特景象,清人吳仰賢曾經寫道;「鐵版銅琶*韃聲,髯翁才氣劇縱橫。樓頭一百八十字,黃鶴留題萬古名」。但孫髯翁也許才氣縱橫,也許負氣自傲,而長聯本身的境界,卻是超越千古的,是對於宇宙人生真相的詮釋,《眼前有景道不得》,這樣的感概,恐非一人。
這裡要說到淨樂,這位嘉慶、道光年間活躍於昆明西郊的名僧,以重修昆明白馬廟及乾印(亦有書稱此人為明人,待考)觀音寺聞名一時,他持戒精嚴,才情名望甚高,因頗不服氣一介寒士孫髯翁的「恃才之作騙,乃集資在大觀樓後建起了一座五楹三層之華嚴閣,高出大觀樓丈餘,淨樂親自撰寫刊刻了一幅一八四字的新長聯懸於樓前(世稱淨樂長詩),欲以孫氏長聯一較高低,聯曰:
疊閣凌虛,彩雲南觀,皇圖列千峰拱首,萬派朝宗,金碧聯輝,山河壯麗。視晴嵐掩翠,曉霧含煙,升曙色於丹崖,蒼松鶴淚;挂斜陽於青峰,石廠猿啼,暫息煩襟,凝神雅曠,豁爾謳歌葉韻,風月宜人,性靜幽閑,互相唱和;得意時指點此間真面目;
層樓映水,佛日西懸,帝德容六昭皈心,百蠻順化,昆華聚秀,宇宙清夷。聽梵唄高吟,法音朗誦,笑拈花于鷲岭,理契衣傳;儕立雪於少林,道微缽受。久修淨行,釋念圓融,歷然主伴交秦,凡聖泯跡,心源妙湛,回脫根塵,忘機處發揮這段大光明。
淨樂長聯雖用語華麗,對仗工整,平仄精當,但其境界無論詞意還是胸中所涵,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去孫氏長聯多矣!時間是錘煉藝術的最好的尺度,隨著華嚴閣毀於戰火,淨樂長聯也隨之湮沒無聞(近日筆者因參與撰寫《昆明佛教史》,方從一私人藏書處偶然找到這幅長聯,特抄出以饗讀者,作為史料一存也)。
在有關大觀樓長聯的諸多改竄中,最貽笑於後人的莫過於阮元。這位當時名重一時,胸中並不乏學問文章的一代名人,竟因改纂孫髯翁的長聯,而留下一個千古笑柄,也許這位「正統」的雲貴總督大人嗅出了什麼吧,居然在孫髯翁的長聯中嗅出了「叛逆」的氣息,「以正統之漢唐宋元偉烈豐功總歸一空為主,豈不駸駸乎說到我朝?於是煞費苦心,纂改長聯,他把好瑞瑞的長聯改成了什麼樣子?請看阮芸台大人的大筆: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憑欄向遠,喜茫茫波浪無邊。有東釀金馬,西耆碧雞,北倚盤龍,南馴寶象。高人韻士,惜抛流水光陰。趁蟹嶼螺洲,襯將起蒼崖翠壁。更蘋天葦地,早收回薄霧殘霞。莫孤負:四周香稻,萬頃鷗沙,九夏芙蓉,三春場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爨長蒙酋,費盡移山氣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蘚碣苔碑,都付與荒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鴻雁,一片滄桑。
這樣拙劣的東西,不僅滇中文人,就連民間群眾也不難看出個優劣,《滇中瑣記》中載有一名諺云:「軟(阮)煙袋(芸台)不通,韭菜夢卜蔥。擅改古人對,笑煞孫髯翁!」可見老百姓的天空中,與他們心心相共嗚的是胸中有無窮大境界、大宇宙的孫髯翁,是那位墊居昆明大梅園巷中「萬樹梅花一布衣」的可親可敬的孫髯翁!是孫髯翁用畢生心力唱出的一闋長聯絕響!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用這兩句詞來稱讚被譽為「天下第一長聯」昆明大觀樓長聯作者孫髯翁的胸懷,也許並不為過,因為在這副「渾灝流轉,化去堆深之跡」的百八十字間,分明展現著一個比大海、比天空更廣闊的人的襟懷│
這襟懷中融入了山與水,草與花,人與事,詩與史,融入了千年往事,萬古煙雲,更融入了無限的情懷,卓絕的品質……「心事浩茫連廣字」,兩百多年來,風風雨雨它贏得了多少人的讚嘆,贏得了多少人心靈的共嗚!「長聯獨在壁,巨筆信如橡。我亦披襟久,雄心溢兩間」。孫髯翁,是誰賦予了你這樣的靈感,這樣的妙語,這樣的大手筆?
作為一介寒士,終生未仕,窮困潦倒,晚年甚至只能「寄寓圓通寺之咒蛟台,更號蛟台老人,卜易為活,然求百錢不可得,恒數日斷炊煙……」(師范《孫髯翁擬輸捐直省條緩征逮欠謝表後記》),孫髯翁何以擁有這樣的胸襟,擁有這樣長久的另一種生命,藝術的生命?
其實,他一生中的特立獨行,如鶴入雞群,為我們詮釋著一個可驚、可嘆、可佩的長天飄然一髯翁│
這位自小「生而有髭,故以髯名」的奇人,「自幼負奇氣,應童試,功令必搜檢乃放入,憤然曰:『是以盜賊待士也,吾不能受辱。』掉頭去,從此不復與考」。士可殺不可辱;在他的同時代人錢澧、師范、傅映(應)台等的記述中,我們看到:
「……布衣孫髯,故三原人也,詩名著稱尤早,記覽亦博……」、「博學多識,詩古文辭皆豪者不羈,一時名士相與酬唱,所撰樂府,雖不逮漢魏,亦幾入香山、崆峒之室。五、七規仿唐人,時有傑作……」,「至其近體,氣韻沈(沉)雄,一時社中皆為斂手。」「躪史執經,揚風于雅。鶴峰李中丞、昆浦錢少司馬、南村孫大令以及唐藥州、楊夢舫、施竹田咸與酬唱,每出游心以書自隨,累累盈路,觀者無不指為孫老先生行廚也……。」
「中歲客大理,作竹枝詞云:『龍王不下栽秋雨,躲在蒼山晌日頭』。……是時太守王公懶不治事,故以此諷之……。」
「願不肯應試,廣寧張東閣為制師示意於徐南岡太守,孫潛村山長連促之,皆辭……」「喜種梅,嘗作小印曰『萬樹梅花一布衣』。」
這何等瀟灑,何等傲然不群,又何等高潔,甚至顯出了林和靖那「梅妻鶴子」的局促,做作。「吾滇士風有此硯隱一派,君子哉!美俗哉!」(袁嘉谷《滇繹》)
在林(松)玉田的《(孫頤庵擬盤龍江水利圖說)後跋》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然未嘗不念斯民之利病焉,故於詩賦藝文外,著有(盤龍江水利圖說)一冊,……自源至委,防利之所在,害之所積,言之最詳,及疏之何方,導之何術,亦靡不籌之最當。誰謂無志功名者,即無心世故哉!」當我煞費心神解讀髯翁的《圖說》,我與林玉田深有同感,我彷彿看見的是那位不求聞達的長髯布衣傴褸地行走在故鄉河沿、郊外,他關心民瘓甚於關心己疾,「窮歲月之跋涉」「閑披《禹貢》、《桑經》、《酈注》之書」真正具備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情懷,這是怎樣的人生境界?
這樣的胸懷,這樣的境界,不可能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悲天憫人,寧靜致遠,在孫髯翁組合成的文字後,在那一片無窮的天空,那一種穿越時空的神籟。可以想見,一個人的胸懷與境界,早已是超越語言和文字而存在的,在語言文字中迷戀,無疑會成為「髏骷的迷戀者」,這只能是雕蟲小技,不可能雕琢出生命最實在的部分。
我曾經多次登臨過大觀樓,憑欄遠眺,品味那一種海天寥廓的感覺,吟味長聯,更平添幾許思古悠情和人生況味。浩淼的滇池,你給了這飄然髯翁怎樣的靈光,這靈光一直洞穿到今天,當當年你步履響徹的老街已被鋪天蓋地的馬賽克和玻璃墻所替代的今天,這屬於多麼難得的享受?當你種滿萬樹梅花的大梅園巷已成為一片廢墟,你日夜歌吟,生於茲長於茲的昆明已成為某些權貴賣地皮求發財,貪污腐敗,徹底毀滅歷史文化的地方時,你會到哪裡去尋找你心的歸屬?當我所在城市最後一塊田野消失的時候,我只好到更遠的地方去尋覓你心的應答。在彌勒,你埋瘞鶴骨的地方,我去尋找過,在豪華賓館的後面,我看見了你的墓冢,在華麗的裝飾中,你那簡單的大土堆是否顯得有些不協調,你讀得懂那些現代的方式嗎?人的境界中,為什麼非要堆砌起繁復的石頭,石頭上又何需鐫上金光燦斕的名字呢?「道在多違俗,名高轉誤身。自非天下士,誰是個中人?魚鳥忘機盡,江山寫照真。我懷相領取,汨沒任風塵。」你說。物我兩忘,妙有真空,這是指人間真詮的「心中話」。恍惚間,這髯翁活了,在一堆被廢棄的舊墓碑間,在一群遛鳥的老人間,在一陣吆喝聲中,一縷陽光,一片雲影中,無處不在的髯翁,人間髯翁。
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輕就是那種卑瑣、狹隘、極端物欲之輕,它們將關閉一扇扇心窗,讓人們無法進入更廣闊、更長久的時空。孫髯翁的胸懷,如海納百川;孫髯翁的胸懷,若壁立千仞。在當年被中心話語者剝奪了話語權的一個寒士,燈火闌珊處卻驀現了他「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的胸中大宇宙,這是涵容萬千氣象、氣吞萬里的大宇宙,歷史還給了他永久的話語權:「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0期;民國89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