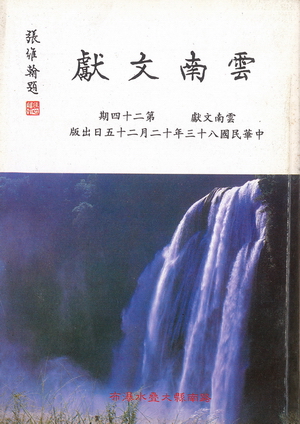陳榮昌先生評傳
作者/張誠
清末民初,雲南也同全國一樣,正在實施戊戌變法時的「新政」。「新政」的內容主要是改革軍制和改變教育制度。雲南在實施「新政」方面做得比較突出,在全國有一定的影響。在改革軍制方面,清政府於一九○八年在雲南改編新軍,成立陸軍第十九鎮(全國共有新軍三十六鎮)。同年,雲南陸軍講武學堂成立,專門培訓軍官。雲南講武堂在辛亥革命前後培養了不少中國當代傑出的軍事人才,這些人在雲南重九起義、護國起義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黃埔軍校成立,孫中山曾從雲南講武堂中選調一批教官去黃埔任教,講武堂在全國享有較高的聲譽。在改革教育制度方面雲南也做得很好,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在昆明設經正書院,這是當時雲南的最高學府。隨著新學制的改革,一九○二年雲南將經正書院、五華書院合併成立雲南高等學堂,並開始選派留日學生。留日生中又以學習陸軍的占多數,這些人後來都成為雲南、貴州軍政界的要人(如:唐繼堯、李根源、周鐘岳、顧品珍、楊振鴻、葉荃、黃毓成、羅佩金、庾恩暘等),在全國影響很大。
陳榮昌正是在這一新舊變革時期擔任重要職務並能承上啓下的歷史人物。研究他這一段時期的主要經歷及其書法藝術的創作過程,無疑是雲貴兩省近代教育史、書法史上重要的一頁。
陳榮昌,字筱圃,號虛齋,又號鐵人,別號遁農,晚號困叟,雲南昆明人。先生祖籍江蘇上元縣,明崇禎九年(一六三六)來滇,遂世居昆明,以商為業。至曾祖輩,始從儒學。他的父親陳維愷中進士後,授福建知事,因閩語不通,恐訴訟有失,乃辭官歸里,清廷授雲南東川府學教授。在偕周夫人赴任途中,陳榮昌於咸豐十年(一八六○)六月二十四日誕生於旅途中。之後,父親任職東川,陳榮昌亦隨家居東川多年。
他出生後,正值國家多事之秋。外則鴉片戰爭失利、割地賠款,英法聯軍大舉入侵破壞;內則太平天國起義正與清軍酣戰江淮:本省回族杜文秀起義,圍攻省會昆明。清軍雖鎮壓了起義軍,但全國老百姓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清廷的腐敗無能,終使甲午海戰失利,戊戌變法失敗,八國聯軍干涉,遂至巨額庚子賠款諸事端。最後導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反對帝制的護國討袁等等。近一個世紀,中國的國計民生,終未得安定。
儘管國事日非,筱圃先生仍以仕途為正身。他從小聰慧過人,刻苦用功讀書,很早就顯露出極大的才華。他父親去世時,他才八歲,父親臨終前把教育他的責任托咐給會澤宿儒孟覺人《光鐸)先生。他在極艱苦的學習環境中,精究經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基礎,能作很好的詩詞和駢散文章,並寫得一手好字。陳榮昌一直非常欽佩孟師的學問、為人,孟覺人除竭心盡力地教育他外,還不時接濟他家柴米。後來他取得功名做了大官,始終不忘恩師孟覺人。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陳榮昌由東川赴昆明應考,居然得中頭名秀才,年僅十四歲。雲南學政李端棻驚嘆地說:「吾意此文必滇中老儒所作,不料竟出爾幼童之手。」李公又將他推荐給當時任雲南巡撫的岑毓英,岑要當面親試。據傳,岑見他身著一蘭布長衫,脫口便說。「小人蘭衫拖地。』筱圃先生隨口應道;「大人紅頂朝天。」雖是戲言,但對仗之工,應對之速,令毓英贊不絕口,「這娃娃果然名不虛傳。」又問及身世、讀書情況,愈加愛憐,遂把他接進撫署讀書。先生因此而結識岑帥,並與其子春榮、春暄(後任雲貴總督)、春蓂(後任湖南巡撫)結成莫逆終生好友。
年紀稍長,岑毓英又送他進五華書院深造。經過五年的刻苦攻讀,於清光緒六年(一八八○)朝考中選;八年(一八八二)鄉試!以榜首中解元!九年(一八八三)赴京會試!中二甲進士,入翰林院庶吉士、時年二十四歲,在翰林院的幾年中,廣結賢儒之士,學問精進,十二年(一八八六)授翰林院編修,供職國史館。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秋八月,先生奉命調任貴州提學使,年僅二十九歲。十二月履任,迎母養於貴州。先生在黔督學四年,全力整頓學風,風格峭厲,力主先敦品而後立學,使黔省學風為之一變,倍受黔省人士贊揚,時有「小學台」的稱譽。先生任職之初,曾上游五棚之貴陽府、遵義府、貴定府、興義府、安順府考試畢、將情況奏明,文武鄉試畢後,又出省城考試下游之平越廳、鎮遠廳、思南府…等八棚,所到之處,嚴格甄核,拔取人材。自先生親督黔學後,凡每歲兩試,都是關防極嚴,偏門命題,即督試教官稽察,至掃棚乃退。試卷,助閱員擬呈後,先生一一覆閱,始定甲乙,考優極慎重,故所取皆真才,為全省人士所敬佩。
先生一生景仰錢南園,在即將卸任黔學之際,追思雲南鄉賢南園之正氣文章,恐將代遠年久而淹沒無聞。如何激勵雲南學子效先正高風亮節,使之流傳後世,唯有建專祠而能永享馨芳。於是他倡建南園祠堂,並寄俸銀二千兩回滇,託摯友施有奎、陳蘭卿為南園先生卜地建祠。擇得翠湖畔史姓地,寬敞甚佳,經與地主史小泉商洽,得小泉同意,建祠三楹,東西廂房各二,祠東隙地辟為花園,建樓三楹(即今翠湖賓館一側之青蓮街口,筱圃先生去世後,《錢公祠》被盧漢改建為別墅)。所剩銀兩,備刻《南園遺集》,購置祭田十數畝,作為祠堂夏秋二季祭祀掃墓費用。筱圃先生開此尊崇鄉賢之風,樹立先正楷模,對於振奮滇省精神、培養地方人才確是做了一件大好事。難怪施有奎先生在存古軒文集《錢南園先生遺集後序》中云:「余嘗怪滇人士之服官歸者,多求田問舍,不能為鄉先達收拾遺文。令嘉言懿行墜地,故人才不振,日就衰歇,陳君小圃,素景仰先生,既為先生建祠堂,又寄俸金囑余刻先生遺集,為刊印若干部,廣其傳,報存祠堂中…」
年底,他離黔抵京復命。供職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武英殿纂修,大考二等,記名過缺題奏。在史館時,先生纂修國史,負責清代早期(未入關前)史實及先朝諸臣列傳十餘篇,存國史館檔案中。張之洞入掌軍機,調閱檔案,得見先生所述各文,乃稱贊曰:「敘事明徹,頗具史才,滇英雋之士也。」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甲午戰事失敗,遂簽馬關條約。國人大憤,有會試舉人康有為、梁啓超聯絡各省舉子一千三百多人,給光緒皇帝上書請願,即「公車上書」,請變法以圖存。是年二月,禮部任陳榮昌為本科會試房考官,分校第十八房(廣東籍)考生,康、梁二人均參與會試。試前即密議,康、梁公車上書,概不取錄,凡試卷迥不同眾,言論犀利明燦者,即認為康梁之卷,各房考自行抽卷,不必上荐,即使上荐亦遏而不取,某房所荐者,即發還某房。先生在十八房中閱得一卷,觀其文辭,詳瞻古雅,疑即康梁之卷,格於密議之忌,先生未及示上。距發榜之日尚多,又再取此卷反復審閱,確認此實是國家通材,不忍棄此明珠於不顧。今國家急需人才,若不推荐此卷,則有失為國選材之職守。於是筱圃先生不顧禁忌,堅持原則,毅然將此卷加批補荐,上呈李總裁(文田)。總裁細察其文,亦疑是康梁之作,即批還十八房。先生又二次再保,仍被批還。筱圃先生細閱批辭,知總裁亦受其才華,致有「還君明珠淚雙垂」之句,筱圃先生越不忍棄。時距發榜還有十餘日,還可補荐,仍不顧密議之忌,硬荐強保,並擬就長批大膽舉荐,致函李總裁,慷慨陳詞。經筱圃先生再三保荐,李總裁無可推諉,終同意先生所請,同意中額。及至填榜拆密封,康有為試卷雖列首位,但僅得中進士第五。而筱圃先生三荐之卷仍被削落,至此才知此卷乃梁啓超之卷。先生為之義憤填膺,後始知梁卷之落第,實皆為閱卷大臣徐桐之主張,彼堅持原議,不允取中。故筱圃先生雖三次用心硬保,亦終無濟於事。在京會試各房考官都十分欽佩筱圃先生的膽識,認為如此長批硬荐為從來未有事。會試結束,中額門生來見者,同鄉來看視者,落第公車求書者,日給不暇。先生慧眼識才,三次犯諱荐賢之事,盛傳京師。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先生要求回雲南奉母,獲准啓程返鄉。七月出都,十二月抵家。途中所作詩四十四首,定名《南歸》。先生歸里,雲南的督撫大員,都久慕筱圃先生的道德文章。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六),雲南巡撫裕祥禮聘先生主講經正書院,繼之任山長(校長)。經正者,取經正民興之意,為滇中最高學府。校址在今翠湖之北市體委內,環境優美,有鷺飛魚躍之觀,沂水春風之勝,湖山清曠,是學子究讀佳所。自筱圃先生掌書院後,積極整飾院務,淳淳訓誨,在他的影響下,雲南學風為之一振。先生品端學富,為滇中文學巨子,時滇中舉貢生員,聞先生掌教書院,三迤之士,遠近來歸,以入院肄業為榮,故一時人才濟濟,俊義之士咸集。高才生如李坤、錢平階、宋嘉俊、秦光玉、袁嘉谷、熊廷權、張學智、陳度、李增、顧視高、王燦等先生,又如李根源、羅佩金、唐繼堯、顧品珍、殷承瓛等先生,均先後執經請益,文韜武略,極滇中一時之盛。滇中文教得以與中原媲美,經正書院實為啓蒙基地,而先生六年來之教誨,實起決定性作用。先生領導了雲南全省的文教事業,由於重視教育,雲南在辛亥革命後,已成為在全國舉足輕重的省分。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他親自草擬傳單,揭發法帝國主義分子私運軍火至昆明,密謀制造事端,侵略我國。先生的揭發激起民眾的義憤,焚燒教堂釀成教案,督撫屈服於法人壓力要追究責任,興大獄。筱圃先生據理力爭,義正嚴詞地表示:「毀譽是非,利害生死、榮昌一人擔之」,寧可殺他一人,絕不連累廣大民眾。於此,可知先生膽認之過人。
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為加速改革教育,創辦新學,雲南成立高等學堂。時遇林紹年(林則徐之孫)任雲南巡撫,聘陳榮昌擔任高等學堂總教習(校長)。時全省學務尚無學政機關,即以高等學堂兼辦全省學務事宜。課程除經史、地理、詞章外,有英文、算術(已接近現代教學科目)。考入學生多為廪生,亦有少數未入學之童生,供給伙食,每月大考一次,評定甲乙,擇優給獎金。教習有秦光玉、黃學瓊、李學仁等,亦曾聘日本人數名,任文科、理科、政法教習。學生中之優秀者,選派出國留學。是歲,先生提議選送學生錢良駿、李培元、吳錫忠(書法家)、劉昌明、李萼芬、由宗龍、邵光年、陳治恭、何鴻翼、李燮元十人赴日本,此為滇生出國留學之始。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先生議請林紹年中丞,又遣送六批留日學生,計一○三名。攻讀專業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師範、文學、商業,哲學、法律、醫學、冶金等,留學生日益增多,攻讀專業之廣是前所未有的。當時清廷學部議令各省設學務處,辦理全省學務,原由高等學堂兼辦之學務事宜,劃歸學務處辦理。處設總理、藩司,雲貴總督魏光燾照會先生兼任總參議。先生於滇省教育學務之規畫,高瞻遠矚傾心盡力。時先生赴越參觀法人醫院,占地極寬敞,皆為後方戰地醫院設施;又參觀其提督衙門(駐軍司令部)見其張掛之地圖,測繪精確,皆為吾滇關防要沖;且法人每年練兵數萬,法帝犯滇野心,昭然若揭。返滇後,先生立即上書總督,建議聘日本教習為我省練兵,同時派陸軍學生出洋學習軍事,學成後返滇轉練滇軍,以增強國防實力。當局懼怕請日人練兵,觸怒法人,未予表態。遂決定請派員留日之策,是年選送留日陸軍學生三十人,唐繼堯、李根源、葉荃、羅佩金等皆為人選,(這些人後來都是雲南陸軍講武學堂的骨幹)。
最值一提的是:是年(一九○三),筱圃先生任經正書院山長時之高足弟子袁嘉谷,經先生舉荐赴京參加經濟特科會試,一舉高中經濟特元,名列一等第一名(相當於狀元,實則比狀元更難),嘉谷曾受到慈禧太后兩度召見於仁壽殿的殊榮。雲南自置行省,從未出過狀元。袁嘉谷首次奪魁,原任雲貴總督魏光燾榜書「大魁天下」匾懸於昆明城南聚奎樓上,從此人稱此樓為「狀元樓」。光緒三十年(一九○四)八月,袁嘉谷奉諭赴日本考察學務、政務。時滇省赴日留學日漸增多,又被聘為雲南留日學生監督。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乙巳二月,筱圃先生受禮部批准,赴日本考察學政,並送生徒十二人前往留學,七月抵日本京都,得與袁嘉谷在異國相聚會。袁曾有詩云:「獨是骨嶙峋,蓬山證宿因;十年弟子誼,異國倍相親。」師生之情溢於言表。在日期間,先生得留日門人的引導翻譯,廣結日本政教界名士,如大偎重信(伯爵,早稻田大學的創始人)、嘉納治五郎(院長)長岡護美(子爵)等,故得以多方考察、參觀、討論、遊覽、酬酌。在日本的三個月中,先生每日則記述見聞及心得體會,寫成《乙巳東游日記》。東游日本使他眼界大開,回國之後更加注重教育的倡導與改革。先生探索研究日人的維新政治措施,從日本購置科學儀器回滇,並以高薪聘日人來雲南任教。為適應滇省的發展,先生在教育經費極為有限的情況下,憑著他在雲南軍政界的影響和威望,到處為教育奔走呼籲,終於在雲南增設了兩級師範學堂,創建了各種專科學校,購置大量圖書充實圖書館。
筱圃先生又奉詔再度出任貴州提學使。他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四月到任,母周氏也迎養在任所。他到任後,激於愛國愛鄉的義憤,曾將當時在貴州任巡撫的興祿參奏革職。興祿在雲南迤東道總辦洋務(外交)時,有意欺蒙,辜恩溺職,派民工修築鐵路,不給工資;又划滇緬邊界,崇洋媚外,喪失大片國土。僅此兩大罪狀,便使這位滿州大員被參革。筱圃先生不畏強權,當時他還是興祿的屬官,但仍直言敢諫,先生一時名聲大振。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他母親去世,回鄉丁憂。二月初由黔扶櫬回籍,月底抵昆,安葬守制。在昆丁憂期間,他被總督錫良聘任學務公所議長兼總辦滇蜀鐵路公司。對全省學務,先生盡力提倡贊助。次年(一九○八),先生又充任雲南自治總局局長,咨議局籌辦協理。後學部議令各省設省教育總會,公舉先生為會長,先生門人姚安由雲龍為副會長,門人普寧錢平階為駐會常務幹事,拔三迤基金產業,收租為常年經費。初成立於萬鐘街(此街今已不存)禁煙公所騰出之房屋,教育總會對推進全省教育的改進及改良民風民俗,開通民智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先生此間又為黃綜之《嗣音集》孤版重刊、王樂山《雲南備徵志》重刻作序,對滇文化倍加珍視推崇。是年,中越邊界不靖,法帝通匪滋事釀亂河口。繼而法人又以我兵邊境至巴龍槍斃法官打傷越兵為口實,處心積慮,蓄謀製造「巴龍之案」,進而犯我邊境。雖經我方委派道府縣要員會查交涉,而法帝仍一味狡賴。對此,先生極為憤慨,即與三迤士紳書《瀝陳滇法交涉情形奏稿》上奏,籲請外務部與法使交涉,務保國權而顧民命。
至宣統元年(一九○九)四月,先生守制二十七個月,服滿。此間他協助鄉里做了大量興辦地方實業和發展滇省文化教育的工作,這在三迤父老中是有口皆碑的。宣統二年(一九一○)朝廷任命他為山東提學使,赴濟南任職。山東乃孔子故鄉,文風夙著,朝廷素選品高學富之士充任學使。其時學部所定為學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先生則奏請頒行天下。此間先生所作詩定名為《尊孔集》。歲暮,先生門人畢近斗、嚴繼光考取留美預備科,入京肄業,特抵濟南竭見先生,先生留置度歲,並以守歲十章相勛。是年,先生又為滇省代擬《請款以興實業摺》,奏請撥款興辦滇省實業,以達救貧致富的目的。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嶺,各省嚮應。雲南新軍蔡鍔、李根源、李鴻祥等起義,全省光復,清廷被推翻。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他卸去山東提學使職務寓居上海,不再出任。山東、雲南再次電請他任職,他均一一嚴詞拒絕。晚年回鄉,先隱居安寧縣明夷河,此間作品以詞翰為多,收為《騷涕集》,取「離騷攬涕沾襟」之意。先生此時的思想,正處於新舊交替階段,有鬥爭也有矛盾。這從先生當年在《復山東周都督書》中可以看出,先生寫道:「既為清吏,不敢背朝,既生中土,不敢忘中國。苦清亡,則終身為民,不復言仕,今民國已成,是即榮昌終身為民,不復言仕之秋也。」先生先後居明夷河畔近七年,初不問世事,在鄉村租屋而居,後購得舊屋三椽,重加修葺,起樓三楹,題為「墨波樓」。先生靜心著述,或游於泉林山寺之中。時三迤耆宿,輯刻《雲南叢書》,聘先生為名譽總纂。對此,先生則表示極大的關注,成立大會時,親自由明夷河趕來省城參加。民國七年冬,先生在明夷河遭匪患,仍移居昆明舊廬,閉門著書,課讀子侄。先生決意不再做官,以賣文賣字為生計,自稱「困叟」。先生非常懷念明夷河陶淵明式的歸隱生活,曾有詩云:「明夷河畔舊山莊,翠柏如雲覆短牆,一道河流分左右,吾廬恰在水中央。」
然而,先生愛國愛鄉,服務桑梓,重視家鄉文化教育的崇高精神,始終是他一生的主流。對滇省的文教事業,他關懷備至,對雲南的教育發展,他傾心盡力。對滇省教育的商討,他絕對不會杜門謝客的。一九二二年,雲南國學專修館成立,筱圃先生又受聘為館長,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辦學。雖然他當時已屆六十三歲,但仍憚精竭慮,以培養人才,發揚祖國文化為職志。開學首致訓詞曰:「勤以讀書以立品,持之以有恒,凜之毋欺,夫如是必有成就」。以此勉勵鞭策學員。先生立德立言,躬行實踐,以身作則,開雲南近代教育的崇高風範。故出其門者,大抵為一時俊彥。在國學專修館就讀的同學前後近五百人,現大都相繼過世,分散在各地者都已年近古稀。據筆者所知,在美國的有朱之履醫學博士,在台灣的有經濟專家楊家麟(現任旅台雲南同鄉會理事長),在昆明的有楊存恭、周潤蒼、曹鍾瑜、李東平、周光顯、李冠西等先生。筱圃先生晚年除從事教育外,潛心著述,研究滇中金石碑板,或考釋,或題跋。他常為眾門人的著述作序,獎掖後學,不遺餘力。先生著述等身,已刊印的有:《虛齋文集》、《虛齋詩集》、《桐村駢文》、《滇詩拾遺》、《劍南詩鈔》、《乙巳東游日記》、《老易通》、《周訓》、等書。還未刊印的有:《騷涕集》、《硯食錄》、《虛齋詞》、《明夷子讀易記》、等書(本文只擇其主要著作列舉)這些書現在收藏在其家族中及圖書館內。
先生晚年最大的特點是皈依佛門,長齋唸佛,不遠游。早歲先生回鄉丁憂周太夫人時,住門人映空和尚(映空早年就讀經正書院)住持之曇華寺中。一守母墓,篡述周訓七篇(追述周太夫人言行教誨)。先生在曇華寺守孝時,映空法師常隨左右,以示師生之緣。夜則與映空悟坐,映空為先生講說佛經佛理,此乃先生領悟佛說之始。及至民國九年(一九二○),虛雲法師由大理雞足赴西山華亭寺擔任住持。雲師慕名訪先生,亦與先生講說佛法,相為契交。先生此後每與雲師互訪,必究討佛理,終日不倦。虛雲法師亦贈先生佛像佛物甚多,先生至此虔心阪依淨土。西山華亭寺經虛雲重修擴建,遂成滇中佛教聖地,大興佛法,佛徒朝山受戒者往來不絕。虛雲法師尤常邀先生至寺,供奉殷勤,每日除同參佛理外,雲師又嘗求先生書屏聯匾額數幅,懸之寺中,故先生之墨跡,在華亭寺頗多,皆住寺時所書。先生深究佛理,寄情於故鄉的名勝山水,此間我們看到他為各名勝所題的匾聯和書法作品,多是描寫佛門清淨無為,超脫自逸思想的。他在一首詞中寫道:「出家人,萬事閒休;脫離了玉鎖金鈎,從今不染紅塵垢,也不慕富貴王候,也不羨大廈高樓,茅庵草舍松藤構,淡黃齋勝似珍饈,蒲團柱杖相親厚。破納衣,賽過輕裘;孤雲野鶴隨吾後,游山岳參謁高流,訪諸賢四海雲游,乾坤到處仍依舊。笑世人,百計營謀,嘆今人空結冤仇,怎比我無煩無愁,不如我做個緇流,身心瀟灑無榮辱,古寺里自在優游,大丈夫及早回頭,向空門苦行堅修,彌陀佛系念心頭。數珠兒時時向西方,極樂瀛洲。」落款為:「夢生行者甲子(一九二四)夏五月十三日困叟」這正是先生當時思想,生活的真實寫照,脫俗高雅,不染紅塵,不慕官宦。他的這一行為,又大大地影嚮了他的門人弟子,這在當時或許是很有卓見的。他們雖沒有出家,但都成為有名的老居士。如袁嘉谷(屏山居士)、張學智(若園居士)、顧視高(漱石居士)、陳古逸(琴禪居士)、陳維庚(葉洲居士)等,他們都篤信佛理,皈依佛門。以上各位都精於書法,這足見禪與書法有著密切的聯係。
先生對鄉賢的供奉與尊崇,世人有口皆碑,但他決不是盲目推崇,時時可見他對鄉賢品評的尺度和分寸是相當嚴格的。周鍾岳倡建(景賢祠)於翠湖東百花莊落成,先生熱心參與並揮毫題寫聯對。先生臨終前曾為周鍾岳詩集寫序曰:「惺庵有夙慧,為童子時,穎悟異常,落筆驚人。」對周非常贊許。一九一七年五月,唐繼堯病卒,據傳先生曾挽聯云:「治滇無善政,護國有奇勛。」寥寥數語,便評定了唐繼堯一生的功過,非滇中學界泰斗宗師,無可下此定論(又有一說此聯為越藩所題,尚待詳考)。舊時昆明有名的「近日樓」(今昆明百貨大樓前街心花園處)系清康熙鬫禎大手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日戰事相繼爆發,人們僧恨日寇,曾有人建議換書「近日樓」匾額,一時爭論不休。最後還是筱圃先生出面加以制止說:「第一,不能望文生義;第二有誰寫的字比鬫東白的好,就換。」終無人敢換。
筱圃先生於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逝,享年七十六歲。先生原配呂夫人早先生三日而逝,年七十三歲,遂成老鶴齊飛之象,時人皆謂為福壽同歸。
先生一生,文章品德,稱譽於時,他平生敬仰魯公,跬步南園。近代雲南書法家中,最敬重、最推崇錢南園的就是陳榮昌。不惟錢、陳二公都是昆明人(祖籍皆為江蘇),就其書品和人品而言,也大體相似。《新纂雲南通志》有先生門人秦光玉為先生立傳曰:「先生慕錢南園之為人,自少小時(先生曾夢南園傳授筆法),即矢志學南園,卒之志同道合,先後一揆。南園督學楚南(湖南)以方正著稱;先生督學黔魯(貴州、山束),亦以嚴格教育,樹之標的稱著於世。南園劾魯撫國泰,正色立朝;先生亦劾黔撫興祿,不畏權勢。南園奉諱家居,疏濬昆明六河,功在鄉黨;先生旅居較久,掌書院、興學堂、輯叢書,濟儒嫠,辦團練,倡修鐵路,籌備自治,服務鄉梓,貢獻甚多。固不獨書法遒勁,詩文朴茂,是先生與南園有共同之點也。」先生病臥時,眾門人皆來探視,尤其是袁嘉谷、顧視高、秦光玉、吳崑、方樹梅諸先生,早年親聆教誨,師生情誼甚篤,故皆日夕環侍榻前,聘醫調藥,不忍須臾離去,直至先生歸道山。人殮之日,門人袁嘉谷、顧視高、周鍾岳、由雲龍等二、三十人,均環立靈床前,告別遺顏,依依難捨,皆痛哭失聲,不能自仰,家人則退立外圍,共視含殮,此情此景,皆出於至誠。先生既殮,經眾門人等齊議,組成治喪協事處,共策喪葬等事。先生門生故舊在南京者甚多,故同時又在南京籌設一治喪處,就地追悼,由先生門人李根源、張維翰、盧鑄、王燦等先生主其事。昆明治喪處為先生繪遺容一禎,由門人袁嘉谷題贊曰:「以顧黃之高節,兼張陸之心源。抗朱王之詩集,跨方姚之文篇。持衡如老紅豆,愛鄉如小停雲。教澤上邁乎潭西,道脈直接乎南園;集一代師儒之大成,延三迤文獻之薪傳。於噓吾師!人仰斗山,天賜大年。謹述古三不朽之義,贊一辭曰:立德、立功、立言。」
祭奠之日,士學各界,以及民眾不期而執番前來弔祭者,充塞門庭,數日不絕。出殯之日,市民自願執紼相送者逾萬人,行道為之阻塞。先生門人及家屬,共議葬先生於昆明西山之陰貓貓菁。下葬之日,門人會集者甚多,南京治喪處亦派代表前來會葬,極一時之盛。眾門人以先生處處奉南園為楷模,南園先生因筱圃而建專祠,而今祠宇巋然,廟宇清芬。弟子門人遂仿照清例私謐先生為「文貞」並將筱圃先生的牌位奉祀錢公一祠,改稱:「錢陳二公祠。」袁嘉谷直書先生墓碑曰:「前清誥封榮祿大夫私謚文貞顯考陳公諱榮昌之墓」,又為先生撰書神道碑立於墓道。
筱圃先生書法馳名全省,為雲南近代書法家之首。他在書法上博取專攻,從隸、楷、章、草、行;鍾、王、歐、褚、米、黃、越、董,無一不學,無一不精。但尤以錢南園為宗,乃其氣質所定。袁嘉谷曾說:「魯公之後;南園一人而已。南園之後,公一人而已。」這是很有見地的評價。他所書大楷嚴守南園法度,布局用筆更為嚴謹,應規入矩,其在滇所書碑刻甚多,如:《謁薛爾望墓文》、《唐繼堯墓志》、《護國門碑記》、《雲南大學會澤院碑銘》,昆明大觀樓、西山華亭寺均有他書寫的匾聯。我們可以看到他學錢書大楷的代表作,也可看到他以南園為基礎,摻以褚米筆意,寫出自己獨特風格的行書。他在晚年,則潛心研究漢、魏碑刻、特別是對昭通《孟孝琚碑》、陸良《爨龍顏碑》作過精確的考證。《孟孝琚碑》出土時,殘缺三分之一,每行開頭缺七個字。筱圃先生根據他自己的學識見解,結合現存文意,把《孟》碑每行開頭殘缺的七個字親自點校增補,這實在是對此碑考證的大貢獻。將來有幸找到《孟考琚碑》上截,能以合璧,則將反證筱圃先生潛心研究滇中碑版的結果。①筱圃先生稱《孟》碑為「雲南第一古石」,糾正了阮元稱《爨龍顏碑》為「雲南第一古石」的錯誤提法。筱圃先生的書法,學南園而得南園平整莊重之勢,以「顏錢」書體為精髓,旁通各家。是他正宗地繼承發展了「顏錢」書體的端莊平正,特別是繼南園之後,把「顏體」行書推向趨於完備的階段。我們從顏真卿到錢南園、陳榮昌可以清楚地看到顏書體系的師承關係和發展脈絡,這一點在雲南書法風格上顯得特別突出。筱圃先生在書法上的主張是:「書法筆筆要有來歷,有法度。這正是他一貫主張文章貴於博覽,書法也要貴在博見,不能流入淺薄,只有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才能創新的觀點。這與當今那種急功近利,沽名釣譽的所謂「書法家」是格格不入的。他認為歷來書家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取法高下的根本上,學書起點要高,即取法乎上,得之於中;取法乎中,得之於下。這是筱圃先生很有見地的看法。從筱圃先生的一生可以看出,只寫字不做學問是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書法家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書法只是讀書人的副業,這從中國書法史上可以得到印證。從筱圃先生留下來的大量書法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書法落款約分三個階段:授翰林前署陳榮昌,授翰之後署筱圃陳榮昌,告老還鄉後署困叟。
綜觀筱圃先生的一生,愛國愛鄉是他的主流。早在甲午海戰失利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時,他就不顧官卑職小,毅然上書力陳「賠款甚巨,何以籌償」,「台灣乃祖宗之基業,萬不可割讓」。這從他創作的大量憂國憂民的詩篇中,亦可窺見其愛國情感。筱圃先生有著雲南山地人剛毅堅定的性格,他曾幾上北京,赴貴州、山東任職,在當時交通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僅路途之遙,也是令一般內地人難以想像的,何況還要取得功名,那就不容易了。在赴京的旅途中,他經歷了車撞、船翻的各種磨難,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非同一般。過去有人對筱圃先生過於求全責備,認為他是前清遺老,不肯出任民國官職,反對辛亥革命。其實,筱圃先生對辛亥革命的態度並非一成不變,他能親書《護國門碑記》這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碑文,實屬一種順乎革命潮流的舉動。②他晚年辦學,服務桑梓,為發展雲南省教育事業,在培養人才,改革學制,轉變學風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先後擔任過經正書院山長(院長)、雲南高等學堂總教習(校長)、雲南國學專修館館長,雲南教育總會首屆會長。在主持雲南學務期間,根據雲南實際,創辦了一批專科學校,大大提高了雲南的教育水平。雲南從未有狀元;有之,則從筱圃先生執掌經正書院門人袁嘉谷始。③雲南從未有留學生;有之,乃從先生主講經正書院提議選派始。雲南之所以能以貧脊之省首倡護國討袁的義旗,則是筱圃先生留日門人所為。雲南在清末民初何以人材大振,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教育分不開的,而最關鍵的是筱圃先生畢生致力教育事業。是他引進了當時國內、國外的先進教育方法,始終使雲南的教育與全國保持一致,在很多方面還居於領先地位。所有這一切?都與近代雲南省文教界的一代宗師陳榮昌是分不開的。
注
①《書法散論》第五九頁(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版)
②《書法散論》第二三一頁。
③《「特元」比「狀元」更難》一九九二年九月三日《春城晚報》第三版。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4期;民國83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