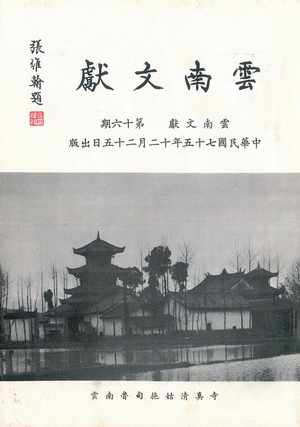滇中翰墨 筆驚風雨
作者/張誠
書法是我國具有悠久歷史的獨特藝術之花,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組成部份。我國書法,遺產豐富,從甲骨文發展到今天的文字已有三千多年,共百餘種書體。書法風格因書家所處的時代、地域的不同而千姿百態。
雲南書法有他自己的特色,在我國書法史上曾留下了光輝的篇章。本文想就自己的認識,談談雲南在全國有影響的著名碑刻和已經形成的書法傳統源流。
一、東漢『孟孝琚碑』
中國書法藝術能流傳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與碑刻有著密切的關係。雲南著名碑刻很多,年代最早的是『孟孝琚碑』,從文風、字體、碑文中所見官制等作全面考察,此碑為東漢,桓帝永壽二年或三年(西元一五六年至一五七年)所立。①『孟孝琚碑』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出土於昭通城南的白泥井,現存昭通第三中學。此碑出土後,即引起全國有關人士的注意,著名學者羅振玉、梁啟超、袁嘉谷等均先後考證論述。該碑出土時上端殘缺(約缺三分之一),現存殘高一‧三三米,寬○‧九六米,碑文共十五行,行殘存二十一字(從文意推斷,上應缺七字)隸書。碑文兩側有龍紋和虎紋,下有龜蛇紋,上原應有朱雀紋。據筆者見到一份清末民初昆明書法家陳榮昌先生收藏的『孟孝琚碑』拓本,極為罕見。筱圃先生根據他自己的學識和見解,結合現殘存文意,把『孟孝琚碑』每行開頭殘缺的七個字親自點校補。這實在是對此碑考證的大貢獻,將來有幸找到『孟孝琚碑』上截,能以合璧,則將反證筱圃先生潛心研究滇中碑板的結果。
『孟孝琚碑』與著名漢碑『禮器碑』同年立石,孟碑字體方正澤樸,就書法而言,能與『衡方碑陽『張遷碑』媲美,所謂:「滇南無漢碑」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日本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出版的『書道全集』也曾載有此碑拓片,足見它的影響甚廣。此碑的出土,又再一次證明了東漢時中華文化在雲南的傳播。如按年代論,『孟孝琚碑』是目前雲南唯一的一塊漢碑,真正「雲南第一古石」應是『孟孝琚碑』。可惜「孟碑」出土的時候,阮文達公(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年)已經去世了。
二、『爨寶子碑』卡『爨龍顏碑』
在民族史和書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應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的雲南『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根據碑身的大小,金石學家和書法家習慣把前者稱為「小爨」,後者稱為「大爨」。按書體演變的大體分類,一般地說「二爨」均為正書。「小爨」現存雲南曲靖一中碑亭內,「大爨」現存雲南陸良縣新建碑亭內。
『爨寶子碑』立於東晉義熙元年(西元四○五年),『鑿龍顏碑』立於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西元四五八年)。寶子碑早龍顏碑五十三年,至今已有一千五百餘年的歷史。東漢以來,在雲南東北部的少數民族統治集團是爨氏家族,爨寶子和爨龍顏就是其中的兩個成員,這兩塊碑就是這兩個奴隸主死後為他們而立的。『爨寶子碑』於清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出土,清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出任雲貴總督的金石考據學家阮元首先發現並肯定了『爨龍顏碑』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囿於見述,他稱之為「雲南第一古石」,當時,有派書家為了矯正「館閣體」軟媚庸俗的流弊,力主推崇北朝碑板,阮元在清代首倡「南帖北碑」,隨後包世臣鼓吹碑學,晚清康有為更是大力提倡尊碑。康說『爨龍顏碑』「雄強茂美」,繼而把龍顏碑列為「神品第一」。康氏對『爨寶子碑』更是推崇備至,他說:「寶子端樸若古佛之容,厚重古拙,體勢飛揚,用筆如長槍大戟,直來直往,沉著而痛快。」「當為正書古石第一本。」②「二爨」在書法藝術上與同時代的一些碑刻相比,確是居眾碑之首的。
由「二爨」的書體也可知當時中原文化對邊陲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少數民族中的上層人物許多人深受漢民族文化的熏陶,師法漢民族的文化藝術,「二爨」碑的撰寫,便是明證,但它又有其獨自的特點和風格。在研究文字書體演變的關系上,「小爨」是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由隸書過渡到楷書的典型實物,「大爨」時代稍後,但仍然保留了相當濃重的隸書意味。「小爨」用方筆,「大爨」用圓筆,兩者皆氣魄雄渾,結構多變,給人以一種壯美的感覺。「二爨」這種似隸非隸,似楷非楷的書體,即後人所稱的「魏碑體」,屬正書範疇。「二爨」具有高度的美學價值,在我國書法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最近香港『書譜』出版社出版的李濟琛舊藏『爨寶子碑』出土初拓本,這就說明了它在海外的影響。這兩塊著名碑刻出在雲南,這不能不說是雲南書法史上的光榮和驕傲。
三、清康熙年間書法家闞禎兆
闞禎兆,(一六四一│一七一○年)號東白,雲南通海人,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鄉舉,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二)中進士。詩文書法造詣很高,極有才氣,被當時雲南督府王繼文聘為幕友,(相當於現在秘書長職),故凡滇中所署王繼文撰書的碑刻,文章書法無不出於闞氏手筆。他師法二王及張芝、鐘繇。屬王書正宗,筆力雄健,豪放不拘,手跡遍及滇中名勝。
現通海秀山公園有其古柏行詩石刻,書文並美,為其平生佳作。用筆精妙,入羲獻堂奧,識者爭相榻摹,廣為流傳。由於才藝很高,故當時引起朝廷重視,闞氏古柏行一文傳至京都,皇帝見闞的文和字,甚為驚訝。讀其古柏行,恐其有野心,然又慕其才,特派大臣許弘勳前往通海訪之。許氏亦精書翰,其手迹在昆明不少,一見闞氏如同故友,並書贈闞氏對聯日:「如公才望能超古,近代夔龍孰比降。」兩人唱酬約半年而別,臨行前又贈一聯云:「戲綵埋輸在夫子則吾豈敢;浣花坦腹唯斯人其誰與歸。」觀此二聯,亦可想見闞氏在當時的才望影響非同一般。
闞禎兆在昆明留下的手迹,可惜現都不多了,原近日樓城樓(即今昆明有貨商店前噴水池)上「近日樓」三字匾額,即闞氏所書,金底藍字,每字約三尺六左右,氣勢雄健,巍然挺立。抗戰爆發,曾有人想換書其字,陳榮昌先生出面加以制止說:「第一不能望文生意,第二寫的字比闞東白的好,就換。」終無人敢換。筆者童年的時候,還曾見過「近日樓」三字的。另外一處是大北門的「望京樓」(即現北門街圓通動物園後門處),拆大北門時就不在了。當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胡小石先生就特別讚賞「望京樓」三字。此兩樓在清康雍年間都是昆明關防要地,非高手妙筆是不能書寫的。
四、剛正不阿字如其人的錢南園
錢澧:(一七四○│一七九五)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進士。性剛正不阿,做學問特別注重品德的修養,仰慕顏魯公的書法和人品,工詩文,善書,擅畫瘦馬。做過通政司副史,湖南學政,監察御史等職。為人耿正,對乾隆皇帝直言敢諫,不畏強暴,多次挺身而出,與貪官污吏,奸邪暴政作頑強的鬪爭。曾向貪污營私的和珅、畢源、國泰等權臣作過面對面的鬪爭,這種不畏權勢敢於鬪爭的精神,在當時的士大夫中還是少見的,清史稿評他:「素以直聲震天下」。③
他的書法,剛健雄厚,早年遍臨各家,學顏能升堂入室,得顏書神髓自成一家。他的字結體穩實,十分尊嚴,凜然不可侵犯。清道人李瑞清評他說:「南園先生學魯公而能自運,又無一筆無來歷,能令君謨(蔡襄)卻步,東坡(蘇東坡)失色,魯公後一人而已。」④這是很有見地的評述。由於他對顏書有深刻的理解,自己又有別於顏書的精臻造詣,開一代書風,凡他所到之處,學書者無不師承顏書,摹習錢字。他在湖南督學最久,墨蹟流傳湘中為多,這對湖南書法的顏書風範頗有影響。清代中葉,凡學顏書者都宗法南園,清代書家何紹基、翁同龢為了學其書法,四壁均懸掛南園墨迹,朝夕臨習皆取法南園,後來各自終成大書家,於是南園書名久而益大。世人有褒何貶錢的說法,此實屬偏頗之言。近人周鐘嶽題錢南園先生書詩云:「氣節文章一代宗,郎論筆力亦強雄。藝舟雙楫稱佳品,慎伯書評儻未公。」即認為包世臣、康有為對錢字的品評也未必公允。湖南更有甚者,多方搜尋南園手跡,竟連公文批函一類的只隻言片語均視為至寶。民國年間湖南譚延凱、譚澤凱兄弟專攻顏書,尤喜南園書法,不惜出重金求購百幅錢字,號稱「百錢堂」,湘人欽崇之致可見一斑。南園先生回居故里,對昆明地區的殿閣廟宇撰寫的匾額為數不少。他的墨跡在北京、湖南、昆明等地影響極大,散落在民間的也是可觀的,有相當部份還流傳到海外。
五、白族學者、書法家趙藩
雲南劍川白族學者書法家趙藩,宇介白、號樾材,晚號石禪,一八五一年生於劍川縣向湖村一九二七年卒於昆明,光緒乙亥舉人。趙藩才華出眾,雖科舉不得意,但仍腳踏實地,不圖虛名勤奮讀書。他的書法,宗法顏錢,得南園剛勁之氣,但又有別於錢書的氣勢和結構。現存昆明大觀樓孫髯翁長聯,即是他三十八歲時的手筆。官至臬台(相當於有高等決院院長職務),官聲很好,在川為官體察民情,整頓經濟,從教化入手,開辦學堂,稽查貪污中飽,人稱「趙菩薩」。辛亥革命前夕,他在四川做臬台,當時川督趙爾豐補殺密謀起義的革命黨人謝奉琦。趙出審案情,謝被捕後的英勇表現,使趙藩深受感動。他為救謝不果,竟至忿然辭官不做,這足見他的為人。⑤
趙藩在昆明為人書寫甚多,曾有「滿城皆趙字,無處不藩書」的稱譽。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內有一幅聞名中外的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這就是出任四川鹽茶道時趙藩撰寫的。勁健潭厚的顏體行書,文字樸素而不平庸,精辟而辨證,發人深思。要是沒有對四川民情和史實的深入透澈的理解,那是不可能在短短數語之中,把四川的史實和民情概括得如此周全。中外旅遊觀光的有識之士,無不對此楹聯給予高度的評價。辛亥革命後,趙藩能隨時勢而激進,投身護國起義,曾署名「滇南子趙藩」通電討袁,後又出任孫中山先生廣川護法軍政府交通部長。唐繼堯去世後,他送輓聯曰:「治滇無善政;護國有奇勛。」廖之數語,便評定了唐繼堯一生的功過,褒貶得當,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學者、書法家能有此雄略卓見,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見的。趙藩晚年著書立說,就聘為雲南省圖書博物館第一任館長,負責刊刻「雲南簡史」專門收集整理雲南先賢著作,對雲南文獻史料貢獻甚大。
六、書法、教育家陳榮昌
陳榮昌(一八六○│一九三五)字筱圃,號虛齋,晚年自號困叟,雲南昆明人。幼聰穎過人,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二十四歲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督學貴州,遷山東提學使,歸主講經正書院,曾赴日本考察教育。筱圃先生文章品德,稱譽於時,他平生敬仰魯公,蛙步南園。他後來做官參劾污吏貴州巡撫興祿,表彰鄉里先賢,提攜後進,協助治理地方公益,皆以南園為楷模,一步一趨,身體力行。曾用俸銀二千兩,倡建錢南園先生祠堂,即此一端,足見他對鄉先賢的尊崇。進而主持刊印『南園遺集』。他一生所學所為又多與南園先生一樣,南園善寫褚書,筱圃先生亦善褚,南園寫米,他亦寫米。他的書法,學南園而得南園平整莊重之勢,亦能以「顏錢」書體為精髓,旁通各家。他正宗並發展了「顏錢」書體的端莊平正,特別是繼南園之後,把「顏體」行書推向趨於完備的階段。他的書法當時馳名全省,為雲南書法家之首,他的學生袁嘉穀曾經說過:「魯公之後,南園人而已,南園之後,公一人而已。」這很精道地闡明了顏書系統的師承關係和發展脈絡。他在書法上的主張是:「書法筆之要有來歷,有法度。」這正是他一貫主張的文章貴於博覽,書法也要貴在博見,不能流入淺薄,只有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才能創新的觀點。他認為歷來書家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取法高下的根本上,這是筱圃先生很有見地的看法。
滇中有名氣的碑額匾聯,多為陳榮昌手筆,這因為他德高望重,門下生徒不少,多半是很有學識和作為的人,就中達官顯貴也不少,如唐繼堯、李根源、顧品珍等都是他的學生。他寫的重大碑文有:『護國門碑記』、『唐繼堯墓表』、『薛爾望先生祠堂碑』,西山「華亭寺」匾聯及雲南各名勝地均有他的手筆。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學人在京會考,京師盛傳梁啟超的考卷是他看的,筱圃先生一見梁卷,即認為是奇才,曾三次冒違推荐,終因朝廷嫉恨康梁新黨,不予錄用。
滿清推翻,筱圃先生不再出任官職,早年為官公正清廉,晚年清貧自號困叟。他的書法落款約分三個階段;授翰林前署陳榮昌,授翰之後署筱圃陳榮昌,告老還鄉後署困叟。清朝末年,筱圃先生目睹了朝廷的腐敗,外來強權的入侵,辛亥後的動蕩時局,他曾寫下了不少抵禦外辱的詩篇,也寄託了自己厭世的情緒。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他赴日考察學政,回國後著『乙己東遊日記』詳載日本新政措施,專購科學儀器回國並以高薪聘日人來雲南任教。但在當時政局動亂的中國,他的這一切振興國民,首倡教育的努力,都付之東流了。他只好篤信佛教,吃長素,不遠遊,偶爾去華亭寺虛雲和尚處小住數日,寄情於故鄉的名勝山水,此問我們看到他所題的匾聯和書法作品,多是描寫佛門清淨無為,超脫自逸思想的。脫俗而不染紅塵,這在當時或許是很有卓見的,筱圃先生的晚年是在教育、著述和賣字當中渡過的。他對大清的留戀,但他畢竟未反對推翻清廷的革命,對於前人,我們是不能苛求的。
七、清末狀元書家│袁嘉穀
袁嘉穀(一八七二│一九三七年),字樹五,別字澍圃,晚自號屏山居士,雲南石屏人,清末狀元。昆明拓東路跨於金汁河上,原有一座聚奎樓,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袁嘉穀經陳榮昌推荐到京應試,三十二歲考中經濟特科一等第一名(相當於狀元),雲貴總督魏午莊榜書「大魁天下」四字掛於聚奎樓上以誌紀念。其時科舉已廢,後人沿襲舊制,尊稱袁嘉穀為狀元,聚奎樓也從此更名叫狀元樓了。(此樓民國四十八年拓寬馬路時拆去)。袁嘉穀青年時在陳榮昌主辦的經正書院讀書,學業名列第一,為筱圃先生高足弟子。袁嘉穀先生考上「經濟特元」之後,光緒三十年(-九○四年)清廷派赴日本考察學政,兼任雲南留日學生監督,日本明治維新對他的思想影嚮很大。回國又調任浙江提學使兼布政使,歷任學部圖書編譯局局長等職,中國學校之有教科書,從嘉穀先生始。袁先生獎掖後進,提拔人才,在學部任職時,嚴復、王國維等均在其門下供職為先生所愛重。他一生興辦教育,整理經史,對地方文獻貢獻很大。
袁嘉穀先生善詩,他的詩作清新生動,特別注重字句的垂煉,在外辱內亂的滿清末年,他的不少詩篇洋盜著憂國憂民的情感。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詩作影響了他的書法造詣。袁嘉穀叔兄嘉猷嫻書法,嘉穀自幼從之學。他書工行楷,尤以行書見長,以王、歐為本,兼取褚、米,自創一格,以峭拔後秀稱勝,見者呼為袁家書。古人說:「書貴有書卷氣」,這對評價袁嘉穀的書法來說是比較確切的。雲南不少名勝區留有袁嘉穀先生的手筆,例如著名的相開庵祠對聯:「經籍之光,古書渾之灝灝爾;湖山在抱,佳氣郁之葱之然。」欣賞袁嘉穀先生的作品,一定要把書法和詩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品評。現存昆明翠湖公園「湖心亭」三字,就是是他(代唐繼堯書)的手筆,「湖心一予」書法蒼勁有力,筆酣墨暢,特別「心」字的處理安排獨具匠心。袁以飛快的筆勢完成了「湖」字,又飽沾了墨汁把沉重厚樸的「心」字的三筆一氣呵成,接著從容地完成了「亭」字。這是「袁家書」的代表作,識者無不留步觀賞,頗有暢情逸懷之感。袁嘉穀的書法在全國各地存留的不少,曾輯『當代名人書林』一冊,亦存有先生條幅一幀。對於別人求書,他幾乎是有求必應,即便是農民求書也是如此。縱觀袁嘉穀先生的書法,給人一租氣勢流暢的感覺,簡言之就是「氣貫」,往之不是寫字而是寫意,徜若你再仔細看一下「湖心亭」三字,就會更有這種感受。
八、對雲南書法的展望
古代雲南的碑刻很多,從漢到清,見於地方文獻著錄者約有大小碑刻二千一百一十九塊(明清碑佔九六%)。有的具有相當高的書法史料價值,有的則對研究雲南少數民族與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方面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史料。但從書法藝術史的角度來看,縱觀雲南眾多的碑刻,恐怕還得首推東漢的『孟孝琚碑』,雖然他出土較「二爨」晚,它畢竟是雲南現存僅有的一塊漢碑,名符其實的「雲南第一古石。」其次則是東晉、南北朝的『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二爨」碑文書法極佳,又是我國文字書體演變過程中由隸書過渡到楷書的典型實物,這尤以「小爨」最為突出。考證和研究這些著名碑刻,無疑會對今天書法藝術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認識和學習也同樣是對民族文化遺產的尊重,從而增強中華民族的自信心,雲南書法界在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今後在「孟碑」、「二爨」的考證研究方面是會有所成就的。
雲南的書家,自東漢「孟碑」的發現始,可以說是就有從事書法藝術活動的書法家了。雖然「孟碑」、「二爨」無從考證是誰書丹,正如眾多的漢碑無從留下書寫者姓名一樣。自漢始,雲南歷代均有碑刻亦有書家出現,但以清代書家最多,成就最甚,據方樹梅先生統計,清代能書善畫者省內外馳名的約二百多人。清代碑刻超過一千二百塊,幾乎佔所有滇碑一半以上。縱觀書法藝術的成就及影響,康、雍年間則推闞禎兆,其書體為王書系統,繼其餘緒的書家不乏其人。自乾隆南園始,顏書體系在雲南佔了很大的優勢。從南園到趙藩、陳榮昌,書家輩出,源遠流長,影響所及,早已超出了地區的範圍。如果你有興趣到昆明地區的名勝古迹走走,大凡著名的楹聯、匾額,幾乎都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與顏書有密切深厚的淵源關係。中國書法主要地是以王、顏兩大系統為主,這裏當然不是提倡學書都寫顏字,只是想就幾輩人已經形成的傳統風格作一些探討。我想,清末民初,在全國聲望很高的學者、書法家趙藩、陳榮昌、袁嘉穀(袁雖不寫顏書,但取法歐褚,異軍突起,別具一格),他們的存在,使得雲南書風大振,「顏書錢字」的摹寫學習蔚然成風,文章、書法、立品三者並重,逐步形成了滇中翰墨的傳統風格。這無疑有一種尊崇先賢,忠君的思想在支配,陳榮昌為錢南園建祠堂,趙藩為錢南園整理校刊遺集,袁嘉穀為錢南園故里豎碑,每逢南園生辰,幾位老者率眾總要祭祀一番的。
典型的書家、典型的代表書作,幾輩人不懈的努力,這自然形成了「顏書錢字」的傳統,這已經為事實所證明了。顏真卿、錢南園、趙藩、陳榮昌以至袁嘉穀,他們的書法之所以能廣泛地被人民所喜愛,除了他們高深的書法造詣之外,書品和人品能完美地統一在一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文章、書法、道德並重,這是中國傳統書法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清末民初,昆明的三位書法家(趙、陳、袁),他們所經歷的時代,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壯烈的社會變更,他們有的消極,也有的激進,或多或少他們都走過變法圖強,拯救中國的道路。由於時局的變動,連年內戰,民不聊生,貧窮落後的中國一蹶不振,再加上日寇入侵,山河破碎,他們尚未見到中國光明的前途,憂國憂民,終於在民國三十年代前後相繼去世了。然而他們所遺留下來「顏書錢字」的傳統風格,卻被後世所接受,因為這種風格具有一種中華民族特有的氣質。現在學習「顏書錢字」的不乏其人、傳統,特別是民族的傳統,是永遠不會被中斷的,因為他是深入民族脊髓的東西。
註:
① 汪寧生著『雲南考古』。
②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
③『物清史稿』。
④『南園行書集』清道人跋,商務版。
⑤ 吳玉章著『辛亥革命』九十一頁。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六期;民國75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