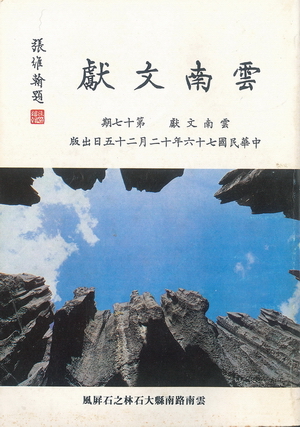遙慰異域袍澤
作者/趙懷志
七、八年前因中風而不良於行,友好們知道我是來自滇緬邊區,看到一本新出版的卓元相君所著「異域烽火續集」就買來送我,我接過手來很禮貌的翻了一下,告訴他:「謝謝你的好意,等我心情好一點的時候,慢慢的再看。」便把它置之高閣不去理它。因為當時寫這類文章的人,常憑一知半解的資料便捕風捉影的自吹自捧起來,把自己描述成為英雄好漢,其實值不得識者一笑,從此我就再也不看這一類的書籍了。最近因為兩次斷腿兩次住院開刀接骨,嘗盡了痛苦的滋味,每日枯坐無聊,不知不覺的走到了藏書的地方,一眼就看到了「異域烽火續集」還靜靜的站在那裡,心裡忽然想起,何不拿來看一看到底胡說些什麼?拿到座位上成去佈滿了灰塵的封面,細心的翻閱時才發現所敘述的事實,大都是毀家抒難發展而成的家鄉子弟兵團,如朱鴻原、李文煥、段希文等。自從盧漢叛變後,土共搶先接收各縣時,不願做奴隸的有識之士,便在各縣紛紛組織起反共游擊隊來,尤其是滇緬邊區的縣份,騰衝縣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盧漢沒有叛變前我們一群忠於黨國的人士就有了週密的應變計劃,待土共進城後就按照計劃一步一步的進行起來。李祖科還擔任著剿匪大隊長的職務,就推請他充任反共游擊隊的負責人,從速準備迎接未來的大難;投機份子正式宣佈投降後,游擊隊就照原訂計劃以滇西反共總指揮名稱相號召,附近各縣紛紛響應,據當時統計約有十多萬人參加,因為一時風聲太大,震驚了駐滇最高匪酋,乃派滇西匪軍陳庚,秘密從小路分頭進軍,入城後尚且不知,及至游擊隊開始集中時,匪軍一夜之間即從四面包圍起來,所幸發覺得早,且天黑路熟安全的向緬邊撤退,因為半年前我在盞西與李祖科做成最後決定後,即以政治難民身份到達緬甸的密支那從事與李彌將軍之間的聯絡工作。李祖科君早已被派為反共救國軍第四縱隊司令,我也被派為總部上校高參兼騰衝縣縣長,仍留在緬北聯絡。李軍退入緬境後,即到猛撤總部整訓,直到整訓完成另組第三軍政區以第四縱隊為基礎,再度北上駛展到大猛允時,我亦逃離政治難民特定區域到達木姐,遇上昔日初到緬甸同住一家旅社的難友林君,他告訴我他是先頭部隊,蒙他不忘舊誼,要我與他同住,隨同我一起去的人則被借用,編入他的隊伍中;以大吃小是發展史中的慣例,幸好我是不計小事的人,還能相安無事,只是做了他們幾天的臨時演員罷了。每日跟隨他們大街小巷中找尋獵物,以便達到他們發展的目的,但天怒人怨的公路搶劫消息不斷傳來,最後更有殺教士、劫財物的事件發生,再加上圍攻緬軍營地,嚴重違反了國際法,引起了世人的公憤,緬甸政府也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乃發動全國總動員,使用陸空聯合作戰追剿緬北游擊隊,另一方面也把確實的證據報到聯合國,說我國侵略,非立即全部撤出入侵的部隊不可!正在緬北從事發展的部隊便首當其衝,每日空中炸射,散處於各地為非作歹之輩,也不能不來集中於三軍區臨時總部。也許是上天要懲罰這些視人民如草芥的烏合之眾,使出「擒賊先擒王」的高招,所以在亂炮中一炮就擊斃了司令許季行,他雖然死了但留給人們的仍然是謙謙君子的風範,上天之所以如此做法,也許是戰亂中減少生命財產損失的唯一辦法,權其輕重也只有使用最後的徹手銷,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所有部隊又只好退回總部的老巢。
在撤退前那種亂糟糟的時候,不知為了什麼竟認識了朱鴻源部隊的唐春秀,是朱部最有力量的大隊長,野外求生經驗豐富,我倆一見如故,他要我同他們一起同行,他那一份誠懇的態度深探的打動了我的心,遂決定與他們同行,不知在什麼情形下還弄到了一匹瘦馬,必要時要騎上一小段路程,如果得不到唐君的邀約,問題還實在不少呢!自從到了唐部以後,他把我視同手足,凡是有關我的一切都為我安排的井井有條,一點也用不著我操心,還有他那幾位志同道合的死黨,也同樣的把我視同他們的一部份,遇到風景優美的草原,他把部隊停下來,讓馬兒飽餐,人兒飽玩以便舒展困乏身心的人,飽玩的唯一方法就是衛生麻將,一切用具都準備齊全,一有機會就可以坐下來玩,在牌友中有一位我們稱他為「老路子」的人,他的名字雖已記不清楚,但是他的聲音,笑貌卻還常常縈繞在腦際,因為只要有人連莊,問他如何下莊?他就說:「老路子。」意思就是照以往的習慣-樣,因此我們都叫他「老路子」而不名。行軍期間,唐君始終與我同行,路上看到可以吃的東西就採摘下來放在隨身鐫帶的提包裡,故每餐都有新鮮可口美味的野菜可吃。
爬山涉水,談天說地,野外求生都是我倆談話的資料。還有他那愛護我無微不至的真誠,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寫來歷歷如在眼前,尤其經過緬兵封鎖線的那一個晚上,唐君和另一個大漢始終在我身邊保護,到達危險地帶時,他倆一左一右挾持著我飛也以的離開危險地帶,那種捨身護友的偉大情操終身難以忘懷。還記得經過綠油油的草原時,我情不自禁的與唐君說:「像這樣優美而又肥沃的地方,假如我們能在此地建立一個王國,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與世無爭,不就成了桃花源了嗎?」我們就這樣的暫時把-切煩惱忘掉,愉快的過著我們漫長的流亡生活,相處越久越覺得親切,如果真能夠這樣永久相處下去,那該是多麼的好?可是快樂的時光是那麼容易的消逝,目的地│猛撤總部即在眼前,只好互道珍重而別!
回到總部後,各部隊有各自的防區,各人有各自的任務,與他們見面的機會就不容易了。我被安置在特派員辦公室聽候差遣,雖無事可做倒也清閒自在,每日無事就到田野民間閑遊,有好多同事會當地的語言,常與當地美麗大方,活潑多情的少女閒遊,我只有艷羨之份。這一異有廣闊的平原,善良的人民對游擊隊的到來也非常友善,用金錢與他們交易購買食米更受歡迎,所以初到才能那麼容易的建築營房、開辦學校、修築飛機場等,只可惜太快弄成尾大不調之勢再加上緬北所闖的禍受到國際間重視,國際壓力-天天的加重,看樣子是非撇離不可了,但政府打算只作象徵性的將老弱婦孺撤退;誰知風聲一經傳出,首先響應的竟是開創這個基地的首領,正所謂的「一聲霹雷天下響」一下就驚動了整個的基地,有勇無謀的粗人,實在是可惜而又可悲,他以為他曾經做過名震一時的游擊英雄,回到台灣有的是享用不盡的高官厚祿,何必再留在異域受苦呢?他這一宣佈政府是苦在心裡,表面上還要嘉許他的服從,就命令他率領第一梯次撤到台灣。王牌的第一梯次撤走後,雜牌不堪一擊的自然也想撤退,所以才有第二梯次的撤退,是以李祖科部隊及總部人員為主,本來李祖科事前也是猶豫不決,聽了我要為家鄉子弟前途著想的話所以才決定撤退。故第二次撤退時,我被派為第二批帶隊官,我把隊伍帶到接運我們的飛機前整齊隊伍向飛機上的青天白日國衣敬禮;有許多人興奮的落下淚來,每一個人都鍛投入母親懷抱的心情走上飛機,在藍天白雲的上空遨遊了八九個小時,其問經過共產國家領空:急劇的亂流使飛機劇升劇降,對這些初次遠航的人來說,其滋味實在不好受。到了松山機場下機時,我也曾受到曇花一現的盛大歡迎場面,也接受過影歌星的獻花,記者的攝影,短暫的時間一過,一輛輛的大卡車即開來,上了卡車到達臨時收容所聽候安置。把隊伍暫時命名為忠貞部隊,在待命期間我做了許多接運逃緬難胞來台的工作。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當初我離開密支那時,曾托人轉告李少青,告之我走後要他負責照顧難胞,並隨時與我連絡;雖在撤退時中斷了一段時日,但到台灣不久後就聯絡上,難胞們的信也越來越多,先把情真意切悲慘的信函送請在新生報服務的同鄉記者李文忠先生發表,再帶著大批求救資料專程前往陶府請求陶立委設法營救,因為我在省訓團受過訓是他的學生;擔任騰衝縣三民主義青年救國團分團主任時,又是他的部下,我所請求的事他不能不管,況且他又是一個熱心公益的人,對我所請求救助緬甸難胞的事,一口就答應下來設法解決。不久就把逃緬難胞源源不斷的接運來台,據事後統計,由我轉請陶委員設法接運來的約有兩千人以上。這種小人物也能做大事情的成就感受,一直溫暖在我的心中,如果有人問我這一輩子最得意的事是什麼?我會毫不考慮的說:是最先發動反共游擊組織與赤手空拳的接運逃緬難胞來台就業與就學。但有時候又深深的譴責自己,假如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開始選舉時,我不要以青年救國團分團主任及摯交好友的身份,盲目的逼迫著不被提名而高票當選的青年才俊熊建璽放棄當選的話,今天他還不是站在最高民意代表的殿堂上,為多災多難的難胞服務,又何須我「越俎代庖」呢?一念之差造成了終身的遺憾!
部隊整編,我被編到戰鬥第一團,因為都是校級軍官組成,所以人們又稱梅花兵團,倒也新奇別緻。接受六個月的步兵學校高級斑訓練畢業後國防部派人訪問各人的志願,我選擇了假退役,從此結束了半生的戎馬生涯。
退役後,過了一段吃不飽餓不死的艱困生活,又因家庭變故,非另找工作不可,不得不再請陶、楊兩位立法委員向輔導會趙主任委員推荐,才弄到一個叢山峻嶺人跡罕至的山地工作站去管理造林榮民的工作,這種工作不是一般人所願意做的,因為那個時候榮民留給人們的印象實在太壞了,最不講理的是不做工也要錢,我所接任的管理員,就是高高在上的住在平地,有機會還要揩上一點汕水,被榮民弟兄知道了就告到輔導會他只好走路,所姒我才有了這個就業的機會。我深知就業的機會得來不易,決定咬緊牙關拼到底,遂收拾行囊爬上高山與榮民弟兄共同生活,抱定以榮民的憂患為憂患,以榮民的喜樂為喜樂,一切以榮民的利益為優先,不到半年的時間,他們就把我視為親人一般,凡不如意或難處理的事,只須要經過我的排解都會化為烏有,最後落得一個「土地公」的渾號,就為了這個渾號,犧牲了我整個的後半生。退休後本打算到泰北一行,再看一看久別的老朋友斂一敘往日的情誼,誰知天妒有心人,高血壓病魔不請自來,中風使我癱瘓,一切的計劃又落了空!
不良於行的苦惱就是每日枯坐無聊,不得不胡思亂想,終於讓我找出了最好的方法與答案,就是要使我們這些飽經戰亂而始終忠於國家的雲南老人,對國家民族做過些什麼特殊的貢獻?對後輩青年有些什麼期許?對未來的新情勢應如何的去迎接?就憑這多少年來的經驗,用各位的生花妙筆把一些最成功的事蹟記述出來,在雲南文獻上發表,以便後輩們效法。我現在就先來發起一個,·讓雲南地區選出來的最高民意代表,代表在台的選民,到泰北去看一看那裡的難胞情形,並慰問他們。我相信對這些代表雲南地區的最高民意代表來說,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因為你們在法統的保障下,免除了競選的煩惱,除了定期性的會議外,有的是時間,出入境又是那麼的方便,為何不自動的組團去看一看處在水深火熱中十萬以上難胞的實際情形?也許那是永遠解決不了的老問題,去了也沒有用,如果真有這樣的想法,那就太可悲了!自從泰北有難胞以來,具有名望的鄉人,有誰關心過?演藝人員發動的送炭去泰北又有誰去參加過?難道我們的熱血到了台灣以後也會變涼了嗎?在這裡我還要提供你們一些泰北難胞的資料:中華日報於七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副刊上刊載著有關泰北難胞的報導值得鄉人們的重視,消息的來源是這樣的:「深入泰北難民村達六次之多並發動救助難胞的陳友旺教授,在歡迎中國文藝訪問團在泰國宴會席上指出,他先後六次和友人深入難民村,明天將作第七次的訪問。那裡有數萬名的難胞,他們一方面要抵禦共黨的政擊,方面又要防患毒蛇猛獸的侵襲,飢寒交迫苦不堪言,因此發起救助難民運動,認養一人每月約需四百元,這-運動各界反應熟烈,一時風起雲湧,大家紛紛伸出援手。希望作家們為文報導以激發更大的迦響。」四月二十六日青年日報記者章紹安先生泰北之行所寫:「泰北唐窩││一個需要關愛的地方」從六天的連續報導中可以看出在那裡難胞的生活是多麼的艱困?尤其是有關李文煥將軍的報導,李將軍是雲南反共救國軍第三軍的軍長,始終沒有離開過邊區一步。我政府宣佈撤軍時,糧餉即告斷絕,一萬多人的生活就完全靠他一個人來也稽,一個月一千多包大米的供應,數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急病送醫,急難救助等都不能不理,等於是一個上萬人的大家庭;李將軍以家長的身份,負擔著這「供」「養」的重擔,以一人之力為萬人的生活而奔走,一毫無怨言。精祈何其偉大?以上所述,不過是李將軍部份,其他還有段希文等部份,更是繁雜而眾多,像這樣多的忠貞難胞,一直就在邊區為自由世界保衛著泰國這一張骨牌不讓它倒下去,才保全了整個東南亞,也保全了台灣,功在自由世界,而其結果竟落得如此的下場,別的人可以見利而忘義,吃飽喝足後可以不管,而我們是血肉相連的鄉親,也能長期坐視不管嗎?但願我這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升斗小民所提出來的呼籲,不要等閒視之!國家有的是用不完的錢,正在愁著無法消化,就請你們去宣慰他們的時候詳細的考查一下,要如何的做才不會白虛此行,才能徹底的解決他們的問題?如果需要資金,就告訴那邊的重要可靠的負責人,來辦理創業貸款手續;關於教育方面的問題,因限於泰化規定,在泰不能正式教授中文,但也應該派人去開辦小型的補習班,最好是爭取救總在台設立一個泰北難民子弟學校,從小就接受祖國的文化教育,將來才會是最可靠的反共救國鬥士,因為他們一出生下來,所看、所聽、所接觸到的就是一些反共救國的聲音與事蹟,息息相關如同生命的一部份。除此之外就是衣、食、住、行的問題,假如能使他們從小就回到祖國的懷抱,過著與台灣兒童一樣的學習環境和讀書生活,他們就會把這裡視為自己的家,絕對不會做出「數典忘祖」的事來,我與留在那裡的大多數家長們,有深厚誠摯的友誼,所以有特別關愛他們的必要,趁著還能寫幾個字的時候,把心裡所要說的話寫了出來,也算是盡到了遙慰異域袍澤的一點心意。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七期;民國76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