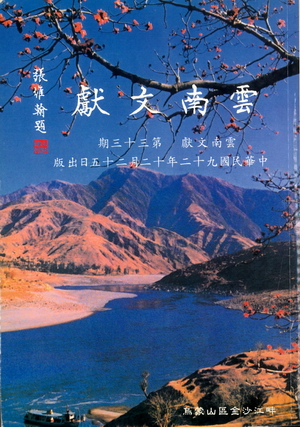十九世紀末葉滇越邊界變遷淺析
蔣家驊
越南在中國元明清時期,即十九世紀末葉以前,與中國為藩邦關係。所謂藩邦關係,則不同於近代史上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西方國家所形成的殖民地、附屬國、保護國的關係。中國在中世紀時期所形成的藩邦關係,在其藩邦的內政上,其國王或酋長享有其極大的自主權。中國朝廷放任不與過問。只是藩邦王位更迭或繼承,必須得到中國朝廷冊封即任命。這樣,國王才上對朝廷,下對其地方人民取得合法地位。管理其國內事務,也才具有聲譽和威望。同時,藩邦國王在一定時期內,也須向中國朝廷繳納貢賦,即進京述職。這是藩邦國王對中國朝廷應該履行的唯一義務。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封建特殊關係。即使彼此之間有邊界糾紛,亦不是中國朝廷與藩邦國王的爭執,而是兩方的土司官之間的利益爭執。能即時調解與否,關係兩方的邊防與商務利益不大。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法國殖民者併吞了越南,國際關係起了根本變化。中法滇越邊界糾紛,也變得愈形複雜了。這時期的邊界糾紛已不是雙方土司官之間的問題,而是中法兩大國之間的領土、商務的外交問題了。法國殖民者吞併越南後,對我國兩廣及西南各省,要求開辟商埠,擴大貿易,激劇推行侵略擴張政策。使我國主權,在政治上、經濟上受到極大損失。而國防問題亦日趨嚴重。因此,當中法戰爭甫告結束,公元一八八五年,中方軍機大臣李鴻章與法方全權特使巴特諾在天津簽訂《中法條約》(注1)其中第三條議定,本條約畫押後六個月期限內,會勘中法滇越邊界。滇越邊界由東廣南府到西臨安府共長一千餘百公里。雙方達成協議分五段進行會勘。這就是中法滇越邊界,會勘交涉變遷之始。我們在以下分三部分討論。
一、今馬關、麻栗坡沿邊的變遷
歷史文獻記載,唐代即南詔時期的行政管轄區域,南至今越南北圻一帶,賭咒河及鉛廠小河都屬於南詔。元代平定雲南後,在今馬關縣的八寨設置阿焚萬戶府。今文山、馬關、麻栗坡、富寧以及今越南境內的賭咒河流域以北一帶均在其管轄之內。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廢阿僰萬戶府,改置安南長官司,但其轄區仍舊。清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平定土官王朔及祿昌賢等的叛亂,於是,改土歸流,廢安南長官司,設置開化府。以今文山縣城為府治。《清一統志》卷三七四載:「賭咒河在文山縣南二百四十里,與交阯交界」。《舊志》「係蠻夷為誓,各不相侵之處」。賭咒河之名即由此時,此義而得。可見,康熙初年,賭咒河仍然是中國與交陸的分界線。清政府尚在這裡設置巡檢司,征派田賦,為行政管轄所達到的地方。並非藩邦安南管轄之地,亦非甌脫之地。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安南國王黎維正不顧這個地區的歷史傳統,和政治隸屬關係,妄言原為安南故地,係被開化府土司侵佔,請求朝廷飭令該土司退還。康熙帝據雲南巡撫石文晟奏,這一地區歷來向開化府納糧,非安南之地。……遂即移文斥責黎維正「妄言生事」。而黎認罪誠服,不敢爭辯。開化土司與安南國王邊界之爭,暫告平息。到了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這個地區又發生安南國王與安南長官司土目邊界爭執。這時雲南總督高其倬向朝廷奏請:清查雲南與安南地界。並云:「開化府白馬訊外四十里至鉛廠山下小河。內有逢春里六寨,冊載秋糧十二擔零,於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入於交阯。……自開化府文山縣南二百四十里,至賭咒河。……至鉛廠山下小河亦止一百六十里。鉛廠山下小河以外,尚有八十里,亦係雲南舊境。雖失之勝朝,但封疆所係,亦請一併清查。(注3)」由此可見,這一帶地方,歷來就屬於中國,只是明代中葉,鉛廠山下小河以外八十里地,及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逢春里六寨,曾先後被安南國王侵佔。關於這次邊界之爭,由於當時中越兩國還有宗主國與藩屬的特殊關係,因此,清朝廷即以「安南既列藩封,尺土莫非吾土」的傳統封建觀念,將白馬訊及小賭咒河以外一百二十里縱深地帶償給安南國王。
到了一八八六年,中法雙方會勘邊界時,越南已淪為法國殖民者的保護國。中越的宗主藩邦關係已不存在。當年清朝廷施行「牽遠之道」,曾將大片國土恩賜藩邦,這時理應收回。《清史稿‧邦交志》載:「周德潤與狄隆各按地圖校改,互有爭執。而於大小賭咒河;猛梭、猛賴兩段爭執尤力。」周德潤為會勘中越邊界中方欽差大臣;狄隆為法方全權特使。可見這時的周德潤尚有決心爭回失地。然而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新約》,李鴻章未繼朝廷及軍機大臣們認真研究,竟貿然草率簽字,致使中國損失甚大。在邊界問題上,也鑄成大錯。勘界的大員們,縱使舌乾唇焦,力圖挽回,但已無能為力。
中法雙方依據《中法新約》,周德潤與狄隆議訂會勘辦法八條,其中說明:「這次所勘之界,即是現行之界」。所謂現行之界,就是指當時中越雙方行政管轄所控制的地方。這就否決了邊界問題上的「歷史」這一因素。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以前,中越之間,具有久遠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歷史關係。會勘邊界,以實際控制線為根據。按地圖定界。忽視歷史因素。這都是極端荒謬的。中越交界一帶,眾山起伏,層巒疊幛。山脈河流,分水嶺等等,未經實地訪問、考察、勘測。沒有對地理形勢徹底摸清楚的時候,那麼,行政管轄所達到的地方,也是一句含混模糊之辭。便於老奸計猾的法殖民者所利用。
這次會勘邊界,法國方面的思想意圖,是以商務利益為主,領土考慮則在其次。而中國的思考意圖是以邊防要隘為重,而商務考慮則在其次。中國儘管思想意圖如此,但其後果不止商務問題損失甚大,而在防務問題上,亦毫無所得。
滇越沿邊界線一千多公里,從何地開始會勘,也是一個爭執的問題。法國的意圖重在商務。它的謀略詭計是:如果,商務得到中方的便宜,則界務可稍作讓步。所以要求先勘老街即河口到龍膊河及龍膊河鄰近地方。這是分五段會勘中的第三段。而中國的立場重在防務,則要求先勘爭議最大的地方。如白馬關及大小賭咒河以南一帶。這是分五段會勘中的第二段。從何地開始會勘,雖然是個技術問題,但實質上亦含有策略意義。雙方遂為之爭議不決,會勘工作延耽數月之久。後來,清政府採取妥協立場,同意法方要求。按《中法新約》第五款議訂:「保勝(今老街)以上,諒山以北通商。中國設關,法國設領事。北圻亦可駐中國領事。」法國根據這條款,決定調查蒙自是否符合設埠的條件。並決定入滇通商,以那條道路為宜。因此,堅持先會勘老街到龍膊河及其鄰近地方。會勘邊界的程序,關係界務、商務的全局很大。清政府不諳法方意圖,貿然對法妥協,遂致後來在各段邊界的會勘中,喪失主權不少。
中法戰爭結束雖已年餘,而法國政府在越南北圻的控制力量還很藩弱。北圻一帶尚有反法殖民者的「黑旗軍」餘部。該餘部得到中越沿邊各族人民的支援,經常騷擾法國殖民者的後方。有些地區仍為黑旗軍所控制。北圻地方,及其邊界沿線並不平靖。這又給雙方在會勘邊界的根據上提出了一個課題,即「會勘定界,或是就圖定界」。狄隆對邊界一帶的安全問題,很有戒心,早有就圖定界的思想。而中方則力主會勘定界。因為會勘定界則須進行實地考察,訪問當地証人。藉此可以摸清楚邊界問題上的歷史沿革,以及現實地理背景,行政管轄上的隸屬關係。清朝廷堅持會勘定界原則是正確的。但雙方正在會商這一課題的緊要關頭,黑旗軍散勇出於愛國及反法殖民主義的激情,在省蘭地區殺死法國勘界引路弁兵數名。於是,引起雙方糾紛,停止會商數日。法方以此為口實,力主就圖定界。法國政府也以此項要求,照會中國政府,請以就圖定界。並申言若畫定有不符合者,俟沿邊社會安靖後,再行補勘。中國政府考慮當時會勘的實際困難,只好放棄自己的既定的勘界原則,遷就了法方的要求。
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法國殖民者曾屢次派遣特工人員潛入中越沿邊一帶,進行勘測活動,如繪製地圖,搜集礦產資源,勘測航運河道。以及邊界兩側的民族分布,民情風俗文化等等資料。對中越沿邊一帶的了解,不在中國官員之下。因此,法方之所以提出就圖定界,它是胸有成竹。遠在一八六五年,法國交陸阯那總督就派了德‧拉格及弗朗西安業組織探測隊,於一八六六年六月,從西貢出發,沿湄公河(在中國境內稱瀾滄江)北上,直達大理。完成了最重要的探卜測工作。並全面地勘探了湄公河兩岸的土地(注4)。可是,這次探測的結果,法國殖民者知道了湄公河做為進入雲南的航線是不適宜的。因為,湄公河水流湍激,河谷深狹,不能航行。遂放棄利用水路進入雲南的幻想。
這時,湖廣總督李瀚章鎮壓農民起義,購買法國軍火,與法國軍火商人杜布益相熟悉。而雲南巡撫岑毓英這時因鎮壓回民起義,須購買法、比、德各國的武器,遂電請李瀚章轉告杜布益來滇,商洽軍火購買事宜。杜布益到雲南後,得岑毓英允許,可由紅河運軍火經老街進入雲南。杜布益及法殖民者始知越南紅河一線為越南進入雲南的歷史通道。這就給後來滇越鐵路線走向,奠定了基礎。
一八八八年,法國殖民者又派遣巴維率領一百餘人的所謂探測隊,從老撾沿湄公河流域進入黑水河地區,進行勘查並繪製地圖。可見,法國殖民者對中越沿邊一帶曾作了多年的侵略活動。關於這一帶的物產資源、山脈、河流、地貌、分水嶺已瞭如指掌。就圖定界,不利中國。
清政府在商務問題上,同意了法方恭思當之要求,修訂《滇越邊界通商約》。在商務上損失利益也大。「法殖民者的商務苟可通融,界務亦可稍讓」的諾言,不過欺人之談而已。
二、猛蚌、猛賴、猛梭之喪失
中法滇越邊界會勘伊始,雙方達成協議,分五段進行。本段是協議中的第五段。今雲南把邊江下游,名為李仙江。流入越南境內名黑江或黑河。又流經今越南萊州以下,名為黑水。今綠春縣北有水名藤條江,東南流入越南境折而南流,名為南那河。到萊州城下與黑江匯合,並流入黑水河,經紅河三角洲入海。我們在各種地方文獻中常見到的猛蚌、猛賴、猛梭、猛刺、猛丁、猛弄等所謂六猛,就是分布在黑江以北,藤條江沿岸一帶。為當時雲南省南疆的六個重鎮。這六猛之地,自元代以來,皆設置寧遠州管轄。州治在猛賴。猛賴即萊州。今猛蚌、猛賴、猛梭在越南境內。這是一八八五年,中法依據《中法續議界務專條》畫出雲南境外的。
這一帶地方,山高箐深,地勢險峻,為雲南天然屏障。元明清均相承於此設置土司治理。其政治隸屬關係,皆直接受臨安府管轄。其邊界線,在此次勘界以前,明清以來,未曾變更。史籍嘗載:「臨安府南境與安南;以黑江為界(注5)」。猛蚌、猛賴、猛梭三地,皆在黑江之北,自然在臨安府管轄之內。
猛蚌等三土司地,當中法會勘邊界時,為什麼亦有邊界糾紛的懸案呢?現在追述一下歷史。當十九世紀初葉,安南所屬的萊州土官刀姓不安本分,狂暴好事,當向猛蚌等三土司敲詐勒索,霸佔搶劫。三土司不堪其侵擾,甘受萊州土官指使,淪為附屬。然三土司仍向臨安府繳納田賦,此後不久,雲南值回民起義,全省動亂,督、撫、總兵皆無暇過問,致使三土司長期淪為萊州刀姓土司附庸。這就是三猛邊界懸案之由來。
中法此次會勘並亟待解決的邊界懸案,就是第一段即三蓬之地;第二段的大小賭咒河流域,以及現在討論的第五段三猛之地。在全段勘界畫界過程中,要以第二段第五段問題最多,爭執最激烈,而中國損失亦大。其所以爭執激烈,扶方拒不承認歷史隸屬關係。當會勘三猛之地,法殖民者知道三猛之地對滇越雙方的戰略上國防上的地地位。當然要否定三猛的歷史因素。堅持現行的實際控制。否則法方就沒有理由,把三猛地區踞為己有。由於清朝廷腐朽昏嘖,勘界大臣之無能,下級官員知識短淺,以致定界畫界,著著失敗。會勘協議結果,將大小賭咒河地的猛峒三村畫歸中國,將三猛之地畫歸法方。自我安慰曰「互換」。以我國領土兌換我國領土,而各級勘界大員不據理力爭,竟然同意法方要求,豈非怪事。
廣南府三蓬之地(今富寧田蓬鎮一帶)歸還中國,這是理所當然。因廣南土司官與越南保樂州土司官互為婚嫁。廣南土司官嫁女將三蓬之地陪送給保樂州土司官。用土地陪嫁,清朝廷是不准許的。但法使只同意歸還上蓬之田蓬街及其所屬之八個寨子,只是三蓬之一小部分。而勘界之欽差大員卻沾沾自喜,以為「拓地」縱深三十餘里。更不可解者,三蓬民眾眷戀祖國,不願為法越蠻邦的子民,群起呼籲,向中方官府大員請願,卻受到鎮壓。廣南府府官興祿的一段話可見其本質。他說;「卑府到界之初,風聞越南之三蓬民人麋集,相率鼓動。意欲抗令,要求法員將三蓬地方畫入中國。若果如此,不獨阻撓界務,且恐變生臨時,關係誠非淺鮮。當即密派隨員,授以機宜,前趨安撫。幸不辱命,一律解散,聲色無聞」。此為地方官吏,會勘邊界,不唯不支持邊民要求,而且甘心賣國求榮。更不可原諒的為總署(注6)大臣奏云:「臣等通盤熟計,因彼讓界務,我亦允以商務稍為通融。設關本《津約》所有。減稅與《俄約》略同。土藥出口係彼此得利之事。而前後展拓新界不下千餘里。皆該督、該大臣等所稱,險要膏腴之地。又將未經批准之商務;爭執不決之界務,一律清結,仍尚不為失算(注7)」。猛峒三村及猛峒山,原為中國領土,後被越南侵佔,今以《中法續議界務專條》收回,正是「物歸原主」。與其說「展拓新界」,不如說喪失歸界。失去三猛之地,收回三村一山,豈能算做不下千餘里。總署大臣視封疆邊土如草芥;以界務為國際交涉之末節。其自我安慰,欺騙輿情,亦非偶然。清朝政府在界務上之失敗,當時,中國官場輿論,亦不乏正義之言。如駐英國欽差大臣薛福成批評總署云:「竊維數十年,西洋諸國競知中國幅圓遼闊,又有不爭遠土之名,一遇界務,鮮有不為耽耽之視,……。中國素守好大喜功之戒,避開疆土生事之嫌。得之則曰猶獲石田,失之則曰不勤遠略。顧石田棄,而腴壤危矣。遠略弛,而近憂迫矣。我視為荒土而讓之與彼,一經營則荒土化為奧區,以奪我利柄。我見為甌脫而忽之。彼一布置則甌脫變為重鎮,以倡我岩疆。伺間蹈瑕,永無底止。歲復日削,後患何窮。」深中肯綮,可謂明智之言。然清朝廷軍機大臣,皆腐化昏瞶,不予重視。
此次中法畫界,將臨安府所轄之猛蚌、猛賴、猛梭三土司地畫歸法越。則臨安府南境,僅抵廣思河。南辣比河流域畫歸法越。凡水流入南辣比之地一併歸法。廣思河流域畫歸中國,即今中國南疆現行管轄之邊界。
三、猛烏、烏得之割讓
中法會勘邊界,協議分五段進行,上文已有略述。一八九三年,六月,法方玩弄卑劣技倆,始將普洱府所屬,歷來無界務糾紛的猛烏、烏得列為第六段會勘。雙方會勘前五段邊界,不涉及其他第三方面的多國國際關係。也與鄰邦英緬的界務也無關。而現在將要討論的猛烏、烏得問題,就與前五段大不相同。它與第三國英國有外交直接關係。
當一八八六年,中法開始會勘邊界時,雙方達成協議,所勘邊界的地理位置,東起廣南府的普梅河,西至臨安府的黑江止。黑江與九龍江(即瀾滄江)相距甚遠。後來法越強加第六段,這就與中國的車里、猛連接壞。自然引起中英國際關係。當黑江以東五段界務,行將會勘完畢時,為什麼法方提出第六段界務?這時,印度支那的國際形勢發生變化。法國與暹國(泰國)戰爭,結果暹羅失敗,雙方簽訂了《法暹協訂》,暹羅承認湄公河東岸地方讓給法國。法國殖民者為了鞏固在印度支那的既得侵略果實,同時,亦為了防止英殖民者的勢力向印度支那滲透。因此,對於中、法、英三國交界的這一地區,在法殖民者看來,就有必要會勘,明確邊界位置,以便設置邊防重鎮。這一地區,自元明清以來,就是中國車界宣慰司(今西雙版納)的轄區。歷來沒有邊界爭議懸案,也沒有不清楚之處。不能與黑江以東各段相提並論。中國勘界委員,對於法方勘界代表的這種毫無根據的要求,曾以「此次勘界,不能越總署所頒五圖地面之外」,據理拒絕。然而,清朝廷此時受朝鮮問題的困擾,全力對付與日本的交涉。對於法國政府的這一要求,遂採取妥協立場。並通知中國勘界委員云:「法使既奉彼國命令,明求利益,其萬難依行者,自應拒絕。其可以遷就者,不得不稍為變通。庶足以固邦交,而敦睦誼(注8)」。朝廷的對策如此。於是,中方勘界委員同意五段之外,補勘第六段。為什麼猛烏、烏得是這段邊界會勘中心議題呢?
今老撾豐沙里以北,南烏江上游,就是猛烏、烏得地區。這一地區,在元明清時期,為東里宣慰司所轄的猛烏、烏得兩土司地方。雍正年間,改土司歸流,設普洱府、寧洱縣。遂將猛烏、烏得兩土司地方,從車里宣慰司析出,撥歸寧洱縣管轄。兩土司官銜為「土把總」。定有上繳其錢糧數。頒發有印冊。各種《雲南通志》及《清朝續文獻通考》都有記載。其邊界四至清楚。猛烏縱橫八十餘里。烏得縱橫二百餘里。其地距思茅六茶山僅二百里。盛產茶葉,為普洱茶之故鄉。有磨掃、磨旺等鹽井,產食豐旺盛。在中法會勘滇越邊界以前,無論歷史傳統關係,或實際行政隸屬關係,兩土司都是中國府一級,及縣一級行政管理所達到的地方。這時,法方勘界代表巴威提出會勘這段邊界,實屬荒謬。而巴威既協議、條約在先,又無法理上的依據。他自己感到理屈辭窮,遂使用極其卑劣的欺騙手段。自繪地圖,將猛烏、烏得畫入越南。並以封官許願巧言誘惑中方勘界委員黎肇元會印。黎初則據理爭論,堅決拒絕會印。但巴威此時聲色俱厲,怒氣沖沖。黎恐會勘破裂,影響界務大局。於是,立場動搖,同意會印。殊不知巴威其人極為陰險,會印得意之後,即卷圖返回暹羅,並通報法國政府,以此圖為此段界務交涉之口實。後經清朝廷力爭,不能以此圖為據。無奈法方以勘界委員會印為借口,已無可挽回。黎肇元經雲貴總督奏參,革職留用。論者以為猛烏、烏得之喪失,實由黎肇元之昏庸貪鄙所致。然而追本溯源,喪權辱國者,非黎個人,而總署大員,亦不可辭其咎。當此不久之前,法英簽訂《密約》,法暹簽訂《協訂》英國、暹羅都承認湄公河東岸之地讓給法越。而湄公河東岸之地,包含有中國領土。清政府對此《密約》、《協議》卻漠然置之,不提出任何抗議或申明。可見猛烏、烏得之喪朱,清政府昧於國際信息,缺乏外交見聞,而不在勘界委員一時之疏忽失誤。法國殖民者始則要求會勘湄公河東岸之地;繼則製造會印口實,步步如意。攫取猛烏、烏得只待時機而已。
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結果,中國失敗,雙方簽訂《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割地賠款。日本意圖乘機霸佔遼東。但是,這時日本與德國、俄國在中國東北、華北均有政治的、經濟的利益矛盾。而德國、俄國、法國因這時在歐州有共同利害關係,結成同盟國家。他們維護共同利益採取一致行動。於是,三國聯合起來,迫使日本把遼東還給中國。日本還遼東給中國,在法國殖民者看來,是對中國極大的幫助,要求中國割讓猛烏、烏得作為報酬。清政府自鴉片戰爭以來,軍事、外交屢次失敗,視帝國殖民者如虎狼,不敢抗拒。凡所要求,無不屈從。
法、德、俄三國干涉日本,將遼東退還中國,對德、俄來說,是有其切身利害關係。因為中國東北是俄國的勢力範圍,而山東是德國的勢力範圍,是有其切身利害關係,必須迫使日本將遼東退還給中國。對法國來說,其勢力範圍在中國西南,還遼東給中國與否,無關其切身痛癢。只因法、德、俄三國有同盟國關係。為了履行同盟條約義務,須要一致行動。因此,隨聲敷合,搖旗吶喊而已。法殖民者,事先萬料不到,這一隨聲敷合,成為攫取猛烏、烏得的條件。這是法國外交上的意外勝利。中國外交上的極大失敗。
與中法會勘滇越界務的同時,中英兩國也會勘滇緬界務。關於,中國版圖之車里宣慰司,孟連宣撫司兩土司轄區,中英雙方早已達成協訂:「中國必不將孟連與江洪(今景洪)之全地與片土讓與別國;英國同意將木邦宣慰司、科干(今果敢或麻栗壩)土知縣,以及景棟,怒江以東之地畫歸中國(注9)」。中法在會勘第六段邊界之前,法國政府亦與中國駐法公使言明:「將來會勘第六段邊界時,絕不越中國車里之境(注10)」。這一聲明與《中英協訂》,並無矛盾衝突之點。然而,猛烏、烏得在清雍正年間以前,是車里土司所轄的兩個土司,以歷史言之,皆是車里之境。今法方意圖索取兩土司地,已違背它的諾言。中國政府理應向法政府提出抗議,並據法理堅決反對。可是,中國政府卻於此緘默不語。「車里之全地與片土,不讓與別國」,既與英國議訂在先,就應該慎重考慮於後。國際協訂之義務必須遵守,竭力避免被英國指責違約。當時,負責外事全權的李鴻章亦未嘗意料及此。既然中國將猛烏、烏得畫歸法越,英國自然認為中國已違背江洪片土不讓給別國之約。遂向中國政府申言,木邦、科干原屬緬甸,以前與薛福成定界時,強畫入中國,今理應收回。兩地極似多米諾骨牌,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兩地畫歸法方,遂導致木邦宣慰司(今緬甸上撣邦)、科干土知縣(今緬甸瓦邦滾弄以北)、江心坡(今緬甸克欽邦),以及明代萬曆年間,在今德宏州外所設置的八關之中的下四關。即鐵壁、虎踞、天馬、漢龍等四關。都是相繼於十九世紀末葉,中英滇緬會勘界務後,畫歸英緬的。中英滇緬界務,俟另文討論。
猛烏、烏得兩土司官及其民眾,自他們的耳祖鼻祖以來,六百餘年皆隸屬中國。今一旦聞訊畫歸法越管轄,誠如晴天驚雷,群情震憤。皆不忍與中華文明古國、父母之邦脫離。當勘界委員黎肇元、刀丕文由兩烏啓程返鎮邊廳(今瀾滄縣城)之時,該司官率領民眾遮道,哀求挽回。語言悲痛,令人鼻酸。兩司官隨及步行千餘里,到鎮邊廳第六段勘界總部,號泣請願。然未獲勘界大員們收回協議。中法會勘六段界務,可謂悲劇性結束。
注釋:
注1:見《清史稿‧邦交志》3《法蘭西》。《中法新約》、《中法天津條約》。簡稱《津約》。
注2:見《新纂雲南通志‧土司考》2《開化府》。以下簡稱(新志)。
注3:見《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五五三《越南》。
注4:見姆‧馬尼奇、瓊賽;《老撾史》二六四頁。一九七四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版。
注5:見《新志‧邊裔考‧邊防》。《臨安府》。
注6:「總署」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簡稱。
注7:見《清朝續文獻通考‧外交考》10《界務》。
注8:見《新志‧外交考》1。
注9:見《新志‧外交考》3。
注10:見《清朝續文獻通考‧外交考》10《界務》。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3期,民國92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