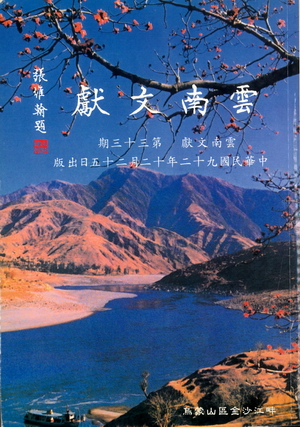辨明歷史真相 弘揚「護國」精神
王佩華
再過兩年,就是雲南護國起義九十周年。
一九一三年,袁世凱背棄贊成共和的諾言,暗殺了國民黨領袖宋教仁,鎮壓了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接著,他指使爪牙組織「籌安會」,密鑼緊鼓地進行復辟帝制的活動。
孫中山在日本發表《討袁宣言》,指出袁世凱「既忘共和,即稱民賊」,號召「愛國之豪傑共圖之」,「戮此民賊,以拯我民」。但袁掌握著清政府留給他的「北洋新軍」,擁有國內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北洋系統的人掌握著許多省的軍政大權;他的爪牙、秘探遍佈全國。他以為,可以輕而易舉地脅迫地方首腦擁戴他實現黃袍加身的美夢。此時,人民雖然反袁,但孫中山流亡海外,國內沒有與袁抗衡的政治力量;各省軍政當局,為求自保,紛紛「勸進」。
地處邊陲的雲南,經濟薄弱,文化落後,交通不便,新軍僅有一鎮(師)一協(旅),人數不到三萬;全省沒有一個兵工廠,槍炮消耗要靠外地補充;編練新軍前留下的巡防營,還在使用刀、劍、戈、矛和銅炮槍、九子槍等原始武器。袁世凱議定,雲南不敢反,也反不了。但他要造成全民擁戴稱帝的假象,也放心不下發動過重九起義的雲南人民。所以他仍然花了很大力氣對付雲南,威脅、利誘,雙管齊下。在廣東、湖南、四川安置他的心腹龍濟光、湯薌銘、陳宦,形成對雲南的包圍圈。他委派雲南巡閱使任可澄、政務廳長劉顯世、鹽運使蕭堃、財政廳長籍忠寅等人掌管行政,通過他們監督政局。同時,他著力拉攏唐繼堯等實權人物。唐繼堯四十大壽,他送了大禮,還贈了一筆專款,表示對雲南的關心。他還派出特使何國華來昆明授勛,封開武將軍唐繼堯勛一位,一等毅勇侯,贈九頭獅子印,並向其他滇軍將領授勛、授爵,答應按月津貼雲南財政三萬元。他並且托何交一封親筆信給唐,大意是:國家多事,西南半壁,惟吾弟是賴。世凱老矣,我此一席,唯吾弟是待。(1)(2)(3)
袁世凱權勢顯赫,如日中天,而身處政治漩渦中心的雲南督軍唐繼堯,不得不反復權衡,瞻前顧後。畢竟,這時的他,已經不是滿腦子共和思想的留日學生,也不是雲南講武堂裡小小的教官,而是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封疆大吏。他首先考慮的,是如何保住他的地盤,他的權勢。因而,在四面受敵的威逼下,在勛爵財富的誘惑下,他對袁世凱恭謹順從。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在《雲南政報》上發佈的「將軍府飭第一號」令稱:「亂黨孫文等自通逃海外以來,專以詐騙金錢,擾亂秩序為目的,種種鬼蜮,久為中外所共知」,飭令所屬機關:「一體查拿究辦可也」;他派出便衣,密查帶兵官的言行,嚴厲警告營長以上軍官;「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行為不能越軌。倘若為亂黨所煽動而有軌外行為,我為了維持地方自安計,只有當作匪徒嚴辦」;他親自審問並槍斃了中華革命黨派來活動的雲南支部總務徐天祿;他告知袁世凱的心腹,四川督軍陳宦;「山河可易,此志不移」,表白效忠帝制之意。他的父親唐省三,更是個死心塌地的保皇派,曾對兒子說:「全國擁護袁大總統做皇帝,是大勢所趨,你必須順應時勢,不能另做打算,主意拿錯了,輕舉妄動,會使我家遭到滅門大禍,還會帶累全省人民呵!」(4)(5)(2)(6)
但唐繼堯穩重地沒有把事情做絕,孫中山派呂志伊回雲南活動,警察廳按北京指示將呂拘囚。呂是雲南同盟會的老領導,唐的故交,所以,唐聽任反袁態度堅決的楊華和鄧泰中將呂保釋出來,吩咐鄧把呂「軟禁」在住宅中,並復電北京稱:「呂某係回家經商,並無他意。」而「軟禁」中的呂志伊卻與各級軍官頻繁集會,發展中華革命黨員,秘密策動反袁。(7)
由於身居高位的唐繼堯態度曖昧,擁袁聲勢甚囂塵上。在這個緊要關頭,一批老同盟會員、參加過雲南重九起義的愛國軍官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為首的,是唐繼堯部主力,步一團團長鄧泰中、步七團團長楊蓁。他們秘密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支持同盟會員馬驤、杜寒甫創辦《滇聲報》,製造反袁輿論,大聲疾呼:「共和成,民國興;皇帝出,吾國死。」「苟有人倡議帝制,破壞共和,吾國人必生啖其肉,死鞭其屍。」(4)(8)
鄧、楊一再對唐力諫,告以大勢,勸以順逆,鼓動唐起義反袁。楊葵憑借唐對他的器重,直接問唐:「北京成立籌安會,硬要將帝制拿出來,你家(您)看如何?」「袁世凱要當皇帝,雲南官兵都很憤恨。」還說:「古人干事,不計成敗。只要應該做,縱雖失敗,也要做,古今一個道理。」唐或者深沉地哈哈一笑,或者含糊其詞地說:「我認得,你好好掌握軍隊就是了。」一九一五年初,楊蓁向步一旅旅長孫永安拜年時明確表示:如果唐督軍不及時行動能來,他們就要幹了。護國軍第一路軍一梯團長劉雲峰評價說:鄧、楊「激烈反對帝制,積極主張討伐袁世凱。鄧是唐的親戚,楊是唐的中堅將領,唐後來同意討袁,這兩個團起了主要作用。」(9)(10)(11)
面對唐的模稜兩可、含而不露,鄧、楊把主要精力用於擴大隊伍,積蓄力量。他們一面遊說上級軍政人務,一面邀集中級軍官,在古幢寺、曇華寺、圓通寺以及太華寺後面的叢林中秘密集會,商討反袁大計。楊蓁慷慨陳詞:「我們都是革命軍人,捍衛共和乃軍人天職,決不與袁世凱共天地。」他認為:「唐將軍被袁世凱的權勢所懾,受袁世凱的利祿所誘,俯伏攀附,入袁世凱轂中。如唐將軍不聽諫言,我們就率滇人起義討袁。」他分析:「我們舉義則利於攻心,袁氏不義則難以用眾,一旦交鋒,袁世凱之北洋軍,心渙眾疑,破之不難。」「到會諸君所掌握的兵力,在省會駐軍中已經占據絕對優勢,只要團結一致,不愁不成功。」他要求同志:「教育所部官兵,人人枕戈待旦;聯絡愛國志士,以期三迤健兒同仇敵愾,齊心赴義。」經過多次密商,中下級軍官議定四項辦法:⒈於適當時候,集體要求唐表明態度;⒉如唐反對帝制,擁護他為領袖;⒊如唐態度中立,把他送往越南;⒋如唐贊成帝制,就把他殺掉,另選人領導反袁。(12)(13)
民主思想濃厚的高級軍官羅佩金、黃毓成等人,也在頻頻密商,他們和鄧、楊建立聯繫,通過鄧、楊模唐的底,並向唐進言。被袁世凱封爵的黃毓成,曾約鄧、楊找唐商議反袁,爭論最激烈時,黃甚至把手搶砸在桌上說:「要麼你討袁,要麼你用手槍把我打了。」唐父說:「黃大哥,你也替我們唐家想想,我家世世代代還沒有封過侯爵哩!」楊蓁說:「將軍,你倘若還想坐在滇軍主將這把交椅上,必須立刻下定決心討袁。」鄧泰中也說:「這是全體軍官的意思,絕對不會更改!」(14)(15)
呂志伊在《雲南舉義實錄》中,概括了當時軍政人員串聯的情況:「予回滇後,乃擔任與鄧君泰中、楊君華聯絡上級軍官,而中下級軍官士卒則由杜(寒甫)、馬(驤)、田(鐘谷)、李(文漢)諸君聯絡,於是滇中軍界全體,已隱有共同一致之軌道矣。」辛亥元老李根源說:「迨洪憲帝制興,若非熔軒(羅佩金字)……諸人醞釀於內,而鄧泰中、楊蓁……等輩應之於外……松坡(蔡鍔字)入滇,直送死而矣(已)。」(13)(16)
在這段時間裡,唐繼堯有著多重表現:既殺了一些革命者,又任用了很多革命者;既追隨袁,又與袁保持距離;既有擁戴,又有敷衍;既跟著「勸進」,又逐步進行反袁部署;既作準備,又不輕易表露心跡,進退之際,處處留有餘地。他曾對雲南宿儒陳榮昌吐露心跡:「楊蓁、鄧泰中等幾個團長都反對帝制,我沒有辦法。」但他又問過鄧泰中、楊蓁:「袁氏稱帝,你贊成嗎?」鄧說:「我願隨將軍的意志為意志。」楊說:「如果將軍反對帝制,我願效死命,如果將軍贊成帝制,我寧願辭職。請問將軍你是什麼意見?」唐說:「事關重大,我不能單獨作出主張,應當取決於多數。」唐地位不同,謹言慎行,可以諒解。這種矛盾起伏的心理狀態,很符合一個新興統治者的思維邏輯。(17)
鄧、楊等人積極果敢的行動,造成了波瀾壯闊、如火燎原的反袁大氣候。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唐終於意識到,違背軍心民意,就不能掌握部隊,就坐不穩「雲南王」的寶座。他終於俯順軍心民意,由首鼠兩端逐步轉到堅決反袁。
九月,唐召集軍事會議表示:「我輩以無數鮮血換來之民國,茲一旦為彼獨夫所私有,是可忍,孰不可忍!願與天下英雄共圖之。」會議部署了儲備軍事人才,添編警衛團,整飭地方團隊,派員調查通往四川各渡口的道路和糧食供給情況,派呂志伊赴海外募捐等備戰事項。唐又派人攜帶土特產和青銅古董,到北京贈送軍政要人,暗地了解袁的左右手馮國璋、段祺瑞對恢復帝制的態度。(18)(19)(3)
十月,唐召集第二次會議,商定起義的時機為:⒈中部有一省可望響應時,⒉黔、桂、川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⒊海外華僑或國民黨接濟武器、軍費時。假如以上條件都不具備,為爭得國民人格,也要孤注一擲,宣告獨立。會後,派人往上海、江蘇、廣西、四川、湖南、廣東、貴州,聯絡各地方實力派。(17)唐致函孫中山,表明全省人民「義憤填膺,誓不與此撩共視息」的決心。(20)
十一月,唐召集第三次會議,決定先頭部隊盡快出動。十二月十九日,首批參戰部隊誓師出征,楊蓁和鄧泰中率部經滇東北向四川挺進,董鴻勛率部到宣威駐紮待命。(21)
十二月初,李烈鈞來到昆明。接著,蔡鍔擺脫袁世凱的軟禁,離開北京,繞道來滇。唐繼堯派其弟唐繼虞到越南迎接並沿途保護,要他告訴蔡鍔:「滇中諸事俱備,只待蔡公借來東風,即舉大事!」二十一日,蔡到昆明。二十三日,唐電促袁世凱取消帝制,要求袁於二十四日上午十時答覆,袁許諾讓唐永為雲南統治者,誘唐罷兵。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唐、蔡、李率連以上軍官「歃血為盟」;「興師起義,誓滅國賊」;「萬苦千難,捨命不渝」。(19)
護國軍兵分三路,指向四川、貴州和廣西。昆明城懸燈結彩,「再造神州」的五色旗迎風招展,「立馬華山,推翻帝制;揮戈燕地,擁護共和」等對聯,貼滿家家戶戶。廣大青年踴躍入伍,學生宣講團巡迴演說,慷慨陳詞,商紳各界捐資贊助,整個昆明沸騰了。
袁世凱糾集重兵圍剿,而曾經與唐約定,雲南起義就響應的一些地方實力派反而擁袁稱帝,迫使護國軍孤軍奮戰,處境十分困難。終因北洋軍人心渙散,一些省份陸續宣告獨立,袁世凱陷入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境地,一九一六年三月,被迫取消帝制,同年六月六日,絕望而死。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總統黎元洪明令雲南護國首義日為全國紀念日。
一九二五年,國民政府頒布政令,褒揚唐繼堯;「袁氏僭號,首義滇省,維護邦基,厥功尤偉」。一九二六年國民政府又頒布特予唐繼堯國葬的政令:「洪憲叛變之際,首義滇疆,聲討帝制,保障民國,卒使奸賊奪魄,國基重固,革命大義,於以昭宣,志節勁於風霜,勛業炳於奕祀。」(20)雲南人為唐在圓通山建墓,在大觀樓立像。
護國起義在雲南爆發,有其必然性:雲南是辛亥後保存革命力量最雄厚的省份,也是由共和派掌握政權的少數省份之一;高中級軍官受過民主共和思想的薰陶,鬥志昂揚;滇軍士兵素質較好,裝備精良,如蔡鍔所說:「精銳冠於全國」;雲南遠離中樞,背靠國外,天高皇帝遠,袁世凱的控制相對較弱。唐的秘書何慧青說:「雲南起義實內因天賦之職責,為良心所驅使,外被中山先生之策動,為正義而奮鬥。」這個看法,相當確切。(17)
護國起義中,地瘠民貧的雲南作出了重大犧牲:官兵傷亡逾萬;教育款項用作軍費;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有騾馬完全被征用。護國起義後,運輸阻滯,商務蕭條,紙幣貶值,財政枯竭,迄十七、八年猶未恢復元氣。當年有人評論:護國起義「對國,為扶危平亂之功臣,為滇,為蕩產破家之敗子。」話雖刻薄,卻道出了所付代價的沉重。
護國起義是雲南近代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
袁世凱恢復帝制,是封建勢力企圖在中國復辟的第一次嘗試。而護國起義是繼辛亥革命之後,又一次反對封建專制的偉大鬥爭。護國起義的勝利,使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徹底粉碎了在中國恢復帝制的可能性。此後,張勛復辟曇花一現,一切野心家都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黃袍加身,即使想圓皇帝夢,也只能喬裝打扮,披著民主的外衣行事。
國父孫中山給予護國起義最為公正的評價:「雲南起義,其目標之正確,信心之堅強,士氣之昂揚,作戰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奮,響應之迅速,與黃花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謂先後輝映,毫無軒輊,充分表露中華民族之正氣,使籌安丑類膽戰心驚。」美籍華人教授朱永德說:「這一轟轟烈烈的起義運動,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罕有的關鍵性的歷史轉捩點。」「護國起義奠定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基礎,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才能發生五四運動這樣如火如荼的愛國主義運動。」(22)(23)
令人遺憾的是,護國起義的歷史意義被貶低,一些書籍,包括現行的中學教科書,談到護國起義時輕描淡寫。聲稱忠實於歷史的電視劇《走向共和》,對於再造共和的護國起義也是點到即止。北美史學會會長、加拿大籍華人學者徐乃德說:「影響中國政治全局的重大事件有五次,其中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西安事變、國共內戰等四次均成為一門顯學……而護國研究卻重視不夠。」他的看法一語中的。(23)
護國起義的歷史被歪曲,護國起義究竟是誰發動的?誰領導的?沒有形成正確的共識。
被世人尊稱為「護國三傑」的唐、蔡、李,他們各有自己的貢獻。唐曾說過:「雲南起義,多由孫(中山)先生倡導,吾滇自主為之」,而「外間不察」。蔡初到昆明就驚異地說:「真使我喜出望外,你們一切都準備好了。」他後來給梁啓超的信也說:「滇中級軍官健在者,如鄧泰中、楊蓁、董鴻勛、黃永社等,自籌安會發生後,憤慨異常,屢進言於莫督(唐),並探詢主張以定進止……人氣敵愾,有如火如荼之觀。滇人俠勇好義,於此可見一斑。」李事後回答護國之役誰主動時,曾經如實地、公允地說:「唐如不是主動,他就不容許我進去。即進去,他可以把我們獻於袁氏,立刻可以封王。唐如不早有決心,不早作準備,我們進去一周,即行露布天下……哪有這種容易的事」,「我和松坡,不過遠道赴義,幫同做一件大事。若言主動或論功,當然以唐為首功,松坡次之。」唐、蔡、李肯定,他們來到之時,雲南已經作好了各項反袁準備。而且,蔡來雲南之前,唐發電報告知:「滇中已有計劃,請公南來。」不僅如此,鄧、楊、董的先頭部隊,已經逼近滇、川邊界!(20)(24)(25)(26)
但是,長期以來,似乎有一種「抑唐揚蔡」的傾向,把發動和領導護國起義的功勞完全掛到蔡鍔頭上。現行中學歷史教科書是這樣寫的:「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宣告雲南獨立。」在這裡,任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的蔡鍔、第二軍總司令的李烈鈞,名列於前;任護國軍總司令兼第三軍總司令的唐繼堯反而敬陪末座。一九九四年昆明出版的《雲南近現代風雲人物錄》,也稱蔡鍔為「再造共和第一人」。而所有描繪護國起義的文藝作品,總是充分渲染蔡鍔和小鳳仙的纏綿愛情,著力突出蔡鍔的作用,使蔡鍔發動護國起義的看法深入人心,幾乎成了定論,以致達到李根源所說:「舉國上下,不知滇人,只知松坡」的地步。近人任光椿所著《蔡鍔傳》,為了塑造蔡鍔這位「軍事家和民主革命的著名鬥士」的光輝形象,竟說蔡到滇後,唐對蔡的到來仍有疑忌,對起兵討袁很猶豫,「口頭上反對恢復帝制,卻又一再拖延公開宣布討袁世凱的時間],經過蔡反復陳述利害之後,態度才「開始鬆動」,「在蔡鍔等人的堅持下,唐繼堯理屈詞窮,沒有什麼借口了,才不得不同意通電全國,由旦布獨立」。這樣的描寫,把「抑唐揚蔡」發揮到了極致!(27)(16)(28)
滇軍將領楊如軒分析,「梁啓超謂,雲南起義,是由蔡來滇後發動。唐所部文墨之士謂,唐不主動,蔡如何能入滇境。」但,「蔡來滇前,滇省已決定討袁,並作了軍事部署。而唐本擁袁稱帝,由於滇軍廣大進步官兵激烈反袁的壓力,迫使唐不得不走上起義討袁的道路」。因而他認為:「發動起義者既非蔡,也非唐,而是滇軍廣大進步官兵。」所以,「抑唐」其實是抑了雲南人民,不僅抹殺了唐的功勛,抹殺了鄧、楊等人的功勛,更抹殺了三迤父老的功勛。(12)
為什麼會形成「抑唐揚蔡」的輿論?
一、梁啓超的自我吹噓。當初,梁曾致電唐:「以一隅而抗天下,開數千年歷史之創局;不計利害為天下先,拯國命於垂亡,當為全民感謝。」他還說過:「帝制議起,國人劫於淫威,含怨蓄怒,側目結舌,莫敢出氣,首發難自會澤(指唐繼堯),黔、桂、川、粵、湘、浙望風嗣響,曾不旬月而奸雄隕,國體復。」他肯定「上將唐公為之主帥,國之虎士,同袍相輔。」但他又聲稱:「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者鍔」,「護國之役,吾所指使也,雲南何有焉。」史學家鄧之誠說:「護國之役,滇人出死命發難,後乃為進步黨人假借取大名,鍔與進步黨密結,自後鍔與滇人非比患難相共也。」而梁啓超是當年學術界的權威,一言九鼎,出版界人士,又多與梁有聯繫,正如李鴻綸所說:「審定教科書之人員,多與梁氏沆瀣一氣,無公理是非可言」,遂將護國起義完全歸功於蔡鍔一人,相沿成習,以訛傳訛。(29)(30)(22)(18)(31)(32)
二、袁世凱為了分化革命力量,故意玩弄政治玄虛,一再布告:「蔡鍔到滇遊說唐繼堯獨立,其實唐非出本心,全由蔡鍔脅制主使。」(29)
三、雲南地處偏僻,呼聲微弱,為國人所漠視。
四、或許最重要的原因是,唐繼堯後來蛻變為軍閥,影響了對他的公正評價。唐是一個經歷復雜的人物。從辛亥革命到護國戰爭,他功大於過;護國戰爭結束後,他利用討袁聲威,窮兵黷武,擴張勢力,墮落成為軍閥,後半生乏善可陳。但筆者以為,即便唐參加反袁「非出本心」,但客觀上起了積極作用,團結了省內外的反袁力量,推動了全國反袁形勢的發展,其貢獻也是不該抹殺的。對歷史人物,不以一語定終生,不以功飾過,也不以過掩功,而是分階段、分事件、分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就事論事地評論,才是正確的科學態度。曾以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省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而名聞天下的學者趙藩說唐:「治滇無善政,護國有奇功」,涇渭分明,最為中肯。(33)(34)
這種「抑唐揚蔡」的論斷極不公正,以致引起雲南人士的普遍不滿。白之瀚說:「在事諸人,分工合作,各有價值,不容軒輊。」「唐、蔡、李同為此役首領,何得獨尊一蔡,抹殺其餘?」但唐「既為發難唯一之地位,復總攬全局之事權,歃血立盟者唐繼堯,領銜討袁者唐繼堯,而西南合組政府之首腦(撫軍長)又復為唐繼堯,無論法理事實,均應為此役之代表。」李鴻綸說:「護國軍發動自滇,軍隊、軍實皆滇所有……所謂名義上、事實上無一非唐……勛勞同一,何以獨敘蔡一人,公理安在!」「此為公理正義及滇人人格上所應必爭者,不能認為唐公個人事也。」馬伯良說:「梁竟謂雲南再造共和的義舉,全係蔡鍔造成,蔡鍔之來滇,全是他的主張指使,實滑天下之大稽,亦不無文人無行之嫌。」李宗黃說:「貪天之功事小,禍國之罪事大,文人無行,政客無信,腐儒誤國,千古同調。」(29)(35)(36)(20)
最有代表性的,是周鍾嶽所發表的意見。周曾在蔡、唐幕府中工作,深知內情。他贈蔡之詩,有「南中草木識威名」的詩句。蔡死,雲南軍政當局按他的建議為蔡立銅像於蔡公祠,可見他對蔡的景仰之情。他說:「蔡公功在國家,不容淹沒」,但「梁啓超所發表,則蔡公松坡之來滇,全為梁所指使,而雲南之首義,又全為蔡公所主張,是蔡公不過為梁之傀儡,而雲南又不過為蔡公之傀儡也」,「此則雲南人所不能不憤慨者」。他尖銳指出,「大凡事變之起也,人人皆瞠目而不敢攖其鋒,及事功之成也,則人人皆攘臂而自以為己力;甚至捏造黑白,變亂是非,詆毀當日首事之人,必欲破其名而後已。」他聲明:「予之所以述及此故事也,並非為唐公一人爭名,誠以護國之役,吾滇軍政各界及全省人民皆以有力。使非吾滇人之慷慨好義,則唐公一人亦不能成功。吾滇人民因此役而犧牲甚大,然共和得以恢復,民國不致動搖,則吾滇民亦絲毫無昕悔;仍當竭力捍衛國家,使國基得以鞏固,此則吾滇人共同之心理。」(18)
二十世紀上半葉,雲南發生過三次起義:一九一一年的重九起義,一九一五年的護國起義,一九四九年的雲南起義。首末兩次起義的影響是局部性的;而護國戰爭雖然短短百日,卻從根本上扭轉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其貢獻是全局性的。
「護國起義」譜寫了雲南近代史上最輝煌的篇章,它所表現的為廣大人民利益挺身而出的愛國主義精神,不畏強權敢為天下先的大無畏精神,為正義事業甘於犧牲奉獻的精神,體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傳統道德精體,是一筆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弘揚「護國」精神,繼承光榮傳統,對增強民族凝聚力,構築先進文化,促進生產力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護國起義」是雲南歷史文化的一個亮點,為了使這個亮點成為璀燦奪目的恆星,筆者建議雲南當局著手籌備「護國起義」九十周年紀念活動,包括:召開學術研討會,澄清事實,正確評價,還「護國起義」的本來面目;搜集文物史料,建立紀念館或舉辦專題展覽;重新命名「護國路」、「護國橋」,在近日公園重豎護國起義紀念碑;命名「護國廣場」,塑造「護國群英」雕像;出版專著、拍攝專題電視片和電視連續劇(像鄧泰中、楊蓁的串聯游說,唐繼堯的由擁袁到反袁,授勛特使何國華在昆明受到前恭後踞的待遇,敘府前線楊蓁四路敗強敵等故事,本身就具有很強的戲劇性,稍加創作,必能獲得極高的收視率),普及「護國」史實,宣傳「護國」精神,古為今用,發揚光大。
普天下的雲南人,都不該淡忘這段光輝的歷史!
注釋:
(1)李丕章《護國軍納溪戰役和軍醫工作回憶》,《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2)鄒若衡《護國軍起義前唐的轉變和有關蔡的二三事》,《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3)詹秉忠、孫天雲《護國戰役中的唐繼堯及其與蔡鍔的關係》,《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4)李理林、李國慶《馬驤烈士革命事略》,昆明,《昆明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五輯,一九九五。
(5)李文漢《雲南護國親歷記》,《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6)鄧漢祥《滇黔反對袁世凱帝制的經過》,《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7)張俊《唐繼堯主持策劃護國起義》,政協會澤縣委員會、會澤民間唐繼堯研究會編《唐繼堯研究》第三輯,二○○○。
(8)一九一六年六月《滇聲報》登載感謝楊藥、鄧泰中等人捐款資助的啓事,轉引自《雲南出版史資料》第六輯,《出版志》編纂委員會編印,昆明,一九九○。
(9)鄒若衡《雲南護國戰役親歷記》,《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10)孫永安《雲南護國起義回憶》,《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11)陳天貴《護國戰役親歷記》,《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12)楊如軒《我知道的雲南護國軍起義經過》,《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13)呂志伊《天民回顧錄》,《昆明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政協昆明市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一九八一。
(14)祿國藩《雲南護國前後之回憶》,《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15)黃清《先父黃毓成談雲南發動討袁經過》,《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
(16)李根源《書丁巳川事》,《護國歷史資料選輯》,昆明,民革雲南省委編印,一九八五。
(17)何慧青《雲南擁護共和之經過》,《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
(18)周鍾岳《雲南護國首義之歷史談》,《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19)董雨蒼《雲南護國歷史資料》,《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20)李宗黃《雲南護國紀實》,《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
(21)奚濟霖《護國軍第一軍二支隊(原步七團)回憶》,《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22)轉引自社奎昌《正確評價唐繼堯在護國起義中的歷史功績》,會澤縣政協、會澤民間唐繼堯研究會編《唐繼堯研究》第三輯,二○○○。
(23)轉引自楊存仁《贊唐繼堯革命的一生》,會澤縣政協、會澤民間唐繼堯研究會編《唐繼堯研究》第三輯,二○○○。
(24)轉引自李文漢《護國軍起義前蔡鍔與唐繼堯的關係》,《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十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25)張鏡淵《昔年聘鼙鼓震南天》,《雲南文獻》第二十七期,台北,一九九七。
(26)李宗黃《雲南起義與唐繼堯、蔡鍔、李烈鈞》,轉引自《雲南文史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
(27)初中《中國歷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二○○一。
(28)任光椿《將軍行│蔡鍔傳》,北京,團結出版社,-九九六。
(29)白之瀚《雲南護國簡史》,《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
(30)梁啓超《唐會澤大事記》,轉引自會澤縣政協、會澤民間唐繼堯研究會編《唐繼堯研究》第一輯,一九九四。
(31)轉引自楊維駿《蔡鍔的政治傾向》,《雲南文獻》第十二期,台北,一九九○。
(32)李鴻綸《民國三十二年五月給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信》,轉引自《雲南文史論集》,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一九九四。
(33)許多人認為唐不是軍閥。一九八七年二月,李長猛、張貢新、張榮光、龍瑞麟四委員在雲南省政協發言說:「唐繼堯一生的主流,是站在清朝政府和北洋軍閥的對立面,並和他們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這樣一個對祖國和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振興做出了影響一代的豐功偉績的重要歷史人物,卻仍然被幾枝『金不換』的毛錐,死死地釘在『軍閥』二字的黑十字架和歷史恥辱柱上,這不能不是對當時雲南各民族人民和為革命流血犧牲的無數先烈們的一種侮辱!」,趙如琨《淺談軍閥兼及唐繼堯》一文認為,要稱唐為「中國舊時的軍閥」,「似乎証據不足」。會澤《唐繼堯研究》各集多位作者持相同的觀點。
(34)蒲元華《護國首義 再造共和》,《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八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二○○一。
另一說,此話為陳榮昌挽唐聯,見李生葂《陳榮昌傳》,《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六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35)李鴻綸《民四年雲南首義再造共和節略》,《護國歷史資料選輯》,民革雲南省委編印,昆明,一九八五。
(36)馬伯良《雲南護國首義史跡》,《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
作者簡介:雲南師範大學高級工程師,《劉淑清(昆明南屏電影院、安寧溫泉賓館、坤維慈幼院創辦人)傳》作者。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3期,民國92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