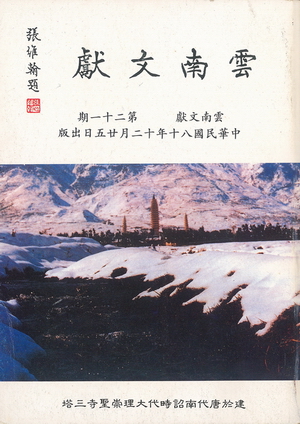雲南起義經過
何慧青遺作
雲南起義,擁護共和,國人俱以蔡鍔為主動,唐繼堯為被動,又以當時研究係首領梁啓超之加入,據其《盾鼻集》「國體戰爭躬歷談」所載,幾全為梁氏所主動,全為研究係之活動,甚至並康有為亦謂吾命梁啓超令蔡鍔為之,以致創建民國之國民黨,何獨於此役,黯然失色?雲南首義紀念,在前與武昌起義並重,今則日形冷落,僅與普通紀念,聊具儀式而已。其實平情言之,若唐繼堯不反對帝制,蔡至滇,唐講交誼可以將其禮送出境,不講交誼將其解交袁氏,以圖王侯之封,在勢均有可能。因蔡此時離滇近三年,所有滇軍將校,屢經更易,已成唐氏之心腹部隊,蔡督滇時,滇軍第一師長為謝役翼、第二師長為李鴻祥,離滇後第一師長為顧品珍、第二師長為沈汪度。唐由貴州調滇後,以張子貞為第一師長,沈汪度死後,以劉祖武為第二師長,旅、團、營長等,幾全更易,至唐所以必須更易之故,因為當時滇軍全係謝、李舊部,陰有拒唐入滇之意,幸旅長張子貞、團長孫永安等擁護,唐始得安然接事,故唐非將謝、李勢力完全鏟除不能自固。直然與蔡不生關係。至言及黨派,則人只見報紙上、表面上研究係之活動,而忘卻彊場上革命戰士衝鋒陷陣之活動。當時起義中人物,自軍都督唐繼堯起,至其他梯團長、支隊長以下,十分之九為同盟會國民黨分子(黨籍詳後表),以國民黨員擲頭顱灑熱血所得之代價,被人貪天之功據為己有,至今國民黨人亦不敢承認為本黨之紀念日,寧不為已死之數萬健兒呼冤。此筆者特於此二十一周年紀念日,將此次真相揭出,以告國人。
欲知雲南此次起義之真相,當先明雲南黨派之內容,至誠南在民初幾全為國民黨勢力,進步黨僅少數之教育界及學術團體,其勢力尚不及國民黨十分之一。更軍界則因握軍符者,全為同盟會份子,故其中下級幹部,多為國民黨員。又自唐氏督滇後,表面上對袁雖極形恭順,實際因唐與李烈鈞、熊克武等私交極篤,故癸丑革命,在湖口、重慶失敗之黨人,皆逃歸雲南,唐俱一一收容於講武學校內,下級軍官則為學生如胡子嘉即是。中上級軍官則為管教員如趙鍾奇、趙又新等是。此時國民黨經袁氏之蹂躪,在國內已消聲逆跡,惟在雲南則以山高皇帝運之故,革命暗潮,潛滋增長,因此軍界對於袁氏無不怒髮衝冠,即無帝制發生,恐討袁亦僅時間間題矣。自帝制問題發生後,上級軍官如羅佩金、黃斐一章等,曾多次勸唐起義,其他中下級軍官無不奔走呼號,迫不及待,空氣之緊張,遠其於辛亥之光復,使在上者似導稍不得往,必致激生內變無疑。唐氏見軍心如此,亦非決心反對帝制不可。惟吾人亦不能認為唐氏之反對帝制,係受部下之逼迫。蓋討袁護國,人同此心,唐亦同盟會強健份子,自不能獨異於眾。若為其個人之富貴利達,則如葉香石、黃斐一草、趙毓衡、趙又新皆速逃之客,袁氏之眼中釘,避之惟恐不遠,何敢親而近之,與之決策定計,此尤可見唐平日之態度。時中山先生在日本,派呂志伊回滇秘密運動軍隊,曾得一部份軍人同意,決定四項辦法:
一、唐氏如反對帝制,則仍擁其為鎖袖。
二、如唐中立,則以禮送其出境。
三、唐氏如贊成帝制則殺之。
四、如實行二、三兩項,則擁羅佩金為領袖。於適當時期,要求唐氏表示態度。
實則唐氏早已決心反對帝制,惟因事體重大,不得不嚴守秘密。如袁見唐不可靠,一令褫職,則討袁計劃,全盤受影響矣。此為中下級軍官所不知,故有是項決議。
呂甫入滇垣,即有統率辦事處電令雲南巡按使署及將軍署略謂:「有亂黨李根源、呂志伊等,入滇擾亂,命嚴防緝辦。」即被捕入警廳拘押,翌日,鄭泰中、楊蓁得訊,報告唐後,即赴警廳邀呂同至五華山謁唐,唐見面即道歉云:「此並非將軍署所為,軍署雖接有此電文,並未行文憲兵司令部,有案可稽。」《南強》雜誌載呂志伊回顧錄云:「唐是時已決心反對帝制,因極端守秘密,故中下級軍官尚不知。唐一日囑趙直齊約余前往磋商,謂反對帝制,早具決心,宜聯絡各省多有響應者,始不至失敗。歡余往各省擔任聯絡工作,余慨然應允。臨行之前一日,正值滇國民大會投票贊成帝制之日,蓋唐表面上不能不敷衍袁氏也。」於此可見當日唐氏反對帝制之決心矣。
一、二、三次秘密會議的經過
唐在籌備起義之前,曾開過五次軍事秘密會議,鄭泰中、楊蓁俱為同盟會員,鄭自恃與唐有親誼,楊自恃為唐得意門人,而又為有實力之團長,鄭、楊兩人亦歡探唐之真實態度而苦無機會。一日,唐忽謂鄭曰:「袁氏稱帝,汝贊成否?」鄭曰:「願隨將軍之意志為意志。」又問楊,楊曰:「將軍反對帝制,則某願效死命,將軍贊成帝制,則某寧願辭職,請問將軍之意如何?」唐日:「茲事體大,吾亦不能獨作主張,當取決多數。」但是時袁氏迭派何國華及江某至滇,徵詢其意見,隱含有監視臺忌,唐行動已難自由,乃囑其弟繼禹在警衛混成團本部,召開團長以上軍事秘密會議,由唐親自出席,宣布開會宗旨後,即謂:今日之會,係徵求全體真正之意思,望各發揮各人心中之真實意見,以備取決多數。眾皆云:「以將軍之意思為意思,並無意見。」唐笑曰:「此係官話,非各人獨立發表意見不可。」良久俱無人應,唐曰:「各位皆不肯,由我指定何人,即由何人發言,不得推諉。」即謂李友勛曰:「汝是第一團團長,由汝先發言。」李曰:「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長官令進則進,令退則退,無意見可言。」唐復笑曰:「此更是官話。」又指其他,皆云與李團長之意見相同。唐見各人俱不肯發言,乃曰:「可用無記名投票表決,希望各位不要揣測長官之意思,亦不要顧慮我們現在之舉措,而請發表自己真正之意思。」投票結束,全體一致反對帝制。唐即當眾宣布云:「既是全體真意如此,則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無論成敗利鈍,皆無後悔。」並決議三事:
一、極提倡部下愛國精神。
二、整理武裝準備作戰。
三、嚴守秘密。
此為第一次之秘密會議,時九月十一日事也。
十月初七日,復在警衛混成團本部開第二次秘密會議,商討起義時期,決定四項辦法如下:
一、中部各省有一省可望響應時。
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
三、海外華僑或民黨接濟軍械時。
四、如以上三項時機均歸無效,則本省為爭國民廉恥計,亦孤往一擲,宣告獨立。
此外並決定派呂志伊赴海外報告孫中山先生,請求在南洋一帶向華僑募捐;又派李宗黃、劉雲峯等往江蘇;趙伸、吳擎天等往廣西;李植生往四川;楊秀靈等往湖南,秘密運動各省響應。
十一月三日,復開第三次秘密會議,決定起義時作戰方面,推羅佩金擬定。羅在滇軍中有「智多星」之稱,凡雲南軍政長官有大計,多取決於彼,蔡督滇時任參謀長,蔡之一切軍政設施多出其擘劃。羅乃計劃以滇軍一、二兩師編為一軍,軍分三梯團,偕剿匪為名,將第一梯團運動至四川敘州附近,第二梯團運動至瀘州附近,第三梯團運動至重慶方面,出其不意,一舉而占敘、瀘、渝。此三重鎮既克,四川全在掌握,然後宣布雲南獨立,反對帝制。別遣第三師,幫助貴州獨立,出湖南、晃,謀會師武漢。並決定由唐繼堯坐鎮滇中,而以羅佩金為第一軍長,殷承瓛為參謀長出川。又以鄭泰中為第一梯團第一支隊,楊蓁為第二支隊,假名開往鎮雄剿匪,先行往川邊移動,鄭、楊遂秘密改編軍隊,準備動員,俱於十二月十日後,分批自雲南省城開拔。
蔡、李聯袂入滇興第四次秘密會議
李烈鈞自海外歸來至香港,見唐與袁之關係,亦不知底蘊,命其學生張維義,致函民黨鉅子葉荃、黃毓成、趙又新等,密探唐意旨,張至滇見雲南捕革命黨正急,蔡濟武及李根源之內弟某俱被捕殺,不敢投遞。(至蔡濟武等之死有兩原因,一因唐與李根源之猜嫌頗深,唐極不願李等之勢力伸張於雲南,一說偵探向唐報告蔡等之舉動時,值袁派之專使何國華在座,鄭泰中、楊蓁事前極力營救無效。唐曾大罵偵探不知進退。蓋雲南內慕雖積極反袁,表面上仍須敷衍。)事為呂志伊聞知,乃為之轉遞。唐聞知即派其弟繼禹赴港往迎,李隨偕方聲濤、熊克武、龔振洲等改裝入滇,仍為袁偵知,即由統率辦事處,代傳袁令曰:
「急滇唐將軍:華密。奉大元帥訓令:『疊據探報,有亂黨重要人,入滇煽亂,情形頗顯等語。唐將軍公忠體國,智勇兼優,必可鎮攝消滅,倘有亂黨赴滇,或猝生擾亂,准唐繼堯以全權便宜處置,無論何人,但有謀亂行為,立置於法,事後報明勿庸先行請示,所有徵剿出力將弁,均准破格請獎。要在保全地方治安,勿使生靈塗炭,予有厚望焉。』等語特達。處巧印。」
隨於十二月十八日,又接統率辦事處皓電云:「蔡鍔、戴戡偕同亂黨入滇,應嚴密防範。」等語。次日蔡鍔即繼李烈鈞之後入滇,《南強》雜誌雲南起義專號載:唐繼禹述唐繼堯派伊赴香港迎李烈鈞事云:「與協和先生同行回滇,及抵河口,接唐公急電云:「據日本領事消息,蔡松坡京寓被檢,已潛行赴日,除由滇電各方探查跺跡外,希弟立即折回香港、上海等處,探尋密約來滇,至協和已另派鄭泰中來接,望轉告」等語。次日鄭泰中已到,乃請協和先生改裝,同鄭泰中密行赴省,繼禹即折回香港,方將啓行,適聞松坡先生已到越南,當即往晤,約之入滇,次日起行。斯時袁氏已有所聞,曾密電唐公立置於法,事後報聞,並電其帝制黨羽蒙自道尹周沆、阿迷知事張一鵾,沿途謀害。唐公乃急電繼禹與駐蒙自師長劉祖武沿途注意。及抵阿迷,周沆、張一鵾,率領親信,暗中佈署,欲有所為,幸繼禹隨帶軍隊警戒周到,卒未得逞。事洩,周沆潛逃,張一鵾被捕,隨即正法。(按張為蘇州張一麐之介弟)繼禹與松坡先生至十二月十九日抵省,松坡與唐晤談,彼此意旨不約而同。據唐繼禹此述,則蔡之赴滇,事先並未經商得同意,亦無信通知。
⒈當時郵電皆受檢查,恐通信洩露機密,不特與自有身有危險,且恐袁對雲南先加防範破壞。
⒉蔡於十一月十一日離京,於十二月十九日抵滇,郵函往返最快四十日,電報則明電既不能明言,密電更惹人注目,事實上無通倘息之可能。
⒊此時蔡尚不知唐之真實態度,如唐係反對帝制固佳,如唐贊成帝制,回函謝絕反成僵局,若逕往則唐即真心向袁,亦可以私人交誼,促其改變態度,故蔡未入滇之先,實未與唐通消息。蔡深悉滇軍之素質及唐氏之人格與交誼,決不至相負,故作不速之客。觀黃斐章在南強雜誌起義專號中發表雲南起義之經過云:「方蔡公之間關走日本也,尚以為雲南未必真能舉義,始到越南試探。唐公知之,即派唐繼禹先生親往河內迎護。蔡公抵滇,首謂不圖同輩已有驚人之決心與準備,而民氣之澎湃,尤為難得云……」
(黃斐章名毓成,任護國軍挺進軍司令,出席將領會議,為雲南首義中堅人物。黃與唐有金蘭之交,後與唐政見不合,不容於唐,通逃在外,唐死後始歸,後在南京陸軍大學任教。其言當係親見親聞,自屬可信。)
蔡鍔抵滇後,見唐氏堅決反對帝制,且各項籌備就緒,即於當日雷梁啓超報告。梁自南京復電謂:「因外交上某種關係,以提前發表為佳。」唐遂於其私邸開第四次秘密會議,變更以前計劃,提前發表。蔡鍔、李烈鈞、方聲濤、熊克武等均出席,唐以梁電自南京發,以為馮國璋必有所助力,且不知外交上有何作用。又以蔡、李等至滇,袁氏已知,再難敷衍。遂決定於二十三日先電袁氏勸其取消帝制,懲辦禍首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限二十四小時答覆,至二十四日無答覆,遂於二十五日宣布里雲南獨立,擁護共和。
論此次戰事,以原有之作戰計劃為佳,出其不意,一戰而克四川,即可合滇、川、黔之眾,與北洋軍周旋於巫峽、夔門以外,東下湘鄂,西去秦隴,革命局勢當為之大振。乃因梁氏一電之促,僅敘州一路,軍隊已運至川邊,占頒尚易,瀘州、重慶方面,則以曹錕、張敬堯等北軍已大集,戰事極為猛烈,幾經挫折,革命精銳,大半犧牲於此。倘無各省響應,則民國之為民國,尚不可知。而所謂外交上某種關係者,至今吾人尚莫名奇妙。梁殆以未悉雲南內情,誠恐夜長夢多又生變化,而不知滇軍顛扑不破之革命精神,決不至「今日之我與明日之我宣戰也。」
起義時之誓詞及各將領之黨籍
宣布起義之前夕,十二月二十二日,復開第五次秘密會議,於五華山將軍署大禮堂。出席者蔡鍔、李烈鈞、任可澄、羅佩金、張子貞、方聲濤、陳廷策、劉法坤、成恍、顧品珍、黃毓成、趙又新、戴戡、殷承瓛、孫永安、楊杰、戢翼翹、葉成林、何海清、馬為麟、吳和宣、盛榮超、鄧塤、唐繼禹、李霈、李友勛、徐進、馬聰、秦光弟、李修家、李朝陽、董鴻勛、趙世銘、李琪、胡道文、李雁賓、王伯群、庾恩暘等,唐繼堯出席。歃血為盟,由唐繼堯刺指瀝血於酒罐內,並以余血塗於親書簽名之誓詞上,蔡、李、任等,依次舉行。其誓詞云:
「擁護共和,我輩之責。興師起義,誓滅國賊。成敗利鈍,與同休戚。萬苦千辛,捨命不渝。凡我同志,堅持定力。有逾此盟,神明必殛。」
宣誓畢,各人飲血酒一杯,焚化誓詞,大呼:「中華民國萬歲!」旋議改組政府,更定軍隊名稱。有議以宜設備臨時政府,推舉大元帥者,唐、蔡均不贊成,以為雲南以大義為天下倡,原期各省聞風響應,若先設此機關,使人謂我輩之舉,係為權利,反阻人向義之路,宜俟響應省份稍多,然後就各省公意組織,方足以示大公,遂決定設立雲南軍政府,設軍都督綜理軍民政事,軍隊則改稱護國軍,將所有滇軍改編為三軍。唐以蔡行輩最老,已曾為部下,即推蔡為都督,擬自率第一軍赴川。蔡又以唐在滇任將軍甚久,駕輕就熟,非唐莫屬,以此來為犧牲救國,願當前鋒,獨任其難,相持不決。卒以多數主張不變更現狀,唐仍從眾議,就軍都督任,聘蔡為第一軍總司令,任命李烈鈞為第二軍組司令,(按李曾因此表示不滿,謂同一軍長,何以一則函聘,一則任命。)此可見唐、蔡起義時,動機之純潔,絕無絲毫權利之心存於其間,其儴德尤為近代軍人中所少見,今將護國軍之編制,及將領之黨籍,表列如下:
軍都督 唐繼堯(同盟會)
總參謀長 張子貞(同盟會)
第一軍總司令 蔡鍔 國民黨滇支部長
總參謀長 羅佩金(同盟會)
第一梯團長 劉雲峯 黨籍未詳
第一支隊長 鄭泰中(同盟會)
營長 馬鑫培 李文漢(同盟會)
第二支隊長 楊蓁(同盟會)
營長 田 谷、金漢鼎(未詳)
第二梯團長 趙又新(同盟會)
第三支隊長 董鴻勛(同盟會)
營長 蔣文華、周頤(未詳)
第四支隊長 何海清(無黨籍)
營長 唐淮源、沙云仙(未詳)
第三梯團長 顧品珍(同盟會)
第五支隊長 祿國藩(未詳)
營長 曹之華、楊希華(未詳)
第六支隊長 朱德
營長 楊池生、鄭森(未詳)
第四梯團長 戴 戡(進步黨)
第七支隊長 熊其勛(未詳)
第八支隊長 王文華(同盟會)
炮兵大隊長 耿錫連
連長 龍文漢、譚兆福、楊磷星、王召棠、劉治琛、孟雄成(未詳)
游擊隊長 廖月江(未詳)
軍警大隊長 賈玉樓(未詳)
憲兵大隊長 聶民德(未詳)
第二軍總司令 李烈鈞(同盟會)
第一梯團長 張開儒(同盟會)
第一支隊長 錢開甲(未詳)
第二支隊長 盛榮超(未詳)
第二梯團長 方聲濤(同盟會)
第三支隊長 黃永社(同盟會)
第四支隊長 馬為麟(未詳)
第三梯團長 何國鈞(同盟會)
第五支隊長 林開武(未詳)
第六支隊長 王錫吉(未詳)
第三軍總司令 唐繼堯(同盟會)
第一梯團長 趙鐘奇(同盟會)
第一支隊長 華封歌(未詳)
第二支隊長 李植生(同盟會)
第二梯團長 韓鳳樓(未詳)
第三支隊長 吳傳聲(未詳)
第四支隊長 彭文治(未詳)
第三梯團長 黃毓成(同盟會)
第五支隊長 楊 杰(國民黨)
第六支隊長 葉成林(未詳)
第四梯團長 劉祖武(同盟會)
第七支隊長 楊體震(未詳)
第八支隊長 李友勛(國民黨)
第五梯團長 庾恩暘(同盟會)
第九支隊長 唐繼禹(同盟會)
第十支隊長 趙世銘(未詳)
第六梯團長 葉荃(同盟會)
第十一支隊長 馬驄(未詳)
第十二支隊長 鄭塤(無黨籍)
觀上表,護國將領,十分之九為國民黨員,進步黨僅戴戡一人,且其所部仍非進步黨,如王文華仍為中山先生信徒,熊其勛雖不詳其黨籍,然熊為黔軍中忠勇最著者,觀其後由川中致死,(即戴挑撥川滇內江)頗多怨艾之詞,深以供人犧牲為不值,可知熊非進步黨,則此次護國之役,為進步黨之力,抑國民黨之力不辨自明。蓋自國民黨被解散後,進步黨亦無形瓦解,各黨俱生兔死狐悲之同情。及帝制發生,皆化除黨見,加入護國團體,各黨為厚集勢力起見,自不能拒絕,初不料喧賓奪主,如梁啓超《國體戰爭躬歷談》及《盾鼻集》所載,幾全為研究係之活動,此猶害之小焉者。最甚者,被貪天之功,熱中名利,不擇手段,致西南團體破壞,北洋軍閥勢力復張,如袁氏取消帝制,退居總統,召段祺瑞組閣,與護國軍停戰議和,梁即密電唐、蔡主和,唐復電以袁氏稱帝,已喪失總統之資格,非其退位,無和可言。梁復由川直電蔡氏,蔡以師生關係,復電贊同,唐聞之復電各軍團長,謂:「前敵將領不能自由發表意見,以免與政府主張兩歧。」蔡見此電,頗形憤慨,以為唐蓂賡居然以上司自居,我連發言之資格已無矣。唐、蔡至此,即生意見。袁死後,梁保戴戡任四川省長,專挑撥川、滇惡感,致川、滇軍內訌,戴亦被戕,是進步黨此次之加入實害過於利也。
編組軍隊師出四川
蔡於雲南起義前三日始入滇,尚在李協和之後,人人皆知,雲南於起義十日以前,即見大批軍隊開拔,聲稱開往鎮雄剿匪,亦為全滇所共曉,若使蔡為主動,雲南為被動,則入川之師,最迅速亦必於蔡至滇之日,始能開拔。由昆明至斂州,須一月路程,即按站前往,一日不休息,亦必於一月二十日始能抵敘。而大部隊長途旅行,決無一日不休息之事,何況沿途均有戰事。再按當日護國第一軍先後開撥之次序,第一梯團長劉雲峯,該梯團於十二月初十、十一、十二、十三日,由省先後出發,向川邊敘州運動,第二梯團長趙又新,於蔡到雲南起義揭曉後四五日始出發。第三梯團長顧品珍係隨蔡五年(一九-六)一月十六日出發,第四梯團長為戴戡,顧、戴兩梯團,成立均較一、二兩梯團為後,因顧時任講武學校校長,戴任北京參政,隨蔡入滇,到貴州後,始成立第四梯團,故較其他各梯團成立為最後。
第一梯團出發後沿途均有戰事,今據楊蓁電云:「我軍自克黃耳坡、燕子坡、鳳來場等處後,節節進攻,克復捧印村,敵勢不支,遂向橫江退卻,時敵軍由敘調集,有炮隊機關槍等,扼守橫江一帶,我軍當即跟踩追躡,於十八日午後三時,進至橫江接近之黃榮鋪,時有敵之北軍約一混成團,漢軍數營,已在該處扼守,形勢極為堅固,我軍遂分兵兩路進攻,第一支隊向敵之左翼攻擊,本支隊向敵之右翼包圍,至午後四時三十分鐘,敵兵不支,紛紛逃散,被我軍擊斃數十人,擊傷數十人,並生擒北軍長官二員,擊斃二員,生擒北兵五人,本支隊即馳橫江追擊前進。至午後七時距橫江約三公里,敵之後衛,猛向我軍射擊,炮彈機關槍,勢如雨下,蓁仍冒險前進。時天色已黑,敵人槍炮亂發,約一小時,旋即崩潰。我軍乘勝奮追,敵軍遂紛紛乘船逃遁,遣棄炮一門,並子彈無算,至午後十一時,遂完全占領橫江。……」
此可見沿途均作戰,且敘州距害南省城須三十日路程,而護國軍一、二兩支隊於一月二十日即占領敘府,即使於蔡到滇之日,即令出兵,依旅次行軍,亦不能到達,況屬戰鬥行軍,自塩井渡以下,黃耳坡、燕子坡、鳳來場、捧印村等,均有敵軍扼守,沿途作戰,耽延時日,十八日橫江之戰事,尤為激烈,此在事實上無可證明蔡未到之先,雲南早已出兵。筆者之為此言,並非抑蔡而揚唐,惟證明唐並非被動,於蔡之人格勛績並不減損,且蔡自有蔡之長處,並不在主動與被動,如在四川作戰,北軍總數超出滇軍五倍以上,而蔡孤軍血戰,當以少勝眾,支持半年之久,雖由滇軍之忠勇善戰,亦全賴指揮官之謀略。而蔡對外之聲望與號召力,亦無形中增加護國軍之勢不小,若使蔡轉而居於唐之位,坐鎮滇中,籌餉增兵,接濟補充,恐又用非所長,唐、蔡實相得而愈彰。故蔡不入滇,雲南亦必起義,惟戰事之發展情況如何,則又不可知。此凡知雲南起義內幕者,當不以余言為虛妄也。再按蔡之就職通電:
「滇督唐公,黔督劉公,皆忠義憤發,備以所部,編成護國軍,以屬之鍔。負弩之責既專,絕纓之志已決。是用整隊北行,取道蜀、漢,誓靖中原……中華民國滇黔護國第一軍組司令蔡鍔叩印。」
此可確證,唐以軍隊編交蔡氏,並非如雁擄君在《中央日報》「中央公園」欄副刊內所述,蔡委唐為留守司令。蔡亦曾稱「滇督唐公,忠義憤發」,對唐已褒美在前,蓋當時唐氏而不公忠為國,雲南而不熱烈同情,則蔡氏一手一足何能為力。蔡決無左右唐之權,更無所謂主動與被動也。
至蔡所以得享大名之原因
一、護國成功後,梁啓超依附馮國璋、段祺瑞取得一部份政權,其宣傳之力自大,民黨則仍在軍閥摒棄之列,尤其段祺瑞對唐繼堯最為嫉畏。
二、因雲南正在贊成帝制,選舉國民代表之際,忽焉蔡氏一至,霹靂一聲,風雲變色,局外人不知,遂以為全係蔡氏之關係。
三、因蔡前在滇有善政,此次功成身死,人皆哀之,唐則坐鎮後方,運兵轉餉,悉索敝賦,結怨於民,遂讓蔡獨享大名。豈知雲南反對帝制,事前曾開五次秘密會議,蔡於第四次始參加,現尚不少人證。此事若非籌備之於平時,焉能於二三日之間,咄嗟立辦,且若不先事敷衍,微見豐采,袁政府又安能相容。護國討袁為雲南軍界之實情,贊成帝制為唐敷衍袁之手段。蔡亦曾以此敷衍袁氏,報一章雜誌,載此事極多,如黃毅《袁氏盜國記》云:「籌安會成立,袁以帝制探蔡意,蔡固重容附之,並允首先表示贊同,袁以為喜。」故雲南起義後,蔡曾通電:謂蔡曾勸進,唐曾贊成,並將唐往復之密電宣布,吾人知蔡之勸進為假,又安能斷唐之贊成為真。若使唐先無決心,準備有素,則蔡決不能於十九日到滇,二十三日即發表討袁。
又此役李烈鈞亦其中之中堅人物,在雲南則唐、蔡、李並稱為護國三杰,而在外即少稱者,以論資格則蔡、李同為都督,論到滇之日期,則李尚先於蔡,論任務則同為軍長,論戰功則李在桂、粵之戰績,亦不亞於四川,但人知有蔡而不知有李,可見人之獲享大名,亦有命運存焉。抑由起義至今,屈指二十一周,當時與盟參戰人物,或捐軀國事,或老死牖下,泰半已作古,今僅健存者,惟李烈鈞、任可澄、黃毓成、殷承瓛、唐繼禹、李宗黃、李修家、董鴻勛、王伯群、朱培德、楊益謙、趙毓衡、成恍、楊杰等諸人,僅居十之二三。其中如李烈鈞、朱培德、楊杰等則已為國家元勛,雖榮枯有別,趨向各殊,而俯仰之間,俱為陳跡,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余亦何暇曉曉為之爭是非哉!故筆者最後得一結論,即雲南起義實內因天賦之職責,為良心所驅使,外被中山先生之策動,為正義而奮鬥,人人皆為主動,人人皆非被動,故唐、蔡不動而雲南亦必動,雲南不動,雖唐、蔡動亦何能為,唐之非為蔡而動,亦猶蔡之非為梁而動,人明知梁啓超之反對帝制,非受康有為之指使,奈何以雲南起義,為受梁、蔡之被動乎?
蔡鍔離京實況
附漢陽哈漢章《春耦筆錄》
四年十一月十日,為予祖母壽辰,宴客北京錢糧胡同聚壽堂。譚鑫培以同鄉交誼,串名角奏劇。蔡松坡同學往還素密,是日早至,謂予曰:「今日大雪,可在此打長夜之牌。」予知松坡有用意,即托劉禹成代為召集。松坡前執手曰:「我與你同案三年,今日要暢聚一夜,你要慎擇選乎。」劉曰:「張紹曾、丁槐(前清提督軍門,雲南鶴慶人。)二人如何?」松坡曰:「可。宜到隔壁雲裳家中,稍遲重要人物來,捧小叫天者必多,聽戰、開席皆不必來請。」予應之,明知袁之偵探亦將隨往也,蔡、劉、張、丁聚博終夜。天未明,松坡躊躇曰:「請主人來,我要走。」紹曾曰:「再打四圈,上總統府不遲。」松坡曰:「善」。七時,松坡由予宅馬房側門出,直入新華門,門衛異之,意以為受極峰所傳。偵探抵府門,亦即星散,未甚置意,松坡抵統率辦事處,侍者曰:「將軍今日來此過早。」松坡曰:「我錶快兩小時矣。」隨以電話告小鳳仙,(瀘妓鳳云,在京張幟,易名小鳳仙,名噪甚,松坡暱之。)午後十二點半,到某處同吃中飯,故示閒暇,倘徉辦事處中,若無其事者,人亦不察。乃密由政事堂出西苑門,乘三等車赴津,繞道日本返滇。自松坡走後,予受嫌疑最重,予宅門以外,邏者不絕,劉禹成、張紹曾次之,丁槐則徉無所謂,小鳳仙因有邀飯之舉,偵探盤結終日,不得要領,乃以小鳳仙坐騾車赴豐台,車內掩藏上聞,予等亦宣揚小鳳仙之俠義,掩人耳目,明日,小鳳仙挾走蔡將軍之美談,傳播全城矣。劉禹成有咏洪憲紀事詩云:
當關油壁掩羅裙,女俠誰知小鳳仙。
緹騎九門搜索遍,美人挾走蔡將軍。
整理者附記
此稿係根據原作者何慧青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南強》雜誌,雲南同鄉紀念擁護共和二十一周年專號所載:《雲南起義與國民黨之關係》。及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南京《中央日報》副刊《中央公園欄》內所載:《蔡松坡入滇起義軼聞》;同在該欄《答雁擄君論蔡松坡入滇起義事》;以及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逸經》第二十一期新年特大號所載:《護國之役雲南起義秘史》;《逸經》第二十四期,《雲南起義秘史補註──答浙江大學愛讀逸經-份子》等前後五篇文稿,加以綜合整理,完成此稿。
對原文並未作任何更改,僅將每篇題目更換,刪去其重復之處。
原作者早年在雲南與惠我春共辦過義聲報,見聞頗廣。又於護國護法時期,擔任過唐繼堯的秘書。因此每篇所述,均係親見親聞。對研究雲南護國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文中所述起義之第一次秘密會議,蔡鍔、李烈鈞之聯袂入滇,梁啓超對護國軍之間挑撥離間,與後來唐、蔡間之矛盾等,均為其他各文中資料所未記述。又護國軍之編制,及將領黨籍表,亦較董雨範所引白小松《護國軍編制將佐暨其黨籍表》為詳。
此外蔡鍔離京問題,向來紀此事者,大都詼奇詭異,故神其說。本文最後附錄哈漢章《春耦筆錄》,因蔡是參加哈家壽宴之後離京的,故當日情景為哈親眼所睹,因哈為主人,劉、張、丁均作陪客,所述自與一般傳聞不同,姑錄之,以供參考。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方壽康整理)
轉載一九八四年四月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1期;民國80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