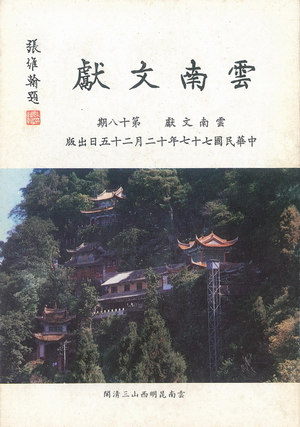與時代若即若離的未央歌
作者/齊邦媛
自從出版界趕上時代潮流,也用電腦排出暢銷書排行榜以來,引起我最大興趣的是浮沉其間的『未央歌』。許多許多年來,這一本厚達六百多頁的老書,自民國四十八年初版至今四十餘版,一直在不斷進出的新書叢中穩穩地佔一席之地。大多數的人稱它為抗戰小說,而它實際上未涉抗戰,年輕的讀者也不見得會為那個時代而讀六百頁的小說。而如果說它是浪漫的愛情故事,它並沒有寫出真正的愛情。那麼『未央歌』一書生存之道何在?
文學作品當然並不一定要反映或刻畫一個時代。也並非每個作者都有這種興趣和使命感。『未央歌』開篇說明它的緣起,點明了抗戰初起的年月和西南聯大遷至昆明的經過。它甚至還繪出了校園的回憶圖。但是對那一個實際上已經翻天覆地的戰爭,保持的是若即若離的態度。作者鹿橋在「再版致未央歌讀者」一文中說得很明白:它是「一本以情調風格來談人生理想的書」,但是它「另外有更重要的任務,它要活鮮鮮地保持一個情調,那些年裡特有的一種又活潑、又自信、又企望、又矜持的樂觀情調。那情調在故事情節人物個性之外,充沛於光線、聲音、節奏、動靜之中。……故事困於時代、地點、人物,往往事過境遷顯得歷史味太重很是陳舊。情調由文字風格來傳達,往往可以隔了時代,因一代新讀者自身經驗及想像力而更替長新。」(第四│五頁)
作者確實堅持用這種情調貫穿了全書,「為了一定要另創一個比較永恆的小說中的世界,我想只有用風快的刀一下把兩個世界割開。」被割掉的世界是抗戰時期的現實世界(譬如說抗戰時期的物價)。割掉這現實的世界,文字才能乾淨,人物性情才能明爽,昆明的陽光才會耀眼,雲南的風雨才能洗脫心上無名的憂傷,如此未央歌裡的地方、情節、人物就分外美。盡情的美,不羞不懼地美,又歡樂的美。」
有了作者加此一番交代,讀者即不能用歷史時代觀稱它為抗戰小說了。雖然書中不是沒有八年抗戰,也不是沒有災禍。「楔子」中有一句說:「這天是九月廿八日,那時節戰火已遍燃國中。東南、東北,半壁江山已是稀糟一片了。」日本飛機也曾轟炸昆明多次,書中也有三頁描述空襲時民眾的傷亡與驚嚇。但是,對於得天獨厚的西南聯大學生,戰爭的災禍自有它輕鬆的一面:「外文系的學生說『警報是對學習第二外國語有利的,我非在躲警報躺在山上樹下時記不熟法文裡不規則動詞的變化。』」流亡學生的貧困也自有天然紓解之道,在校園裡,「他們躺在自長沙帶來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陽光正鬆鬆軟軟的好睡。他們一閉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興奮多變的時代,富壯向榮的年歲,便驕傲得如冬天太陽光下的流浪漢;在那一霎間,他們忘了衣單,忘了無家,也忘了饑腸,確實快樂得和王子一樣。」(第十一頁)
在『未央歌』中,歡樂和喜悅是它主要的情調,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氾濫全書。對於書中人物,「那一霎間」幾乎是他們全部的大學生活。在全書六百一十頁中,太陽似乎很少落下。夕陽是畫家的配色碟,「雨季的尾巴就是孔雀的尾巴」。晨昏「兩道寒風的關口,正像是出入夢境的兩扇大門。」而雲南特產的野生玫瑰,「伸著每枝五小片的尖葉,鑲著細細的淺紅色的小刺,捧著朵朵艷麗的花」從第一頁開到最後一頁,豈止是四季而已!在「緣起」章首,即說這花是有靈性的,「每度花開皆象徵著一個最足為花神所垂顧的女孩子……」
抗戰八年,到了民國三十年珍珠港事變之後,東南亞多已淪入日軍鐵蹄之下。偌大中國已不止是半壁江山稀糟一片了,而戰火始終未燃至昆明。在西南聯大的校園上不僅弦歌不絕,且維持高深的學術理想,為中國培育了許多傑出人才。而這種有靈性的花一直開著,似乎象徵著不止一個為花神所垂顧的幸運兒,蔭庇他們過著有情趣的大學生活,讀書,交友,戀愛,盡情地追求歡樂與美,全然不見顛沛流離,生離死別陰影的威脅,這豈不是比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境界麼?能吸引今日青年讀書的,這必然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但是這本書卻絕不能稱之為抗戰文學作品。書中人物和故事發生在那一場天翻地覆的戰事邊緣,不但未受波及,而且看到了真正太平時代看不到的景象;思索了一些太平時代不會想到的問題。譬如滇緬公路上發國難財的單幫客,把昆明的市區染上了物質浮華的天堂假象,書中人物如宋捷軍者流就棄學從商,成了「白手起家」的小暴發戶。緬甸戰局惡化的時候,中國軍隊與盟軍聯合入緬,征調了一些四年級的外文系學生作翻譯官,然後又去了一些二三年級的外文系學生和各系有特別技能的學生隨軍服務。緬北、滇西的密支那、瓦城、臘戍等城告急的時候,歸僑與難民湧進了昆明,西南聯大參加了政府的急救工作。書中男女主角全曾在一部紅十字會的救濟車上奉獻心力。有時也會自問,活著是為什麼呢?「看見報紙上什麼地方有了天災,立刻在腦中繪出一幅哀鴻遍野的景況,又想到那裡還有戰爭,又想到身邊的社會也不健全,又想到全世界竟無一是處。馬上做刺客?馬上作兵士?全殺不完各種的敵人!馬上去救災?馬上捐掉所有的錢?明天報上的災情仍是嚴重。」(第二七二頁)只是這樣的苦思不多,幾乎完全不影響全書輕快歡愉的情調。對於這一批幸運兒,戰爭是什麼?民族的生存和前途是怎樣?似乎只有極模糊的觀念。甚至有一種事不干己的距離,乃至冷漠。書中有一段寫遷校第三年,學生們為了抵抗奢靡的昆明市聲,「可憐,他們便提高了喉嚨念書。用自己的嗓音阻塞了自己的耳朵。他們是不怕空襲的。有了空襲時,他們說:『炸罷!我們這個病人,病根深得很,戰爭的醫生,多用些虎狼之劑罷!』」(第三百一十七頁)
為何會如此全無憂患意識呢?是誰在投彈,炸的又是誰?既是中國人,又是大學生,怎會有如此怪誕冷酷的戰爭觀?
以這個角度看『未央歌』,覺得這些俊男美女好似參加了一場路程數千里的郊遊,來到了一個芳草鮮美的桃花源。男耕女織非關我事,知識的追尋輕而易舉。政治鬧爭、思家憂國都休提起。在他們追求美與愛的過程中,容不下「世俗」的憂患意識。參加者的名單是由幸運之神親自圈選的。抗戰時期,由淪陷區遷往四川與雲南的大學由於新址與主持人氣質的不同,亦自有其不同的命運,雖然都達到了高等教育的目的。
構成西南聯大的三校,北大、清華、南開,原是中國最具自由學術傳統的大學,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有各具特色的地位。由北平天津輾轉遷往昆明,路途千萬里,若沒有高瞻遠矚的安排和克服萬難的毅力,豈能辦到!想到半世紀前運輸能力之落後,路途之險阻,更令人肅然起敬。『未央歌』的「楔子」故意似舊小說手法敘述一段該校與土地之綠,莫非也是說明人間因緣際會,幸與不幸亦是傳統所謂的天意?查良釗先生在「憶西南聯大」(載『永懷查良釗先生』書中,傳記文學社,七十五年十二月出版)開篇即列出該校精神是:
「自然 自由 自在
如雲 如海 如山」
進一步他更詳述樹立在昆明校園上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上所列四點:
㈠我國歷史亙古自今,亦新亦舊。
㈡三校聯合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不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打破了「文人相輕」之惡形相。
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鍔謬巧。此其可紀念之三也。
㈣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朱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朱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之四也。
此碑樹於抗戰勝利,三校北返復校時。而查先生寫此追憶於個人第五次南渡之後,嗟嘆當年喜悅之短暫,四十年間「往事已為陳跡,環顧世局,變化多端」,北返之期許又已為遙不可及的還鄉夢所代替。查先生孤獨半生,和許多同輩人物一樣,終於埋骨於此。而西南聯大的「自然、自由、自在」的學術研究精神;「如中雲、如海、加山」的人生胸襟,今日何處可尋?
『未央歌』既是寫這樣一個校園上的故事,而昆明也確實倖免戰爭蹂躪,它所要保持的在那個幸運的地方曾經有過的「一種又活潑、又自信、又企望、又矜持的樂觀情調」也就無可厚非了。書中最真實,也較有深度的,是一些學生們的會話。如朱石樵、宴取中、伍寶笙、余孟勤和童孝賢(小童)間對話很傳神地反映了四十年前的大學生的思想內容:他們對國家、學校、課業的看法;對人生的困惑與探討;窮困中自娛的生活情趣……;種種都有他們的看法,雖然是「大學二年級(Sophomoric」的論點,卻有一種深度,一種從容,這種深度和從容必然是校園的理想風格的產物。這自然、自由、自在;如雲、如海、如山的氣度,對流亡無家,正在成長年齡的青年人該有極大的引導作用吧。這種幸運當然遠比一切外在的影響深遠。這也許就是它生存之道之一。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八期;民國77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