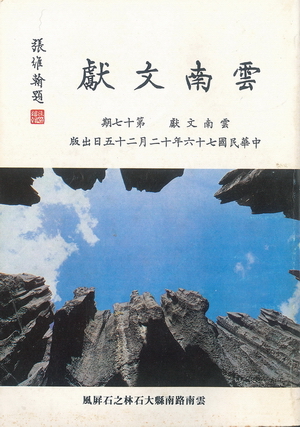懷談在昆明的西南聯大
作者/汪彝定 陳省身 易君博 黃達河
●西南聯大的自由校風
西南聯大於民國二十七年搬遷到雲南,一部分搬到蒙自,一部分搬到昆明,到了二十八年才全部遷到昆明,那時候昆明是很落後的地方,以今天生長台灣的人來看,好像是中世紀時代。
清苦的校園生活
當時房屋不夠,工學院在拓東路一帶,文、法、理、師範則在大西門舊城區的昆華師範、岑襄勤公、(岑椿萱堂)、南院,另外在大西門外蓋了一批土房子,就是新校舍,城裡頭昆華師範與南院之間有一城牆缺口可以相通,論設備與現在學校比簡直是天差地遠。我們的宿舍是一幢幢土房子,每幢住了三、四十人,高架床擺得滿滿的,電燈不夠亮,也沒有自修室,晚上在宿舍裡看書很困難,得跑到茶館或圖書館,擠圖書館是一門大學問,吃完早飯就得去排隊等開門,吃完晚飯要快步去佔位置,圖書館是個大型竹棚子,裡面是粗木頭桌子和凳子,容量小、照明差。
當時營養也很差,發給學生的米摻雜了不少石子,顏色發黃,還有酸臭味,如以今天的標準不知有多少黃麴毒素,吃了三、四年,現在想也不知是怎麼熬過來的。
宿舍裡最可怕的東西是跳蚤,因為泥巴地面,衛生條件不好,光線又很暗,通風也差,每兩個高架床對面擺著,當中空間只有一個窗洞。
那時物價天天上漲,學生靠代金吃飯很苦,早上吃稀飯配花生米、鹹菜,中午和晚上都是站著搶飯吃,第一碗盛少一點很快就吃完,第二碗就塞得滿滿的,到了月底,大家最盼望的事就是打牙祭,現在回想起來也蠻有意思的。
體育課馬虎不得
洗澡也是一種考驗勇氣的事,當年都是冷水,昆明氣候冬天比台北冷,早上水缸表面都結成薄冰,多半要等到下午比較暖和時才能洗。
穿的也很簡單,最初是黃卡其布制服,到了民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以後,學校就沒有制服了,男生絕大多數穿藍布大褂,一條卡其布西裝褲,男同學多半沒有襪子,光腳穿一雙質地很差的皮鞋,也沒人擦鞋油,那時候橡膠運動鞋很貴,很少人買得起。
西南聯大有一特殊規定,體育非上不可,沒有人在乎軍訓課,對體育課卻不敢馬虎。體育課的規定很嚴,先假定一百分每曠課一堂扣五分,請假與否無關重要,只要沒上課就扣,扣了八堂就是六十分,缺了九堂課一定不及格,每個學期都要修一門體育,四學年要修八門體育,如果有一學期不及格,下學期得補回未修兩門,畢業時,不管其他學科成績有多好,體育不及格還是不能畢業,甚至有人先到外面做事後還回學校補修。
體育課第一重要的科目是跑步,男生一定要跑,我唸書時體育老師是籃球國手,他不但規定要跑,還要跑得快,對很多人來說是件痛苦的事。體育總教頭馬約翰,是一位很洋化的閩南人,他跟學生訓話,要學生學習運動精神,我只記得其中幾條,第一是盡力:要全力投入運動,第二是認輸,按照規則比賽就得按規矩承認輸贏,第三是沒有藉口,不能說沒睡好跑不快,或是捧了一跤腿疼不能跑。離開學校已近五十年,這件事到現在我還印象深刻。
邏輯學兩位大師
另一項特殊是共同必修課邏輯學,有兩位老師教,一是邏輯大師金岳霖,分教給得很緊,另一位王憲鈞老師分數給得寬,因此形成一個怪現象,學生上課時都擠到金先生班上,考試時則回到王先生班上,我們那時都戲謔金先生的分數是他口袋裡的錢,不能給人。
在西南聯大,除了體育課外,其他課缺課不要緊,縱使有人點名也與學生成績無關,但是沒有補考制度,不及格的話,下學期重來,這在當時各校中是獨一無二的。學校內完全自由,張貼海報沒有人管,也沒人審查,學生公然貼海報批評老師教得不好亦可,只要不攻擊私人,這種自由風氣是來自北京大學的傳統,也是當時全國非常獨特的。
梅貽琦受人尊敬
西南聯大有三個校務常委共同治理學校││北大校長蔣廷黻、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其中張伯苓先生在重慶擔任參政會副議長,每年來一、兩次給學生演講;蔣廷黻先生也很少來,實際治理學校的就是梅校長,所以行政管理制度完全來自清華。
梅校長是標準的學者(雖然他曾當過一任教育部長),而且是位偉大的學者,他為人公正開明,我讀書時,同學遍布全國知名大學,所有學生對學校當局和校長,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反感和抗拒,像今天的台大也是一樣,但在西南聯大,不論是在校生或是畢業生,對梅校長都充滿了尊敬,梅校長能做到這一點,自然有其人格上讓人佩服的地方。尤其是西南聯大一向自由開放,只要不攻擊別人私生活,愛批評誰就可批評誰,但是就沒有人批評過梅校長。
關於梅先生,我再舉一例,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西南聯大在這兒舉行校友會,那時剛好是李振道、楊振寧兩位同學得到諾貝爾獎,大家非常興奮。那天同學會時,梅先生說:「這幾天人家都來恭喜我說我教出好學生來,可是你們都是我的學生,你們都知道這實在不是我的功勞,西南聯大薄有虛名,所以好學生都來了,進來的學生好,所以就有好學生出來,我所能盡力的地方有限。」這種謙虛的態度,實在讓人佩服。
謠言與學生運動
民國三十年冬天,日本人打香港,那時就有左派學生造謠,說香港快淪陷時,政府派專機接運留在香港的人,孔祥熙院長家裡連狗都上了飛機,可是我們學校的陳寅恪先生不能上飛機,這當然是謠言,後來也證明了是謠言,可是在當時,學生卻相信了,因此吵著要遊行,這就是很有名的倒孔大遊行,那時我們都很糊塗跑去參加,學生情緒很激昂,什麼人也擋不住,校門外有憲兵拿著槍上了刺刀在阻擋,形勢很緊張,梅先生站在台上聲嘶力竭的演講要學生不要去,他的聲音很低沈,那時連擴音機也沒有,當然誰都聽不見,就看見他非常緊張叫人不要去,結果學生在那見吵說:「梅先生,我們很尊敬您,可是這次我們不能聽您的話。」結果學生還是去了。我想在任何一個地方如果要鬧學潮的話,一個校長出來阻擋學生,學生會連校長一起打罵,可是那次梅校長極力阻擋,學生只是在吵校長這回我們不能聽您的話,可見他的確是很受學生的愛戴。
崇高的愛國情操
西南聯大四年,到底給了我們多少教育,我覺得也很難說,有人得到多,有人得到少,但是這四年給人自由思想的啟發是非常突出的。從抗戰一直到今天,大約沒有一所學校能夠做到像西南聯大那樣的自由主義。我不敢說自由主義好,因為假如你覺得你是一個相信自由主義者,就得同意別人有否定自由主義的自由,所以我不敢說自由主義一定好,但是西南聯大是傳播這種信念的地方。
簡單的說,抗戰時的物質生活真的苦,大家求學熱忱很高,擠圖書館時奮不顧身,而且不點名,上課非常整齊,向學之心很盛。學生之間在宿舍談話的主題,很少談到發財、做生意,大家想的是怎樣服務國家社會,我們那時愛國情操相當崇高,就好像宗教一樣。
●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由於抗戰興起,北方幾所大學││北大、清華、南開,為了遷校到大後方的方便,臨時組合而成立的。抗戰勝利後,聯大便自動結束,依然復原為原來的幾所大學。因此,我們可說西南聯大是抗戰的產物,當它經歷了八年抗戰的艱苦歲月後,也就悄然的退出了這個世界。
文理兼備的學風
聯大的實際存在,雖然祇有短短的八年,可是它也有它的特殊風格,後來並引起一些詩意的描寫和嚴肅的討論。如像鹿橋(即吳納蓀,聯大出身,現任教於美國的某大學)就是以文學筆調來描繪聯大的風貌,如易勞逸( L.E. Eastman,美籍歷史學者)就是以歷史的觀點來研究聯大的特徵。當然,每一個不同的角度,都會看到聯大的某些方面,但不一定就是對聯大的完全了解。在此,我想從學風這個角度來談談聯大。
聯大的學風,用一句話說,即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並重及融合。就科學方面來說,聯大非常重視基礎科學的教學,每年因考試不及格而遭到重修或退學的人,比例相當高。同時,規定非理工學院的學生必須選修一種理學院的基礎學科,要求也十分嚴格。這種自然科學的學習與訓練,多少會幫助學生體驗到知識的形成及科學理論的特徵,究竟是回什麼事。至於人文方面,也許由於早年北大倡導新文化運動及清華創辦國學研究所,發生了某種刺激作用,使聯大孕育出一股相當濃厚的人文氣息。當時聯大共有五個學院,各個學院的師資與研究風氣,都很整齊健全,不過各學院的學生卻特別歡喜談論文學院的教授,也愛聽文學院教授的演講。文學院所主辦的純學術性的「文史哲講座」,按期舉行演講,經常有人滿為患的狀況。中文系的某幾個課程,有時旁聽的比選課的還要多。羅庸先生的「杜詩」一課,即是其中之一。均足以顯示出來,聯大的人文風氣,的確相當濃厚。
如果說一個大學的靈魂所在應該是文理兩個學院,那麼當時聯大呈現出來的學風取向,實在值得效法。因為,經這種學風薰陶的學生,比較上說,容易洞悉學問的根,並產生追求真理的熱忱,而不為功利思想所困。
關心時政的傳統
至於談到關心現實政治,不可否認的,聯大學生也承襲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傳統,很喜歡過問現實政治。部分聯大師生常常批評時政,關心國家未來的發展。議論雖然紛紜,而重心祇有一個,那就是中國必須走民主自由的路。可是,當時的實際情形相當特殊,國民黨是執政黨,共產黨、民主同盟也有它們合法存在的地位。當政黨活動介入學校之後,引發不少政爭,甚至演成遊行、示威、罷課的事件。使學校的平靜幾乎喪失無遺,學術研究環境受到很大的傷害。於是多數教授及學生逐漸產生反感,而倡議「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主張大學應超然於實際政治之外,從事獨立的學術研究及傳播。
今天回想起來,當時的確有極少數的聯大師生,由於過分渴望自由和民主,誤信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為靈丹妙藥。他們卻完全沒有想到,中共入主北平之後,數十年來,不僅與民主自由背道而馳,而且他們自身的生命也朝不保夕,甚至被迫而死。這些少數人的遭遇,固然值得悲憫,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們的錯誤,為所有的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大教訓。
●愛國之心人人有
每個人都生活在衝突與矛盾之中,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學生也是一樣。
抗戰的幾年,有許多變化,最初學生們的反應很直接,想馬上就參加抗戰,也有人真的走上第一戰線;後來,學生們慢慢平靜,唸書也較認真,到戰爭快結束時,許多西南聯大的學生都當翻譯官,替美軍工作。
衝突與矛盾
西南聯大在昆明前後五年多,房舍很簡陋,為了紀念那段歲月,昆明曾建了兩個碑,一個是為西南聯大,一個是為任職翻譯官的一千多位聯大學生。
當時的學生情緒,很難用幾句話說清楚,學生們愛國心很重,國家弱被人欺負,當然很氣憤,另一方面,學生又很窮,政府輔助的代金,在當時很有幫助,使學生能付起碼的生活。
西南聯大的學生,是走在時代前頭一點,我認為這和當時西南聯大由三校組成,具有號召力、收了許多好學生有關。學生們的想法,和政府未必一致,劈如日本佔領香港,搶著撒退所發生的問題,就顯現了學生、政府想法不一致的情況。
其實,這也是很自然的,今天柏克萊加大學生的想法,當然和華府不同。抗戰時期面對一個大問題,就是「國、共」,到今天,這個問題仍然存在。
學生們的情緒,是衝突與矛盾的,人人都有國家民族觀念,自然不願意國家、民族「低一級」。我自己也有苦悶的感覺,可是又不能解決問題,回到研究學問的路上,與人無爭反而可以做一點事。
由抗戰時學生的情況看來,它也是一種學生運動,其實歷史上的學潮顯示,學生的看法也有道理,政府要處理實際問題,因此態度比較保守,學生們因沒有顧慮,就比較前進,在時代變化時,前進的想法往往比較有利。
中國人要站起來
談到七七事變,我想講一講日本這個鄰居,中國人不比日本人差,只要站起來,一點都不用怕日本,抗戰就是一個例子,今天,日本的經濟發展,我並不認為會長久,基於中國人的未來與利益,不能讓對日本的仇恨影響我們,更不能阻礙發展。
●千里迢迢勵志為榮
「七七」事變那一年,我是清華大學二年級化學系的學生,剛好在北平西苑二十軍兵營受軍訓,後來就隨著學校遷徙到內地。先是從北平、天津移到長沙,在湖南大學校址分幾個地方上課,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失守,長沙迭遭轟炸,二十七年一月十九日,長沙臨時大學決議再度播遷昆明。
徒步遷校千餘公里
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人人心裡都有所準備,中日戰爭早晚都會爆發,所似大家夜裡聽到礮聲響,也不覺得可怕,在學校決定入滇,三校師生的精神反而更振作,現任清華校友通訊社經理蔡孝敏當時就參加了從長沙徒步到昆明的行列,他們先坐船到益陽,然後開始沿湘黔和黔滇公路步行,走到沅陵之後,因山區土匪出沒,一路走走停停,後來找到十幾部車,師生坐了車衝過去,他們一共步行了一千六百多公里,歷時七十三天,才抵達昆明。其他的同學也輾轉到昆明會合。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長沙臨時大學改稱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在昆明,起初一切設備都很簡陋,還有拿煤油箱堆起來充當桌椅;衣食住行的物質生活簡單,不過精神上並未受到戰爭威脅,教授認真教學,學生好好把功課做好。
物質貧乏教授一流
西南聯大的部分圖書是由清華大學搬遷過去,現任外貿協會董事長張光世當時在學校任助教,他負責押運圖書,抗戰時一切貧乏,好在有這批圖書供學生閱讀。
西南聯大是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聯合,集世界名教授於一校,像物理系的吳大猷、鄭華熾、吳正之、饒毓泰、周培元、葉企蓀,化學系的曾昭倫、高崇熙、錢思亮、黃子卿、揚石先、朱汝華、蘇國楨、張大煜,數學系的陳省身、華羅庚,均為一時之選,成為聯大的特色,也作育不少英才。
造育英才舉世聞名
像李振道,當年在聯大讀書,大學一、二年級就很出眾,吳大猷先生很賞識他,就推薦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直攻博士,後來他和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獎;王浩也是一樣,受到陳省身先生的栽培,後來成為知名學者。
一晃近五十年,已成白頭翁,但是抗戰的大學生活歷歷如繪,尤其是每個人都很珍惜足遍大江南北的經驗,這是可遇而不可求,比什麼都寶貴,人人抗戰的愛國情操似乎仍澎湃在心頭!
│轉載聯合報七六年七七特刊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七期;民國76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