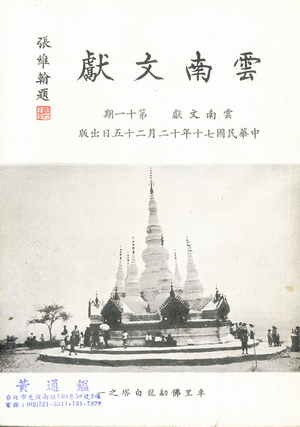雲南健兒異域奮鬬三十年
──泰北金三角游擊區去來
作者/金維純
一、「陳老闆」原來就是陳師長
看過「異域」這本膾炙人口的小說的人都知道,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後,在西南部邊區仍有一批雲南部隊,在李彌將軍統率下從事艱苦反共鬪爭。他們在完全斷絕後援的狀況下,轉戰異國叢林,歷盡了人間最悲慘的境遇。他們堅守志節與共黨鬪爭,與叢林搏鬪的故事,曾經感動干千萬萬的讀者,他們是不折不扣的鬪士。
事隔三十年,這些曾經是正規軍,後來變成游擊隊,後來又淪落為「難民」的反共鬪士,身處異域三十年,如今安在?
懷著曾經被感動的心境,記者在旅行採訪東南亞諸國途中,決意前往探訪這些飄零異國的中國人,把他們的訊息搶回祖國。
記者計劃採訪的地區,正是泰國北部邊境上一般人習稱「神秘金三角」的山區。「金三角」之所以「神秘」,除了傳奇性的游擊隊事跡外,還有關於種鴉片、販毒的種種傳聞。這種事,不親身跑一趟,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以下是採訪實錄。
游擊隊傳捷報
記者抵達泰國後,在曼谷市尋訪了三天,最後搭上一條線連絡到當地的雲南會館,透過會館的協助,找到一位「北邊來的」可靠青年,由他陪伴記者乘坐了十二小時的夜車,前往最接近游擊區的泰國北部邊境城市清萊。
到達清萊的時間是三月廿九日清晨,同行的年輕人告訴記者,報紙上刊出了大新聞,大篇幅報導游擊隊剛打完的一場大勝仗,替泰國政府攻下了二十餘年政府力量無法到達的考可山區苗共基地。報紙上的標題是這樣的:「盤踞隆塞考可山廿餘年共黨數十營寨被掃平,率饒勇戰士激戰前九三師長陳茂修厥功至偉。」
既然發生了大新聞,又有這幅標題引路,該先找什麼人進行訪問,是件再清楚不過的事了。
在記者的觀念裡,要找這位剛打完仗返防的游擊隊師長,總該穿過重重的關卡,透過層層的通報,最後在深山峻嶺的營寨裏見面的。
事責不然。同行的年輕人帶著記者在清萊城一路打聽,穿過大街小巷,人潮車陣,最後走進街邊的一家小電器行。電器行老闆遞給記者一張名片,名片上款印著××電器行,下款赫然是三個大字──陳茂修。
百戰英雄現身
仔細打量這位陳老闆,豈不正是報紙上刊載的「百戰英雄」前九三師師長?
這種見面方式不合記者原先的想像,驚訝之餘,記者努力拋棄成見,準備接受新觀念。畢竟,游擊隊不是正規軍,而且這支盛名在外的游擊隊也可能不同於一般觀念裏的游擊隊。
「陳老闆」看來五十歲上下,但他說已經六十出頭。他身穿居家便服,頭髮梳理的整齊光鮮,除了眼神中略顯英氣,舉止神態中嗅不出一絲軍人氣味,更不像剛打完艱苦戰役歸來的戰士。他看起來更像個殷責的小老闆,尤其是因為他背後的牆上掛的區額不是「用兵如神」,而是「大展圖鴻」的緣故。
聽說記者是從臺灣來的,他倒沒有什麼驚訝的表示,只說「辛苦,辛苦」就好像記者是隔壁過來串門子的鄰人一般。(後來有人告訴記者,這種遇見任何事都不當一回事的氣質,正是所有游擊隊弟兄的共同特徵。因為他們歷盡滄桑,不大容易激動,早已「日光之下無新事了」。)
「陳老闆」操著一口雲南腔,談起話來言簡意賅,倒是典型軍人作風。他知道記者希望瞭解這次戰役的經過,打開話匣就直截了當做起「簡報」來:
「……二月九日我們從金勘機揚坐大型運兵機飛往彭世洛集中,十六日開始分五路入山掃蕩,第一階段的任務是一方面率制敵人,一方面招降苗共,至二十八日告一段落……第二階段從三月四日開始,兵分兩路,第一路五號下午攻佔上考雅,第二路八號攻佔下考雅,敵人沿途阻截頑抗,苦戰二十天……。」這一流水帳式的「簡報」距離臺灣的讀者太遠。
陳師長作簡報
記者截住了話題,開始發問,他一一精簡答覆:
「這次打仗我們總共出動了四百餘名弟兄,最老的六十八歲,最小的十四歲……」
「這個苗共嘛,盤據考可山區二十幾年囉,以前泰國政府軍進剿了許多次,都打不下來……」
「考可山很險囉,拾起頭來看,幅子都會掉的;工事做得又堅固黠不好打的……」
「他們實力不錯十二歲以上的男女都經過軍事訓練,全部武裝起來有三千多人,武器大部分是中共製造的衝鋒槍和十響步槍,另外有五七無後座力砲、六○迫擊砲和大型地雷……基地裏還有軍事學校、小型兵工廠、被服廠、醫院和倉庫……當然,這些倉庫都被我們放火給燒了……」
「你問什麼事最辛苦?噢,主要是補給不上,四天四夜沒吃沒喝,有時候擠芭蕉樹的汁解渴,更慘的時候,弟兄們只有喝自己的尿,真是室前的艱苦……」
「有沒有什麼感人的故事?一時倒想不起來……」
作戰極為艱若
「打勝仗的原因?大約有幾點:第一,我們的官兵有犧牲精神;第二,大家團結一致;第三,絕對服從命令……」
我們談話的地點是電器行的後進,前廳傳來的流行音樂震天價響,和談話內容頗有點不大相稱。訪談之間,店裏顧客進進出出,玩耍的小孩子穿來穿去。其間還來了位提著一籃水菓的中年婦人,跨進門就尖著嗓子說:「恭禧啊,又打了個大勝仗士」陳師長替記者介紹:「這是劉家大妹子,來道賀的。」
大概是覺得自己剛才的說法有點八股了,陳師長立即解釋:「我說的沒有『擴大』,事實是如此啦。」照記者的看法下他有關戰況的描述不僅沒有「擴大」,簡直是有點「縮小」了。他談起戰況的口氣,就像莊稼人說「今天早上到田裏施用殺蟲劑若干,殺死害蟲若干」一樣的稀鬆平常。
泰志願自衛隊
陳師長出身黃埔軍校十八期,在大陸上參加過抗日、剿匪,淪陷後又追隨李彌將軍轉戰泰、緬、寮邊境,直打到八年前才算安定下來。他告訴記者,最近八年來,游擊隊主要探取守勢,大部分部隊駐紮在泰、寮邊境的帕猛山、萊弄山一帶,負責防止寮共入侵。偶爾邊境其餘地區的共黨鬧得太凶,也出兵巷泰國政府清剿,但規模都不算太大。他說,這次記者一到泰國就碰到打仗,算是事有湊巧。
游擊隊目前的正式稱呼是「泰國志願自衛隊」,受泰國軍方零四指揮部節制。陳師長平時除了經營電器行外,也兼任零四指揮部的連絡官,「同泰國朋友一塊辦事」,算是游擊隊在泰方的代表。他出任這職位,據說是因為他娶了泰國妻子,精通泰語的緣故。他是老一輩游擊幹部中的泰國通。陳太太是個富富泰泰的中年婦人,一直笑吟吟地坐在陳師長身邊聽他說話,狠少搭腔,看起來夫婦感情甚篤。
目前住在清萊城的雲南人不少,多半是當初一塊隨軍從大陸出來的。陳師長在地方上算個有影響力的人,親朋好友有事情都不免找他相助使他在不打仗的期間總為朋友的瑣事奔走。他倒是樂此不疲的,對記者說:「這不僅是助人為樂,這賜做助人為榮!」他覺得這句話頂重要,重覆說了三次。當然,可以想見的是,他之所以常能替親朋解決問題,是因為他常替泰國政府打仗的緣故。
陳師長說:「所以我們這次剿共,不是以中國游擊隊的身分,而是以自衛隊的身分,奉泰國最高統率部的命令去的。我們住在泰國,有責任保衛泰國。」後來有人告訴記者,以前游擊除替泰國政府打仗,通常對外不公開,這次報紙大篇幅報導,有點見不大尋常。也許,游擊隊領了泰國番號奉命出擊,就是不尋常的原因。
待遇非常微薄
替泰國政府打仗,待遇如何?陳師長告訴記者,作戰期間,每人每天三十六銖(約合臺幣六十五元),糧餉包括在內,官兵待遇無差別,負傷與陣亡者比照泰國陸軍待遇撫卹。另外,由於這次打了場漂亮的勝仗,參戰官兵各發獎狀一紙。「發給我們高級軍官的是一面獎牌,高級些,可以擺在桌上。」陳師長說。
打仗不是辦家家酒,經常要人命的。這次出擊游擊除犧牲了二十幾名弟兄,負傷的也有二十幾名。全身而返的,每人只能領到一千多銖泰幣。看起來,這不是樁上算的買賣。
記者沒來泰國以前,聽過一種說法,說是泰國邊境上的游擊隊已經變成泰國政府的傭兵。如果真是傭兵,拿這種微薄的待遇打仗,簡直不可思議。促使游擊隊上戰場拼命的真正原因是什麼?記者有個直覺:這答案在清萊城不大容易找到,還得到山區裏走一趟。於是記者匆匆整理行裝,趕往游擊隊指揮部所在地的美斯樂山區。
二、在美斯樂山村會見了雷軍長
美斯樂山村,是段希文將軍生前坐鎮的游擊隊指揮部。段將軍去年七月間去世後,由雷雨田將軍接任指揮官,坐鎮此間指揮各防區的部隊。在游擊除駐防的山區各基地中,無疑地美斯樂並不是前哨,而是心臟地區。
山村景色荒涼貧瘠
從山腳通往美斯樂的山路,全是飛沙沒天的黃泥路,據說雨季期間,簡直不堪通行。沿路兩邊有不少苗族居住的小茅屋,附近的山丘則被遊耕的土著燒得一片片焦黑,使山區的景觀除了荒涼、貧瘠外,又平添一份為生活苦鬪的淒慘。
在靠近美斯樂的山路旁,有座苗族矮茅屋,幾個衣著襤褸,看起來像苗人的小女孩蹲在屋前玩泥巴,記者趨前拍照,正準備按下快門之際,小女孩開口了:「喂,你從那裏來,是不是中國人啊?」竟然是道道地地的雲南話!在那樣的時室場合裏,這幾句話真有萬鈞震撼力,讓記者心頭直發毛。因為小女孩的口音清清楚楚地說明了,她不是苗族子女,而是游擊隊後裔。這是怎麼回事?難道山區裏的游擊隊已經變成了高山族?人還沒有到美斯樂心頭已經蒙上陰影,急於想知道這個山村到底是什麼樣的景觀?
美斯樂山村的景觀比沿路上的苗族村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一條起伏不平的黃泥路把山村分成兩半,路邊的住戶家家開個面對路邊的黑窗口,窗枱邊放上幾捲手工製的土煙、幾樣雜貨,就算個小店舖了。村中比較像樣的住屋多半是竹子編成的,大部分則以茅草做屋頂。
雖然山村入口處用長竹竿做了個柵欄,看來像個關卡,但門禁並不森嚴,只要不是可疑的陌生人,都能隨進隨出。村中來往的男女老少,腰間掛著短刀的,多半是附近山區的土著荷槍實彈的人倒是沒有。山莊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貧窮、寂靜。當然,在外地人的眼光裏,也不免有些詭異的神秘氣氛。神秘的原因,除了有關游擊隊和鴉片的種種傳聞外,最重要的,是它在外觀上像個典型山地部落,住在裏面的人,卻不像山地居民,而是不折不扣的文明已開的內地人,使得氣氛有些不太協調。
雷老將軍溫文儒雅
記者在山莊裏遇見的第一個揹槍的人,是雷雨田指揮官住宅前的警衛。這位年輕的警衛汲著雙日本拖鞋,穿一身鬆垮垮的便服,發現記者想巷他拍照,遠遠就閃進了樹叢裏。
雷軍長約莫六十餘歲模樣,戴了副老花眼鏡,穿著很隨和的便服。他住在半山坡的小木屋裏,屋前有細心栽培的花草,屋裏擺設雖然簡陋,卻流露著一般安閒舒適的韻味。要不是指揮官的頭銜擺在前頭,他看來倒更像個安享晚年的退休老人。
握手寒喧之後,他回答記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原則上,美斯樂村不暴露武裝,因為依照我們與泰方的協議,這個村落不是我們的防區,我們也不希望引起外界誤會。但實際上,因為指揮部設在此地,又要協助維持附近山區的治安、肅清搶匪,不得不有防衛的。」
與泰官方約法三章
十一年前,游擊隊曾與泰國官方舉行一次大規模談判,當時泰方曾要求游擊除撤離美斯樂,協商結果是游擊隊把部分部隊撤往更偏遠的山區去清掃苗共,另建基地,指揮部與大部分眷屬則仍留居山村,只保持小規模防衛力量。但從此以後美斯樂山村算是正式劃歸游擊隊自治,擁有完整的土地使用權,外人入山還須得到指揮部的同意。
「自從談判後,這十一年來我們與泰方關係很好,雙方都建立了信心。在這之前啊,哈,美斯樂四面八方都是工事,哄做『立體防禦』,因為誰也搞不清敵人會從那邊來。可以說,除了自己人,都可能是敵人,真是草木皆兵。」雷軍長說。
「草木皆兵」時代結束後,美斯樂居民開始專心發展農業,種稻子、燕麥、玉蜀黍、咖啡、桃子、李子、柿子……可說是應有盡有。最近有人從香港引進了板栗的種子,開始試種。八年前,泰國國王特地賜下一批茶種,試種結果,尚算成功。目前泰國官方宣布美斯樂是北部的最大人工茶區。嚐過美斯樂茶的人,都說味道與臺灣茶很接近。
但是記者親自觀察的結果,發現美斯樂附近絕少平地,一眼望去,盡是坡度很陡的斜坡,外露的土層又以砂質土居多,十分缺乏發展農業的條件。
發展農耕條件很差
提起這件事,雷老軍長只有嘆氣。「當初部隊迫不得已轉來泰國,大家連地圖都懶得看,誰管那是什麼地方?只一心想打回大陸,那還料到最後要終老異鄉?」他說:「我們在美斯樂建基地,是因為這見山高勢險,易守難攻,完全著眼於軍事考慮。到後來開始搞農耕,才發現土質奇差,坡度奇陡,根本不是塊料。不是料又有什麼辦法?難不成還帶著槍另外佔一塊好地?不成啊!」
在這種條件下發展農耕,其艱苦不問可知。土質差再加上斜度陡,結果是作物時常缺水,灌溉系統又做不起來,種下的茶和菓樹只好死活由天。就以茶來說,前幾年栽下了四百萬株,目前成活的不到一半,去年收成了五千公斤乾茶,以每公斤六十五銖泰幣賣出,全部收入不過亡三十萬銖。平均下來,每戶人家才五百銖收入(合臺幣九百元)還得扣除栽培的成本,這樣的收成怎麼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
但是雷軍長說,他們正研究如何提高技術、改良包裝,希望以後能賣好一點的價錢。他又說,估計今年收成會好轉,也許可以收到兩萬公斤乾茶。兩萬公斤,可是去年收成的四倍啊!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在一年內提高四倍收成?看他臉上自信的神情,記者不忍心再問「為什麼?」。
但是有個問題不能不問,那就是外傳的有關金三角游擊隊種鴉片的事。這個問題,雷軍長顯然被問過很多次,他絲毫不感詫異:「對啊,外邊人一提金三角,就說我們美斯樂,好像我們發了鴉片財,遍地黃金。你這次既然來到這裏,不妨仔細瞧瞧,看看村裏人過的是什麼生活?這應該是最好的答案。
雷軍長說,他對有關販毒的攻擊,早就習以為常。外邊的一些左派人士,不僅歪曲報導,有時候還捏造事實栽贓。他說,就在三年前,曼谷茱拉大學有些左派學生搞圖片展覽,弄了些罌粟花插在茶園裏拍照,硬說這些照片是在美斯樂的茶園裏照的,指控游擊隊以種茶掩護種罌粟。「從那以後,每逢泰國官員來訪,我都笑話他們,叫他們在茶園裏找找,看能不能找出棵罌粟花。」他說。
種煙之說只是栽贓
雷軍長又說:「那些人?什麼帽子都拿來給我們戴,除了說我們種煙,還說我們飯毒、走私,好像我們是無所不為的大盜。」後來,自然有些慕名而來的外國記者跑到美斯樂查證,結果當然什麼也沒找到,於是又問雷軍長:「如果你們真沒幹這種事,為什麼外頭那麼多人這麼說?」問得他只有搖頭嘆氣。事實上,游擊隊員們並無行動自由,除了在泰國官方認可的少數山區謀生外,其他地方是不能隨便去的。在這種狀況下,那裏管得了外面人有什麼說法?
記者又問他,是不是金三角其他地區種煙,栽到了游擊隊頭上來?他回答說:「老責說,我敢保證我們自己人駐紮的區域絕對沒有這種事,出了我們的區域,那就難講囉。」
第二天,村中有位雜貿店老闆告訴記者,段將軍生前曾經下過禁令:凡抓到游擊除的人與鴉片產生任何關係,一律槍斃。這條禁令執行得很嚴厲,絕對沒有人敢觸犯的。
難怪雷軍長要說:「上帝專門懲罰好人。」的確,那些說美斯樂種煙的人,都該親自去看看他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三、楊副師長說:只有打勝仗們能生存
翻山越嶺地老遠趕來採訪游擊隊,倒沒想到與指輝官一見面就大談起莊稼事。但是雷軍長說:「你要知道,我打仗打了這麼多年,直到八年前才算安定下來。腳是安定了,心可不安定,心裏經常有說不出的苦啊。你瞧瞧,這麼一大夥人,吃的、穿的、安全、前途,在在都是問題,不操心想辦法怎麼行?」
退此一步即無死所
雷軍長出生南京憲兵學校,原先在第卅九軍雲南部隊裏當營長。他一生經歷三次大撤退,第一次是抗日時從南京撤守,第二次是淪陷時撤出中國大陸,第三次是從滇緬邊區撤來泰國。「沒有第四次了,退此一步即無死所。」他說。
他目前的煩惱是:「當初在軍事學校裏,我就沒學過『無補給帶兵』,這一課,現在好了,一面帶兵還要一面做生意、種田,處處要人操心。我一生革命到老,家裏頭的人都給共匪殺光了沒想到現在倒成了管家婆。」
提起做生意,雷老軍長想起了一個有趣味的話題。他說,泰國政府經過調查以後,已經宜布美斯樂為觀光區,但是目前尚未著手規劃,對美斯樂村民來說,這倒是一件大事。因為農耕條件既然不佳,不太容易維持基本生活,發展觀光說不定是條換取生活所需的明路。雷老軍長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他仔細地數說美斯樂發展觀光事業的前途:
「美斯樂名氣是不小囉,外面人總覺得我們這見是敏感地帶,總認為這裏有鴉片煙,又神秘又不可思議……更何況又是泰國最大的茶區和松林區……」
「但是,最重要的當然是交通和電力,我們氣候還不錯,就差上山那條路不好走,灰塵大、雨季不通……現在泰國政府答應要替我們舖柏油馬路,等路鋪得差不多,也許可以接上電力……」
一旦交通與電力問題解決,我們馬上著手蓋小型旅館,要地方風味的,像現在美斯樂學校那樣的蓋法。對,以後種果樹也要力求美觀,配合觀光需要……」
有意發展觀光事業
投資是沒間題的,目前很多人有興趣投資,還有人肯拿出兩千萬蓋旅館,必要的時候,當然,也可以邀些同鄉來投資……
「問題是,美斯樂現在名義上是我們指揮部自治,實際上歸泰國統帥部管,統帥部不簽字,業者投齊產權沒保障,誰還敢來?唉,很多事啊,在法律上有問題,又找不到人負責……」
「泰國旅遊機構總裁有一次說,要派手工藝師傅來美斯樂輔導,教我們眷屬做些小土產,……。到時候,我們自己也弄個合作社,推動手工藝品的生產……」
「總而言之,搞觀光事業我們能力有限,還得看泰國政府肯不肯支持……」
雷老軍長沉浸在觀光事業的美夢中,一會見點頭,一會兄搖頭。看起來,美夢距離實現還有相當距離的樣子。
無論如何,就現實來看,美斯樂村民的生活已經瀕臨最低點,觀光事業,無疑地,是大家寄予無限希望的一條出路。
實際上,游擊隊以前管制外人入山,非等閒人物不敢貿然上山持虎鬚,後來漸漸放鬆了管制,很多人還是不敢來,但是它的神秘色彩也的確吸引人,一些膽兒大或熟悉內情的人,也偶爾在好奇心驅使下跑來瞧瞧。曼谷有一些旅行社,甚至以神秘探險為號召,招攪少數不怕事的外國觀光客,帶他們到這見走馬看花。當然,收費可是不低,就這樣東拼西湊,美斯樂也算有了雛型的觀光事業,前陣子還蓋了間簡陋的小旅館,也常人滿為患。難怪雷指揮官對觀光事業抱無限希望。
部隊從未吃過敗仗
雷老軍長整天憂心部隊眷屬的生活問題,與他談話,不大容易扯到打仗的事兒上。記者正準備告辭,沒想到一位年輕人一腳跨進大門,行一個漂亮的軍禮。雷軍長介紹說:「這位是楊維鋼副師長,這次作戰的前線指揮官,昨天剛返防的。」衝著這句話,記者立刻打消了告辭的念頭。
多了一個青年軍官參加談話,氣氛立刻活絡起來。記者首先向楊副師長道賀,他說:「沒什麼,別人可以打敗戰,我們可不行。」這話怎麼說?「有人說我們部除從來沒吃過敗戰,實際上大家是咬緊牙苦撐。我們不能敗啊,敗了後果不堪想像?」雷軍長在旁邊補充:「我們的政治和法律立場都是打出來的,要是有一天不能打了,還有什磨混頭?」他說:「我們什麼地方合法啊?不扛槍入境都不合法,何況扛了槍?」
他又說:「舉個簡單的例子,你瞧這美斯樂,這麼多年就沒人敢來騷擾,因為外邊人都曉得我們不好惹。我們是惡名遠播。這叫做:『虎不傷人,談虎色變』。我們能吃苦,作戰凶悍,沒人敢來囉囌的。」
克敵制勝以求安居
雷軍長解釋的理由,只能算是最簡單的表面說法。實際上,游擊隊至令不得不打仗,又不得不打勝仗,可能還有更微妙的原因。其中比較容易理解的,像是泰國政府幫忙修路啦,開闢觀光區啦,難免都與游擊隊替泰方打仗有關。更複雜些的,就得從頭說起了。
原來雲南游擊隊進入泰國雖已三十年,但直至目前為止,雲南人聚居的各山區與平地村落,仍然通稱為「難民村」。換句話說,他們已經在泰國做了三十年難民。既然仍是難民,就不得享受任何泰國公民的待遇。這其中關係最重大的一點,是「難民們」不得擅自離開指定的居留地,如果違反規定潛入城市謀生隨時可能被捕下獄。
前面說過,目前難民們聚居的地點,幾乎久缺謀生的條件,於是乎,設法取得泰國公民權,就成為難民們(尤其是第二代青年人)謀求生存發展的唯一手段。記者上山之前,曾到北部邊境的一個難民村訪問,那兒有些年輕人向記者發牢騷,說泰國政府用發給公民權為餌,誘使游擊隊替他們作戰,卻握著證件遲遲不發。因此,公民證變成了一個胡蘿蔔,始終掛在游擊隊的鼻子前面,看得吃不到。
記者問雷軍長有關公民權的問題。他說,以前的總理克里安薩曾經親自到美斯樂訪問,答應讓村民全體入籍,後來的政府規定又嚴格了些,說是十三年前參加過一次大戰役的戰士(包括家屬)優先發給,其餘的以後再說。於是指揮部把當時參戰人員造了冊子,總共兩千多人(不到指揮部轄區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泰方對這批名冊也批准了,但是到目前已將近兩年,公民證還沒發下來。
泰遲遲不發公民證
有些比較急躁的年輕人對這件事有他們自己的解釋。他們說,泰方遲遲不發公民證,是怕游擊隊員拿到了公民證,紛紛下山謀生,以後要再有事找游擊隊幫忙,怕湊不出兵源。所以才拖了又拖。把游擊隊拖在北部山區裏替它守邊防。
像這些事,當然有其在國際間題和泰國內政上的複雜性,記者短時間內也無法查證清楚,只有兼聽各方說辭。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公民證對山區「難民」未來出路有絕對重要性,而這件事到目前還沒有肯定的答案。雷軍長說:「泰國政府對我們還是有優待的,其他人申請入籍都要收費,我們可以免費。」
三十四歲的楊副師長對談作戰的話題比較感興趣,經不起記者追問,開始談起前幾天考克山戰役的情形,在作戰細節的描述上,又比陳師長所說的更精彩些。
四、「兵窮而後善戰」
三十四歲的上校副師長楊維綱,是游擊隊第二代青年中的悍將。當初部隊從大陸撤出時,他還是個被褓中的奶娃兒。後來在隨軍學校裏唸到初中畢業,十六歲起正式參軍,南征北討,經歷大小戰役無數。
楊副師長身先士卒
近年來,老一輩游擊隊將領人才凋零,運籌帷幄猶可,衝鋒陷陣的事兒已經做不來了。於是,他成了前線帶兵的主要人物,近年來的重要戰役,都是他親自帶兵打的。前幾天帶兵打苗共兩個月,回來體重竟然減輕了十幾公斤。
他談起打苗共的經過,如何被苗共包圍,如何組織敢死隊突圍,如何用手榴彈猛攻山頭,如何看到弟兄們在身邊倒下,負傷、陣亡……把戰況的慘烈,描述得歷歷如生。他說:「最後決戰在考雅山頂峯,我派弟兄二十四名組成敢死隊衝鋒,結果一排槍響,陣亡了兩名,負傷十九名,只有三名弟兄全身而退……這些苗子啊,槍法真好,我打過中共、緬共、寮共、就屬苗共最難打,他們槍一響就著人,很少放空槍的……」
記者先前在山下聽說,這次作戰人員年齡最小的只有十四歲,問楊副師長是怎麼回事?他說,游擊隊每同作戰都帶幾個小孩同行,算是戰地訓練。「但是有時候小孩真管用呢,尤其是被敵人圍困的時候,小孩目標小,動作又快,在山上跑起來跟個猴兒一樣,來回送補給,敵人的炮火就挨不著他們的邊。」他說。
楊副師長說得興起,話題溢出了這次戰役。他掀起褲腳,露出小腿上碗口大個疤,說是前年作戰負的傷。他說:「那一次啊,真慘!兩個多月打了四百場戰役,我們出動五百多人,受傷同來的倒佔一半以上,戰死了近六十名弟兄,是近年來最慘的一次。」
在記者感覺上,前年那揚「近年來最慘」的戰役,好像是說溜了嘴跑出來的。其中可能有些大家都不願再提起的隱情。結果在記者詢問下,副師長道出了原委。
原來前年那次作戰,倒真是傭兵性質,是為了錢不得巳出兵的。
作戰的原因,是泰國政府計劃在北部修一條公路,由一家私人建築公司承包了築路工程。等那家公司開始舖路後,才發現沿路都是苗共,路還沒開始修,苗共就襲殺築路人員,破壞築路設施,弄得公司損失慘重,泰國軍方去剿了幾次也沒效果。最後公司想到美斯樂有隻善戰聞名的游擊隊,就派代表前來接頭,打算出錢僱請游擊除代為清剿。
採取以戰養兵政策
當時游擊除正處於最艱苦時期,苦做苦吃,面臨生存危機。為了解決迫切的生活問題,指揮部乃斷然決定採取「以戰養兵」政策,與該家公司商談出兵條件,最後談出來的條件是:作戰期間部隊每人每月二千五百銖薪俸(合臺幣四干五百元),負傷者由公司包醫,陣亡者撫恤五千銖泰幣,作戰所需彈藥由游擊隊自理。
結果游擊隊首先派出兩百人,沿著公路預定路線清剿苗共基地,後來實在應付不過來,又加派三百人。兩個月苦戰下來,拔下的共黨基地太多,無兵可守,只好再度增兵,才算把合約交代完畢。
「那次的敵人比想像中頑強太多,超出了合約的範圍,但我們為了維持部隊的聲譽,拼死也只好拼到底。卻沒想到,這個公司竟然不講信義,到今天巳經一年多了,該付我們的錢還沒付清。」雷軍長在旁補充。
結算下來,那次作戰兩個半月,第一月應得款的總數是五十萬銖,第二個月七十五萬銖,剩下的半個月六十萬銖。但是游擊隊在戰役中打掉了二十多萬發彈藥,花了一百多萬銖才買回來。已經是稱虧本生意了,沒想到公司又要賴,薪餉既沒付清負傷人員又不包醫。楊副師長是那次作戰的指揮官,他掀起褲管說:「你瞧,槍彈從小腿肚中間穿過,住院五十八天,花了五萬銖醫療費才萬幸沒變成殘廢。結果公司卻不肯付錢。」
雷軍長也說:「那次作戰還造成不少弟兄重傷殘廢,有的腳打斷,有鼻子打掉,他們喪失了謀生能力,由部除養活,這種錢怎麼算法哪?」他不斷喃喃地說;「這是萬不得巳,唯一的一次。這種事不能再做了。後來很多人來僱我們出兵我都一口回絕……」身為部隊指揮官,籌不到部隊的糧餉,迫不得巳讓弟兄為生活去打仗,又看到弟兄斷手斷腳地回來,他心中的悽楚,又豈是外人所能體會於萬一?
種地收成支應軍糧
戰爭必然是慘烈而恐怖的,但為國家或信念而作戰,心理上總還有所交代。為錢打仗,該是所有戰爭中最悽慘的一種。試想,當游擊隊弟兄們在戰場目睹血肉橫飛的揚面,再想這一切只不過為了每天一百五十塊錢的薪餉,心裏頭是什與樣的滋味?
為了這麼點錢就肯出兵打仗,游擊隊平常過的到底是什麼生活?雷軍長說,從十一年起前,部隊開始接受泰方少量的津貼,這筆每人每月三十六銖泰幣的津點,十一年來未曾調整,至今已經幾乎不管用了。
當初部隊進駐泰國邊境之前,還以保護過路行商的名義,收點「護山費」,勉強維持開銷,接受泰方條件後,護山費不能收,津貼又不夠維持,只靠自己種地的收成支應軍糧。至於軍餉呢?收成好的時侯,還能發點零用金,收成不好就三餐難以為繼了。
在這種狀況下,部隊的員額也時多時少,隨經濟狀況而定。雷軍長告訴記者,他們這一支部隊當初進入泰國時有三千六百人,三十年來進進出出的人數有好幾萬,最高峯時曾多達一萬五千人,到目前只保持一千六百名武裝人員其餘的一部分遣散專事生產,另一部分則在兩次大撤退中送往臺灣。
他說:「我們部隊的聲望高,只要有錢改善待遇,兵源是不愁的,一招呼人就回來了……但是照今天這種狀況看,只能維持一天算一天,到最後要是維持不下去,也不能說是個人的問題。」這些話,很能透露出這位老軍長心頭的驕傲和負擔。
但是即使在這種狀況下,美斯樂的名氣仍然很響亮。雷軍長拿出一些珍藏的照片給記者看,裏面都是些各國要人來訪的紀錄。其中包括美國、德國、日本的軍事專家,各國駐泰武官和英國參謀總長兼陸軍總司令。他說:「這些人都是來研究,為什麼我們閑了卅年,仍然不消減?,為什麼我們打了卅年,至今還不吃敗仗?」
全世界最窮的部隊
後來,楊副師長與記者談起這個問題。他說:「我們能打仗的理由,是別人學不會的,因為他們沒吃過我們吃過的那種苦頭,他們也吃不起那種苦頭。」這旬話倒是一語道破,解釋了游擊隊善戰的原因。「兵窮而後善戰」,這支善戰的游擊隊,大概是全世界最窮的一支部隊了。
另一位山底下的朋友也有中肯的觀察,他對記者說:「你別瞧這美斯樂村,要是有一天打起仗來,槍林彈雨地往下落,準不會有任何人亂跑亂叫,它會安靜的跟座死城一樣,等敵人攻進村裏,才會遭遇最頑強兇猛的抵抗。」這種說法頗合兵法要訣,「徐如林、疾如風」,面對槍林彈雨而不大驚小怪,正是他們不吃敗仗的原因。
五、他們渴望來自祖國的精神食糧
記者逗留美斯樂山村期間,借住在楊副師長家中。晚上我們剪燭夜談,他拿出這次打勝仗泰國政府頒發的獎牌給記者看小小的獎牌上寫滿了泰文,記者看不懂,問他,他竟然也看不懂。後來我們找了個懂泰文的人翻譯,才弄清楚了上面的意思。
這面獎牌是他出生入死贏得的唯一報償,他卻無法瞭解上面說些什麼,說起來,實在是件很諷刺的事。這件小事的背後,豈不象徵著整個游擊隊處境的尷尬?
堅決反共矢志不渝
當然,這支部隊雖然始終堅決反共,如今在泰國境內駐紮三十年,不能也不允許再說它是中華民國的部隊了。目前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常派人前往探問,在某種程度上給予生活上的照顧,也是在泰國政府的容許下進行。但是,基本上他們仍是中國人,偶而替泰國政府打仗,身份卻並不明確。
長吁短嘆地與副師長談到深夜,他拿著蠟燭領記者到臥室就寢,清晨起床,才發現屋角處斜靠著一排衝鋒槍,床頭和牆頭各吊著一把手槍。聽到隔壁發出像是鐵鍊拖地板的聲音,轉過去一瞧原來副師長正與一長髮青年蹲在地上數子彈。數完子彈,長髮青年用麻布袋仔細包好,揹在背上騎摩托車揚長而去。
副師長家中有兩名看起來像傳令兵的便裝青年,他們手腳很快,一大早就把家中的黃泥地洒掃得像軍營裏一般乾淨,然後抱著副師長的孩子餵奶瓶。
副師長太太一大早忙著餵猪、劈柴、裏裏外外團團轉,這其間又來了些提著空酒瓶前來打酒的苗人,她熟練地轉進客廳裡間,挪出一隻大酒缸,蹲在地上一勺勺灌滿那些空酒瓶,只收了幾個零角的酒錢。那缸酒,是她自己種的玉蜀黍釀成的。
副師長平時不打仗期間,經常長途跋涉於部隊各防區之間,督導訓練,無暇為家中生計從事生產。家裏的生計,就靠太太養猪、種田、釀酒來維持。他沒有訴苦,但是記者看得出來,日子過得十分勉強。
小本生意進賬無多
從副師長家裏的生括,一直到整個村落的營生,記者都張大眼睛仔細瞧。從一大早開始,附近山區的苗人、阿卡、擺夷、卡瓦、綠索、洛黑、碰弄各族的山胞,都長途跋涉陸續趕到村中來,把村中那條黃泥幹道變成了臨時小市集。
這些土著老遠趕來村裏,有的沽兩瓶酒、有的買幾擔土煙,有的抓幾棵青菜、幾兩豬肉,有的在食攤上吃碗涼麵,又怱怱趕同山區去了。看起來,他們的購買力相當貧乏。記者看到一位昔人小女孩,在小店裏愛不釋手地把玩一隻粗糙的玩具小浪鼓,她父親則「與店老闆」比手劃腳地講價錢,鬧了半天,最後還是沒成交。
有些村中人家,在窗抬上擺幾捲土煙,幾樣雜貨,家裏人整天守著,一天下來收入不過幾銖泰幣。村裏頭最大的一家雜貨店,看起來稍微有點「店鋪」的規模?老闆告訴記者,一天收入換算成臺幣還不到兩百元。
像這樣進賬可憐的營生,村中人還怕沒得做。除了固定的小市集外,許多人還把雜貨綑在騾子背上,駄到緬甸山區去兜賣。可以說,除了利用美斯樂所可能發展的所有謀生方式外,村中人已經用盡了一切可以用血汗換錢的辦法。但是結果,生活還是艱苦到相當程度。
家庭工廠難望實現
由於記者的「臺灣經驗」作祟,忍不住向村中人建議:為什麼不搞些「家庭工廠」,弄點小型手工業來做?他們對這項建議很感興趣,但接下來紛紛提出的問題,可把記者考倒了;材料由誰供給?技術問題怎麼解決?誰來收購製成品?收購以後賣給誰?畢竟,泰國的條件不比臺灣,發展「家庭工廠」還有些複雜的問題要克服。
除了看得見的謀生方式外,另外有些看不見的進賬。村中人告訴記者,許多耐不住寂寞的年輕人,悄悄潛入泰國城市裏謀生,他們在城裏結交泰國朋友,搞當地社會關係。其中比較有辦法的,都設法弄張黑市身分證,沒辦法的則擔心害怕,在城市打一天工算一天。這些年輕人,總存些錢寄回村裏,成為鄉中父老生活上的重要貼補。
剛打完仗的楊副師長,隨著記者在山村裏逛,路旁總有些熟人翹起大拇指誇他:「這次打得好啊!」還有位在路邊擺麵攤的寡婦說:「等會你們一起來,請你們吃碗麵。」奴此而已、作戰是怎麼同事?大家太清楚了。作戰是為了什麼?也都心裏有數,不必多費唇舌。一位村民告訴記者,這村子裏的居民都知道,部隊出去打仗,是為了大家能安靜地吃貝粗茶淡飯。大家相伙為命,對出去作戰的軍人,都有一份說不出的敬意。
在村中的路上,常會遇到些走路一跛一跛的年輕人,每次記者都問到師長:「是不是作戰受傷的?」他總點點頭,不說什麼話。在經過村裏一家小理髮店的時候,他對記者說:「在這裏巷人理髮的,是幾位作戰受重傷的弟兄,多半兩腳殘廢,不能走路了。」記者沒再追問他,也不好意思進店裏去瞧瞧。在這村裏,好像你每問一個問題,都會觸到別人的隱痛處。
安貧樂道謹守禮教
這個游擊隊村落裏的人,作起戰來比正規軍更強悍,生活情形像難民,觀察他們的舉止行為,又在泠漠之中處處流露著屬於中國人特有的教養馴在這個村子裏人你看不到那種舉止粗鄙的人,聽不對有人說話帶三字經,更不會醮見任何人縱酒高歌、好勇鬪狠。說實在的,這些游擊隊實在不像游擊隊,他們一個個都斯斯文文的、安貧樂道、謹守禮教。在這裏,沒有飄揚的軍旗,沒有閃亮發光的勳章,沒有豪邁動人的軍歌。有的只是,三十年壓在心頭的滄桑歷史和生活重擔。
總算,山底上有位泰國朋友看出了這些人的可貴,對記者說:「幸好這些游擊隊是中國人,要不然以他們這樣的驍勇善戰,準鬧得天翻地覆。善戰而能不好戰,不長死而能安貧樂道。在全世界,怕再也找不到這種有紀律、又有教養的游擊隊了,作為一個中國人,這是值得驕傲的,因為他們在三十年生活重擔的壓迫下,付出了血與汗,卻沒有付出做人的奪嚴。
他們能在如此尷尬的處境中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除了嚴明的軍紀外,最重要的,是由於游擊隊具有重視教育的一貫傳統。即使在當初三餐不繼的叢林戰時代,隨軍學校也始終辦著不輟。就因為部隊長官有這麼深遼的眼光,才使在山區生長的第二代,仍然是有教養的一代。
如今,美斯樂村的中、小學加在一起有近千名學生。小學在泰國政府立案,由泰國教育部分派泰文老師來此任教,學生們只能利用課餘時間補習中文;中學則由游擊隊自行設立,算是全泰國最大的一間中文學校,許多希望子弟唸中文的家長,遠從曼谷和緬甸把子女送來此地寄讀。
學生缺乏中文書藉
記者訪問學校時,深深被那些樸素踏實的老師們所感動。他們為教育下一代所付出的心血,在這荒僻的山村裏,自然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對於簡陌的校舍和殘缺不全的教學設備,他們都有克難補救辦法。唯一無法解決的問題,是學童們嚴重缺乏課外讀物,除了「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致贈的課本外,無中文書籍可讀。
曾經是部隊指揮官的熊校長緊握著記者的雙手,希望記者能把這項國難轉達給臺灣的讀者,募捐些課外讀物,讓學生能有適當的精神食糧。這是記者訪問山村期間,他們提出的唯一要。求若非為著下一代請命,他們是不隨便訴苦的。
當然,記者所訪問的山村,只是泰國邊境上無數中國游擊村中的一個據點,在這數萬名生活在異域的中國人身上,還有說不完的故事等看被發掘。但是山底下來的人說,曼谷的部隊正發動軍事政變,記者只有匆匆下山,趕往曼谷採訪去了。(本文自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刊於中國時報原題異域滄桑三十年)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11期;民國70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