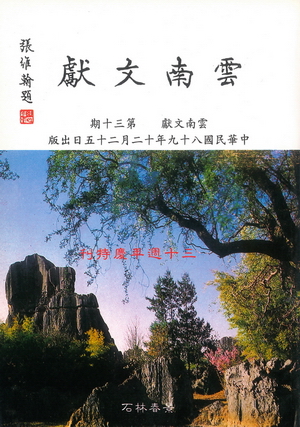泰北難民村近況
石炳銘
泰北約八十個華人難民村,經過卅多年來胼手胝足的掙扎奮鬥,加上近二十年來中華救助總會(原中國大陸災胞救助總會)的積極援助,原始的面貌已有重大改變,如果你曾經在十或廾年前到過難民村,今天再舊地重遊。你會明顯的覺察到今昔的不同。
第一件讓你印象深刻的改變,莫過於村村寨寨都湧現了不少亮麗的新民居。茅草屋逐漸消失了,代之而起的盡是較美觀而耐久的磚墻瓦頂房屋,這種現象的出現,當然是與難民生活的日趨改善有關,同樣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中華救助總會郭哲理事長的愛心關懷。他本著「安得廣廈千萬間,儘披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悲憫情懷,號召祖國各界共申援手,為各難民村廣建新屋。設定建屋目標為三千戶。這個計劃於民國八十六年開始推動,到八十九年上半年,已全部落實完成。
救總推動這個計劃之初,承辦人員莫不捏了一把冷汗,大家並不看好它會成功,因為泰北難民村的救助工作,已經持續進行了一、二十年,國內各方對該地區的關懷,已漸漸冷卻,加上政治氣候也起了很大改變,要別人慷慨捐輸,而且所需金額又相當龐大,所以大家認為難度很高,不過既然決定了要去推動執行,救總上上下下,大家都在挖空心思,思索出各種可行方案,希望能夠順利完成郭理事長的這個決定。
救總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透過各種活動,再度喚起國內各界同胞對泰北難民村的關懷。他們首先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邀請了一批立法委員及媒體記者到泰北考察訪問。兩年後又再度邀請一些立法委員,政府官員及媒體記者數十人,由郭理事長親自陪同再往泰北考察。在國內除透過傳播界廣泛報導外,救總也舉辮了一系列的酒會、座談會,企盼各界共襄盛舉,積極響應並贊助這個具體而又實惠的為貧苦難胞建屋計劃。立法院的一些立法委員,首先響應;他們聯合集中在清邁地區興建了戶住宅,該村居民為表感激之情,把原來的村民更名為「立委新村」。
捐款最多的應屬中國佛教協會理事長淨心大師,他共捐款新台幣八○○萬元,改建貧戶住宅一○○戶,據筆者所知,淨心長老,先後訪問泰北難民村九次,捐款彙計已逾新台幣五千萬元,可說是民間對泰北難民村出力最大的一人了。他的這份善行,具體實現了佛教人間化的新思維。有一位年逾八旬的獨居在安養院內老太太,也慷慨的捐了一百萬元,為美斯樂的榮民之家建了新屋。中國團結自強協會,也捐贈了一百萬元,集中改建了二十五戶住宅,村名也相應的改為自強新村,除了這些大額捐款外,都是金額不等的小額捐款,有一人獨捐一戶者,也有一人慨捐十戶者,因篇幅有限,難以一一列舉。總之,這個為泰北貧戶改建三千戶的計劃,在這種集羽成裘的方式下,已如期順利完成,這也說明了社會上仍充盈著對難胞的一片愛心,遺落在異域的成千上萬苦難中國人,仍有很多人在關懷他們;他們不曾因時間的漫長而被遺忘!
長久困擾著泰北難胞的最大問題,莫過於身份合法化問題,盡管他們定居斯土已先後達三、四十年之久,他們第二代,第三代都已相繼出生並長大,但絕大多數人口,依然是非法移民身份,因此行動及居住都受到嚴格的限制,換句話說,就是劃地為牢,難胞們只能局限在指定的範圍內活動,非經官方特別允准,不能擅離一步。一個失去居住及行動自由的人,自然沒有任何選擇工作的權利可言,唯一的工作,就只有務農一途。而難民村又都建在不適農耕的山區,在這樣的客觀環境下,任誰都會無計可施;要改善生活又從何談起?直到公元二千年的今天,這個綁牢難胞的死結,才得解開;那就是說,泰國政府已用概括包容方式,准許這些眾達數萬的難胞入籍泰國,有了合法的身份,就是除去了長久以來加在難胞身上的桎梏。以中國人的聽明才智及肯吃苦耐勞的習性,他們將會自我釋放出遭禁錮已久的活力,必可振翅而飛,迎向光明的未來。
為了爭取身份合法化,政府相關部門及救總都盡了努力;因為中泰雙方並無正式邦交,外交部雖有心,但卻使不上力,只有救總以民間的姿態出現,才能化解許多阻力,所以它一直扮演著改善中泰實質關係的角色,而身份合法化的問題,自然是力求突破的焦點。經過多年來的努力爭取,部份難胞已陸續取得合法身份証,但仍有甚多的難胞仍無法合法化,直到民國八十九年九月,泰國政府始正式宣佈將給眾達一萬八千多人的泰北中國難民合法身份証,所以困擾泰北難胞數十年的身份問題,可說是基本上得到解決了。
反觀國內,政府卻訂定了世界上最嚴苛的移民條例,很多回台升學或婚姻關係到台灣來求學及居住的泰北難胞,儘管已在這塊土地上打拼了十年八年,有些還生了孩子,但當局卻拒絕發給他們身份証,沒有身份証,就變成無國籍難民,雇主不敢雇用,即使被雇用,也遭到工資上的克扣剝削。警察抓到他們時,就動輒把他們送到位在山峽的外國人收容所。按規定要強迫遣返原居住國,但事實上,這些人都被各該國拒絕入境,實際上是遣返不了的。多年前時常見諸媒體的所謂「六大一小」共七個被禁錮在該收容所的六個大人及一個小孩就是這樣被當成外國人押送進去的;他們被關在裡面長達數年之久。後來經過台北的劉曉華小姐仗義奔走,努力援救。媒體工作者張龍潭先生在電視上呼籲,最後得到立法委員周荃、王天競等的出面援救,才獲得釋放,他們都已在台灣有了自己的家,都過著正常的生活,也都在為這個社會貢獻一己之力。從這「六大一小」的案例中,政府應該自我反省,深刻的檢討一下,有關限制泰緬等地華僑來台的各種苛刻規定,我們為什麼不能較高、較廣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呢?難道我們要永遠把中華民國局限在台灣這個小格局裡嗎?為什麼當今的政治人物,不能把眼光放大,放遠一點呢?最低限度,對於那些一貫忠貞擁護中華民國的海外同胞不應把他們拒之於千里以外吧!為政之道難道不是要激勵忠貞,必要時要國人為國家民族抛頭顱、灑熱血嗎?
很多在民國四十、五十及六十年代在滇緬邊區參加過國軍的戰士,因種種原因而未能隨部隊撤回台灣,這些失落在金三角地區的戰士,人數約在八千人左右,絕大多數都藏匿在深山野林或邊僻山區小村的原住民環境中,幾乎都過著極簡單僕素的半原始生活,與外界的信息處於隔絕狀態。國防部決定要給於他們發放戰士授田憑証補償金,但通知到達泰北難民村時,距登記截止日期只有短短四十天不到,就連很多居住在信息較靈通的泰國北部的人,都無法即時得到消息,那些遠在緬甸東北部的人,則更勿論了;等他們輾轉得知這個消息時,已是一年半載以後的事了。等他們趕來泰北地區登記時,早已逾越時限,但人數實在太多了,有關單位不能不加重視。為了謎這些戰士得以享受應有的權利,立法院還特別修法,將登記截止日期向後延長一年半。之前,救總曾兩次邀請立法委員及政府相關官員前往泰緬邊境了解實況。修法後得以補行登記的老戰士,超過七千人,但實際通過審查者不到一千五白人,尚有五千餘人,因缺乏有效証件或資料,都未獲通過。換句話說,這五千多人都還未得到仕何補償金。救總最近(即八十九年十月)第三次邀請立法委員王天競、洪秀柱等十人,再到泰北考察訪問,當然希望立委們能在立法院仗義直言,為那些老戰士及其他未了待了的難題,盡一些力量,在這些待解決的難題中,有一項是那些已在泰國持有合法居留証的難胞來台灣觀光、探親或打工而被擱阻的問題。
按照泰國法律,凡持有外僑永久居留証者,在泰國是完全自由的,他們可以自由遷居,自由工作,也可自由出入國境,不受任何限制。但偏偏中華民國就不准許他們入境台灣;凡持有居留証(又稱隨身証)護照者,在曼谷的台北辦事處一律拒絕簽証。這是十分不合理的荒謬規定,理由是擔心他們到台灣後就不再離開。這明顯是一極歧視和偏見,也直接違反聯合國有關國際難民及人權的規定,政府天天在叫喊要「走出去」,要邁向國際社會,連這樣最基本人權要求,我們都視而不見,沒有絲毫誠意去履行它,還有什麼顏面要提走向國際呢?
前面所提及的泰北老戰士受領戰士授田補償金一事,就已獲領補償金的人數而言,約有二千人左右,每人最低新台幣五萬元,最高五十萬元,總計已發放金額約新台幣二億五千萬元。這對貧困的老兵而言,可算是一筆可觀的財富,他們突然有了這筆現金,就如同在台灣的老兵一下子得到一百萬一樣的相同價值。說到這裡,幕後最具關鍵影響力者不是別人,而是現任台北市雲南同鄉會理事長簡漢生先生。記得大約是民國八十五年夏天,救總泰北難民村工作團團長龔承業先生,白清邁返台述職,他找我談起泰北還有很老戰士錯失了登記時限,以致無法領到補償金。他因長期駐在泰北工作,受到的壓力很大,雖然已一再向政府反映,但有關單位一律以逾期不受理答覆,毫無討論餘地。他覺得十分無奈,同時也感到十分困擾,他和我討論該怎麼辦?我認為這是必須找黨政高層人員溝通,或可找到一線希望,於是我們倆人就到位於林森南路的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簡漢生主任的辦公室求見,原來簡先生早已了解這個問題,他說這件事即使直接找上總統也沒輒;因為這是法律問題,法律問題必須透過法律解決,所謂解鈴還需繫鈴人,唯一可行的途逕,就只有修法。他並立即當我兩人之面,打電話給立委潘維剛及朱鳳芝,介紹龔團長和我去向他們報告,因為她兩位都是所謂的軍系立委,自然較易取得共識,我們兩人立即遵照簡主任的指示,趕往立法院找人。果然她們都深表關懷,允諾盡力而為。龔團長並向救總領導階層報告經過,救總也立即採取行動,邀請立法委員十人組成考察團到泰北實地考察了解。最後終於成就了立法院修法及補辦登記等一連串的實質效果。
從這個事例,再度予我一種深刻的啓示;那就是不論任何困難的事,涉事者的首要條件,必先「有心」,有一顆熾熱的心,然後才能奉獻心力,在不可能中去尋求突破。雖然不一定能成功,但肯嘗試,肯去盡力,機會總是會有的。如果像時下的大多數工作人員不論是在公家機關或民間機構,一般人都只能消極的去履行他的責任,一遇阻力或困難,就找種種理由推脫,這也就是所謂的官僚文化。
泰北難民村的難胞,雖然物質條件極為艱苦,但一開頭,他們都很重視子女的教育,幾乎村村寨寨都有自辦小學,幾個較大的村寨,如美斯樂、滿堂、滿星疊、熱水塘及大谷地等地,都設有初級中學。復華學校還增設了高中。這些學校的初中畢業生,最大的希望就是來台灣升學。早期(指民國八十年以前)政府一直採取鼓勵他們回國升學政策,救總、教育部都設有全額獎學金。在這樣的寬鬆政策下,幫助了數千名泰北學生在台灣完成了中等以上的教育。隨著台資大量投資於泰國,加上台灣大量引進泰籍勞工,所以這些在台灣完成學業的泰北學生,都成了工商界的搶手貨;他們或擔任翻譯,或成為幹部,表現都十分良好,對於中華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直接的貢獻。這對於那些短視而持反對僑生政策的政客(主要是民進黨)而言,無疑的已給了他們最有力的駁斥。
民國七十五年,泰國政府突然接管了泰北所有的中文學校,禁止教授中文,致使所有的難民子弟學校都頓陷於停頓狀態,但各地很快就採取了因應措施;以家庭補習方式,持續中文教育,這種情形自然影響正常的教育,學生的水準相對難以提高。這是泰北全體難胞共同痛苦,也是寄人離下的悲哀。隨著亞洲華人經濟圈的形成並日益壯大,一向對中文教育採敵視態度的東南亞各國,迫於現實的需要,他們被迫採取較開明的政策,泰北難民子弟學校,也因此得到了轉機,各村中文學校紛紛復校上課,形成一片欣欣向榮景象。值得一提的是僑務委員會及教育部也同步積極的動起來,這兩個部會在泰緬地區投注了遠較過去為多的關懷,大手筆投下經費,大量培訓師資,不僅就地輔導培訓,而且逐年將僑校師資接回台灣,集中屏東師範學院接受長期教育。教育部也一次輔助泰北建華中學新台幣近千萬元,用以興建校設。這些舉措是過去從未曾有過的。美斯樂的興華學校原是泰北最具規模的中文學校,自遭泰方接收後,一直陷於癱瘓狀態。村民雖一直想復校上課,但因美斯樂名氣大,是眾所觸目的焦點,而且迄仍處在軍管狀態,以致遲遲不能復校。該校早期畢業校友如郭泰生、鄒庚生及尚板雲等等有心人士的倡議下,劍及履及的策動了復校重建計劃。除了僑委會曾予補助新台幣二十五萬元外,他們迄今未曾得到任何奧援。但他們並不氣餒,迅速組成籌建委員會,向畢業校友勸募,舉辦了募款餐會,許多在台打工的校友都踴躍出席,當場獲得捐款近百萬元,其中很多都是一千兩千的小額捐款。因為這些校友大多數都是靠工資生活,都還只是二、三十歲的青年,不可能有雄厚的經濟力量。大家全憑一股熱忱,但願同鄉會的鄉長們也能伸出溫暖的手,給這些年輕的未來接班人一些鼓勵,讓他們更有信心去為公益事務奉獻、打拼,也更能凝集鄉親間的感情。
另外值得一提的聯華新村復華學校。那是一處位於湄公河附近的邊僻小村,僅有難胞約五、六十戶,是泰北最貧困的難民村之一,但村民們卻在那樣艱困的環境中,設立了泰北第一所含有高中部的學校,名稱就叫「復華學校」。現有中小學生約四百名,校長李銘亞,是泰北孤軍第二代青年,父親在作戰中陣亡,李校長憑著一股衝勁,亦手空拳的為學校發展而到處奔走,他在最困難的時候,首先得到台北錢秋華小姐慷慨贊助,致使學校能有喘息機會,為爾後的穩步向前奠下基礎。台北的天主教民愛會,也給了他很多支持,由於該會的牽成,復華學校得以和台北及台中的多所學校結成姐妹校,分別是光仁中學、聖心女中及台中的教會學校,這幾所學校每年都派遣教師義務前往輔導,不僅有效提高了復華學校教學水準,而且也資助經費,使該校得以持續成長,難得的是他們都在默默的奉獻,從不對外張揚,充分發揮了普愛精神,十分值得敬佩。
華文教育固然重要,但僑居海外的僑民,必須融入當地社會方是長久之計,因此救總在泰北設有三十名獎學金,獎助泰北華校學生升讀泰文學校。另外救總也正在策劃,準備在泰北地區開辦職業訓練班,輔導難胞子女習得一技之長,以便就地就業,減少返台升學或工作的壓力。
在農牧發展方面,清萊的永泰難民村現在已演變成了泰緬邊境養豬業的指導中心,多年前救總泰北工作團龔團長情商台灣養豬專家于如桐博士前往該村輔導難胞養豬,引進新的改良品種及飼養技術,原來要畜養廾個月以上方可出售的肉豬,現在只要半年不到就可以出售了。該村不僅在兩年內,全數還清了救總貸給他們的二○○萬週轉貸款,而且把養豬事業擴張到緬甸,目前(指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已可隨時供應成豬一萬五千頭。可說是整個中南半島最成功、最俱規模的養豬事業,除了救總工作團的輔導,于如桐博士的義務教導外,此項養豬事業的成功,得力於該村領導人艾小石夫婦的開明及大公無私,他倆人的領導風格是完全信賴專家,放手專家去執行,他們除提供必須的協助外,一切都不加干涉,徹底做到財務透明化及公開化,這是在各難民村中少見的現象,另外從台灣去的王繼雄牧師夫婦及黃鍠岳牧師,也是關鍵性人物,他們在該村傳教,得到艾小石夫妻的完全信任,該村的農牧業發展,就是交由他們去全權執行。艾小石夫婦本身雖然沒有受過任何正規教育,但他們能知人善任,因材器使,實在是非常難能可貴。
附記:民國八十五年、八十七年及八十九年救總三次邀請立法委員到泰北考察訪問,分別是潘維剛、王天競、李鳴臬、吳惠祖、靳曾珍麗、蕭金蘭、陳鴻基、謝東欽、陳一新、林郁芳、徐少萍、郭素春、鄭金玲、洪秀柱、劉光華、章仁香、張世良、陳清寶等計共十八人。他們考察返台後,都盡力替泰北難胞說話,也在立法院相繼推出有利於難胞的法案,這些努力和表現,都值得我們感謝和欣慰。但天下事沒有不自我努力而得人助者,必先自助而後人助,先自強,才能贏得別人的敬佩,所謂「得道多助」實在是不易的真理。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0期;民國89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