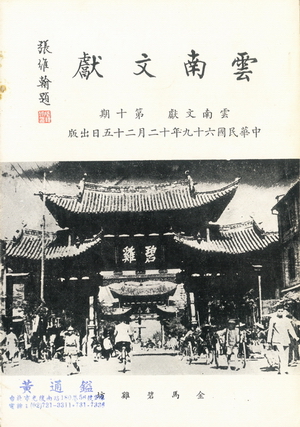為民主自由戰鬪的雲南人民
作者/林翠
永不熄滅的希望
大陸失陷後,雲南人民的反共戰鬪就始終沒有停息過。四十年的春天,在雲南的反共游擊隊,最低限度的估計也在五十支以上。毛共陳賡屬下的第四兵團,都感到難於應付。他們搖頭歎息,認為這是『渡江』以後所未遭遇過的『敵人』。他們常自誇以游擊『起家』,可是卻害怕這種游擊戰。譬如一支毛軍正行進在一片山崗和叢林地帶,槍聲突然響起來了。暴風雨似的槍彈由四週投射過來。成十成百的毛軍帶著慘嘷倒在血泊裏。等待毛軍『搶下高地』而佈置好準備迎戰的時候,一切又靜寂了。除了偶而一陣陣的山風呼嘯而過,『敵人』!敵人在何處呢?這樣的戰爭怎不教毛軍膽寒!在那些身著俄式軍裝已僵硬的死屍上,鮮血在一塊塊的小銅牌上閃著陰森的紅光,那是征服者,自誇的『勝利獎章』!『四平街戰役』、『錦州戰役』、『淮海戰役』以及『渡江紀念章』。──唯物論的統治者在此又否定了物質的力量,他們卻用一塊塊小銅牌的『精神價值』,來換取無數年青人的生命。這些自命是路過『大江大河』的『解放軍』,想不到卻在邊遠的雲南山區裏結束生命。毛澤東所謂『生的光榮,死的偉大。』(毛酋給予一個據說是為『人民英勇犧牲』女黨員劉胡蘭的『悼詞』)對他們正是一場五色的迷夢。如令冰泠的死亡抹去這揚迷夢。然而他們卻永不在人間清醒。
反共游擊隊迅速成長壯大底原因也並非屬於偶然。多年來,雲南人民是被認為具有淳樸、勤勞而勇敢的特性。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不過半月,雲南便飄起了革命旗幟。他們在民國史上也寫過輝煌的史蹟。推翻袁世凱的帝制是雲南人民放的第一槍;在民族抗日戰爭中上百萬的老百姓用他們的血汗,用最原始的工具,征服了山嵐瘴毒,從無人跡的蠻荒峻嶺中,奇蹟似的開闢出中緬和中印公路。用這兩條運輸線支持艱苦的戰爭。雲南的六十軍在臺見莊更用過十字鍬來對付『大日本皇軍』的坦克車。這為廿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歷史,寫下過悲壯的史詩。
沒有遼潤的海岸和巨港,也沒有密如蛛網的交通線。因此所謂西方的物質文明和那些五光十色的『新思想』也就無法大量泛濫在這片土地。那些層層的山脈和峻嶺,像一個頑固的老人緊守住自己的家園。因而這片土地依然大多像似古老的農業社會──這樣的社會也就更多的奪重若傳統──傳統並非完美,但卻具有著強烈的反共性,當它們與當代共產主義的狂潮接觸時,便格格不入的激起反抗。另一點原因是:生長山區的人民在對抗自然和野獸的鬪爭中,必然培養出強悍的一面,這就是蔣百里所說的『生活與戰鬪一致』的特點。因而只要有幾位領導者登高一呼,再加上現實環境迫害的刺激,他們會掮起自己的槍,牽著家裏的馬,加入戰鬪。即令不經過嚴格訓練,他們已經是天生的游擊戰士了。
然而這些壯大了的反共游擊隊又逐漸像天邊的小星隱沒了。這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毛軍十倍百倍的優勢兵力是一個主因;而游擊隊除了向敵人身上取得有限的械彈補給外,便全無後援了。而一些游擊隊領導者的剛愎自用,以及那種狹隘個人英雄主義的性格,使得相互不能團結禦敵,而致被毛軍個別擊破。再說缺少一個堅強,基地的游擊戰爭,也是個致命的弱點。當然,他們大多,數都是在壯烈的戰鬪中消失。
少數明智的游擊領導者已從慘烈的教訓中得到啟示,他們開始凝視著「滇西」──那一條綿延千里的中緬未定界,這正是他們所該選擇的戰線。這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最好戰場,他們含淚的告別自己的家園,突破重重的包圍線,從一個戰役到另一個戰役,終於轉戰千里的到達這片土地,他們幾乎都是失去一切的人,緊抱著那支冰涼的槍和深懷著一個永不熄減的希望。
看那大江東去不回頭
在這片土地上他們開始創另造一個『家』,剛戰勝自然卻又立即要展開戰鬪。毛軍的幫兇──緬軍,在空軍的掩護下向他們猛烈攻擊。每枝槍不超過十發彈藥,迫擊砲僅只餘下兩發砲彈,但是炎黃的子孫從不會在戰爭跟前畏縮的。金光閃閃的樂隊作為前導,戴若大呢帽,穿看整齊的緬軍,列隊邁步而來。面對著這種景相,游擊戰士都在肚裏發笑。他們級瞇著眼瞄若準星。一千碼、五百碼、三百碼、兩百碼,指揮官的槍聲響了,所有的槍也跟著響了。第一波攻擊的緬軍倒下三分之二,餘下的回頭就跑,衝鋒號響了,游擊戰士帶若震天的『殺』聲向緬軍衝去。緬軍的後衛也扭身就跑,戰爭就如此結束了。游擊隊獲得了十幾卡車的彈藥裝備,──這是他們視為如生命般寶貴的東西。緬軍遠遠地走開了。游擊隊獲得了暫時的安定。
有了根據地之後,跟隨而來的是茁壯和發展。在根據地上建立起一個『反共大學』──作為培養軍政幹部的搖籃。內中區分為軍官隊、機砲隊、政幹隊、財務隊、通訊隊和軍士隊等等。游擊區也擴大到數干里之遙,游擊部隊更不斷化整為零的向大陸突擊。每次都能夠帶出很多自願參加反共的雲南青年。聲勢之大,連國際人士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然而,部分卓越的人,卻也看出了遠方的陰影,因為處於四面敵人的包圍中,這實在是危機重重,所以他們腦海裏會構想出一個,「輝煌」的藍圖。在緬南的喀欽是一支很優秀的民族,雖然在數量上他們少於執政的緬族,但從激育水準和品質來看,他們是優越的。這支民族為了反抗緬族的壓迫,在緬南莫爾棉附近建立起一個自己獨立的政府,但因缺少外援,所以,他們的力量是單薄的。他們曾不止一次的派遺代表,與游擊領袖會談,希望能侈得到武裝的協助。但是這請求始終未曾得到游擊領袖們一致同意,因而這個計劃可以說是『胎死腹中』。今天當筆者追溯這一已成為歷史的往事時,也不覺感慨良深:實際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勝利』,為了游擊隊的生存發展和勝利。這『理想』是應當值得一試,甚而是值得全力以赴。最基本的問題是:游擊隊不壯大發展,便可能趨於減亡,處於四面敵人虎視眈眈的情勢下,苟安的路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選擇一條有前途的戰鬪道路。再說:緬甸的政治形態在當時已顯而易見,要想他們自動改變為堅強反共盟國是不可能。要想與緬政府取得諒解和團結,也是不可能的。那末扶助克欽族來取得政權,而使緬甸成為一個奪重自由的國家,這途程雖是艱辛的,但卻是值得走,也是很應該走的路。當然在「方法」上必須要特別『講求』。這一點是個成敗的重要因素。我們很客觀的作一估計,以當時游擊區的人力物力來論,實在足以完成此一壯業。然而時機是永不待人的,真像是『看流水然悠,看那大江東去不回頭』。這樣的時機永不再來了。
事實證明了:第三條路是走不通的。四十二年,緬政有在毛共嚴重的壓力下,一面向聯合國拉告我游擊隊侵佔其領土,另一面又與毛軍及緬共武力組成三路聯軍向我游擊基地展開全面猛攻。雖然在軍事上游擊隊仍可與敵週旋,但其他情勢已經造成了『必須撤臺』的局面。這一年底至次年春天,將近萬人的游擊隊及其家屬撤退回臺。
筆者那時雖是『弱冠』之齡,但當飛機在泰國南邦機場起飛時,在薄霧繚繞的上室俯視那一片綿延的山脈,心底的感慨是複雜而深遠,對於個人生命的發皇來言,那片土地也許並不是最適宜的環境,但從整個反共鬪爭的大局面說:今後要費多少倍的人力物力來重建這個大基地。再說若沒有一個自由的緬甸,自由的東南亞也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事實證明了這些。
四十九年,又一批反共游擊隊撤退回臺。於是,在臺灣的報刊對西南邊區游擊隊的報導幾乎是沒有了。世人也似乎逐漸遺志他們。實際上,他們依舊在戰鬪著,甚而是沒有停止過一分鐘戰鬪。
不知道的明天
目前在那片土地上的重要指揮官有四位,此即段希×、李文×、張啟×、馬靖×,他們領導下的健兒×百由人至×千人。而近些年來他們大都未會接受過政府一槍一彈的援助,是完全自力更生的挺立著。他們已由原來的舊基地轉移到更適宜戰鬪的地區了。(他們都是不願遠離鄉土的人。)在這裏卻又開拓了另一個新的天地。一個方圓數十里的平原,在開墾的阡陌間時來著一幢幢的茅屋和竹樓,黃昏時的炊煙嬝嬝,其中再點級著一些不知名的野花,清澈的溪水潺潺流若。這真像是秀麗昆明的郊野。
雖然有點『春風吹得遊人醉』的情景,可是卻無『且把杭州當汴州』的心情。而情勢也不容許他們苟安下去。每天都有幾十匹的騾馬把補給運送到各個戰鬪基地去。在這裏真正成為了『軍民一家』的小社會,能夠拿槍的人都掮上槍了;其餘的勞動力都投入生產戰線。
這裏有一所幹部訓練學校,區分為軍官隊、軍士隊等。受訓期間為六個月,軍事課程以各種兵器的使用及小部隊戰術,及游擊戰術為主,遣憾的是缺乏較新的教材和資料。一切的設備幾乎都是學員們雙手造成,大碗粗的竹子就是他們的一切建築材料。學員們都是由名個基地輸流調訓,這種訓練可使得游擊部隊永遠保持著戰鬪的朝氣,他們都表現了高度認真的學習精神。
這個基地於不久前又開辦了一所由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二年級的學校。學校的師齊大部份是被緬甸政府迫害而逃亡至此的教師,學生則分為三部份,一屢游擊隊的子女•;二是緬甸的流亡僑生;三是由大陸逃來之義民子女。教材和教木都是使用我們政府所編定者,學校內對環境清寒者會設有獎學金,當然設備的簡陋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這些身逢亂世的男孩和女孩,都有著很高的學習精神。也許由於『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遭遇,師生間的感情也特別深厚。但這些孩子們都表現得較為沉默,──這是時代的悲劇。孩子們原本是最清白的,可是在他們稚弱的心靈上卻已經佈滿了各式各樣的創傷,他們把來自自由祖國──臺灣的報刊都當做珍寶看待。這裏生活的可說是遠離了所謂廿世紀的物質文明。因為連起碼的電燈也沒有。但是依靠若熒熒的油燈和明月照讀的孩子們的一般成績比之在日光燈下的臺灣學童不會更差。
這個基地給予外客的印象,是規律而嚴肅。人們每天清晨與太陽比賽先起床,於是各人走向自己的崗位。人們是在沉靜中奔忙五天一次的『趕街』給這『壩子』帶來了鬧烘烘的氣象,小街兩旁的竹棚輿擺滿了日用百貨、菜蔬、豬肉和一些野味,鮮魚在此是罕有的貴物。穿戴著花花綠綠的山地民族也來到了。你可以聽到緬語、傣語、倮黑語、漢語嘰嘰喳喳的像似一闋奇異的樂曲。緬幣、傣幣、龍圓都可以在此通用,年輕小伙子們不是捐著槍,便是掛若力的,年輕的婦女也總是打扮得花哩胡哨的樣子。他們一串串的笑聲就像是一個個的五色氣球飄滿了小街。偶然也能侈嚐到一點真正家鄉味的「米線」和「餌訣」。(以上二者皆是用米做成)即使是不買東西的人,也願意多在這小街上徘徊留戀一陣。對於這片土地上的人來說。這『趕街』是他們所珍惜的。這不僅是一種經濟需要,而也有更多的精神價值,這裏沒有任何劇院影場和娛樂場所,因而這『趕街』就成為了人們的娛樂。每五天一次,人們打扮好從四面八方匯集這裏,各式各種的衣飾和面孔,把這條街組成一副多采多姿的五彩雲。──其實說是五彩電影才更適合,大家都是主角,卻又都是觀眾。逛累了,在竹棚裏喝杯涼茶,或是喝兩杯酒,便有些飄飄然了。老張老李大家碰頭了,海闊天室的胡扯一陣。心中抑悶時,發幾旬牢騷,罵幾聲『忘八蛋』,氣就消了一半,聽到的人也只會歎口氣說:『大約又是想老家想得發「神經」了!』『趕完街子』,搖搖擺擺的走同去,哼兩句栗成之底老「滇腔」,『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生得好容貌……。』想想自己受苦受難時聲音便有點嘶啞了。再一想陣口吐沬對自己說:『老子總算是自由自在的,這一點就比在共產黨統治下強十倍了。』於是自己又格格笑起來。
每個黃昏,這片土地卻又有另一份風情,田裏的人收工了,戰士也收操了。揹槍的漢子攜著孩子在漁步,小孫女依在老爹爹的懷裏看五彩雲──在雲南高原的傍晚多是有著艷麗的彩雲,小孫女的手指在點若天室,啊!那像是獅子狗,那像小老虎,那像大象,那多像是一條梅花鹿。……小手指都點酸了。天幕上一顆顆的星星亮起來了,照著爹爹的白鬍子,也照著那雙憂鬱的老眼……。
至於明天,誰也不敢肯定明天是怎樣的一天,也許那又是一個流血戰鬪的日子。
勇敢的愛與死
游擊部隊,大多駐紮在靠近前線的卡瓦山區,這一座綿亙險峻的卡瓦山多年來原木屬於「漢人」的禁地。這山區據說一共分轄於十八個卡瓦「王子」管理。卡瓦是一種很驃悍的原始野蠻民族,他們又分為「家卡」和「野卡」。前者因為受了漢族文化的同化,所以性情較為柔順,風俗習慣也逐漸模仿漢族。而後者可說是未開化的民族,野性難馴,喜食腐臭之肉甚而也有吃人肉者。他們亦喜獵人頭,以祭神祝豐收。游擊部隊初進入這片山區時,頗費週折,甚至連炊事挑水時,也需要荷槍實彈給予保護,後來又經過了幾次慘烈的戰鬪,情況才逐漸變好。
今日游擊部隊對於「家卡」可說已經完成安撫,對於「野卡」則一直是恩威並用,與他們的「王子」儘量講求團結。所以逐漸也可以和平相處。但是對於這種蠻族的教化也不是短期可以完成,所以問題仍然存在。
卡瓦山區確是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最佳游擊基地。險峻的地方真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但是在對抗自然和疾病方面,確要付出較多代價。這裏在五百種以上的瘧蚊。游擊戰士往往必須定期服食奎寧,所以他們的臉色,往往常帶點蒼白。
突擊大陸對於游擊戰士來說是一任興奮而又嚴肅的事,他們幾乎任何時機都可以進入大陸。但這征途也是艱巨的。他們的裝備是一條小薄毯,一套內衣褲,其他便全是糧彈。一個自己用竹子做的水壺便是他們身上的惟一裝飾品,從這水壺上是可以看出一點其人的個性。有的在上面雕刻反共的詩句;有的是龍啊,鳳的;風流才子型的卻把自己情人的名姓和倩影刻在上面。還有一塊膠布是最不可少,宿營是可作『床單』,雨季時的雨衣,夜行軍時的披風。
由於生活的鍛鍊,他們都是第一流翻山越嶺能手,在這點上他們遠超過毛軍,又因為他們大多從小就是獵手,所以打毛軍比打兔子和飛鳥更容易。所以即使碰到三五倍的毛軍時,他們有把握『幹掉他幾十個』『發點財』(指毛軍的槍彈與裝備)然後『走之大吉』。
但是,有時候,在不利的地形下,遭遇了十倍以上的毛軍包圍時,這戰鬪就會很慘烈了。一般觀念裏以為衝鋒槍、卡賓槍輕巧,最適宜山林游擊戰。殊不知有利者往往也有害,而此兩種武器的最大弱點是射程不遠,所以最初與毛軍接觸時,這兩種槍聲一響,毛軍『軍官』就會高叫喊:『卡賓槍打不遠,不要怕,前進!』很快的游擊隊就變得更聰明了,他們首先用卡賓槍聲引誘毛軍的『人海戰術』到相當距離時,幾挺『半重式』機槍(即美造A六式機槍)再來『埋葬』毛軍。『半重式』是游擊隊戰士最珍愛的武器。它只需一個壯漢便可撈帶,比之毛軍的馬克沁和俄式重機槍都輕便得多。他們很有自信的認為:如果平均每五人便配有一支『半重式』,他們對大陸突擊,不論遭到任何敵人,必能凱旋歸來。
然而,只要是戰爭也都有著悲慘的一面。海明威在「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alls)一書的末尾描寫擔任游擊隊負傷的男主角緊握一枝機槍來掩護撤退而犧牲。這悲壯的結局會贏得無數人的熱淚。但像如此的事實在雲南反共游擊隊中是太多了。他們其中很多是負了重傷,而又不願速累伙伴,因此,請求留下一個手榴彈和一枝槍(自然不是寶貴的機槍)於是他會扣緊板機,面對攻擊的毛軍喃喃自語:『一個是本錢,兩個是利錢,三個便是利上加利,四個是……。』『轟』一聲手榴彈爆炸了。在遠處的聽到的戰友們眼角裏含有瑩瑩的淚珠。他們會低低的說:『這一回,他真正回「老家」了!』
這是莊嚴的死,但依然是人間悲劇。每一個生命從出生那天就一直為了求生存而戰鬪,每一個人也都寶愛他自己的生命。然而,他們何以會慷慨的視死如歸呢?問題應該歸於毛共的暴政。
毫無疑問,在中國大陸內的反共情緒是普遍的,游擊隊在突擊大陸所帶來的主要困擾就是無法對隨隊逃出難民韋的處理。譬如幾年前會作過一次大規模的突擊,並把鎮越佔領了兩三天。結果老百姓扶老攜幼的跟隨游擊隊撤退的就近萬人,游擊隊為掩護他們的安全,弄得精疲力竭。想想看,一萬人每天要吃多少糧食……。
向歷史底奉獻
那些苦戰多年的游擊戰士們,他們並非鋼鐵造成,而仍然是血肉之軀,他們同樣也有著痛苦和眼淚,他們愛好和平遠勝過戰爭。然而他們卻不會停止的在那片土她上戰鬪了十六年,他們忍受了一切非常人所忍受的磨難。在漫長的歲月裏,他們之中有的壯年而已長滿白髮;由孩子變為青年;由青年進入老邁。嗚咽而奔流的薩爾溫江,流不盡他們心底的哀悲和憤恨……無論他們的結局如何,他們都已經向歷史奉獻了保衛自由和民主底珍貴啟示。
(本文曾載「政治評論」第十四卷、第九期。「中國地方自治」十九卷、九期)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10期;民國69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