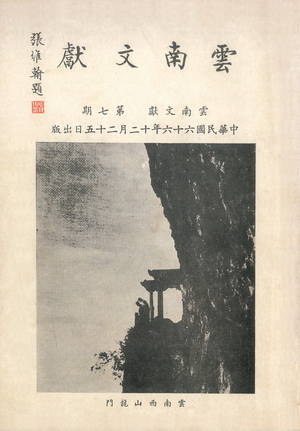南詔非泰族所建
作者/李拂一
此次到暹羅,恰好大泰主義,高唱入雲,盛傳暹羅政府,即將改國號為「泰」,雖尚未見正式公告,而曼谷市招,已可見到「Thailand」字樣,勢在必改,當無疑問。據傳改國號為「泰」的目的有二:㈠使東亞泰族,都可投到暹羅的懷抱;㈡收復過去泰族曾經統治過的地區,而建立一大泰帝國。一個國家裏面,是否僅可容納一個單純的民族(現在的暹羅國內,也就有不少的非泰族分佈在東西南北若干地區?)同一個民族,是否即不應該生存在不同種族的若干國家?這一點,我想暹羅政府,應該認識清楚。至過去泰族曾經統治過的地區,所指何在?而建立大泰帝國,談何容易!據若干暹羅文書刊說:「泰族係發源於科布多,經張掖至隴西,至此分兩支:一東向發展至長安;一南向發展至成都。至此復分為兩支:一支走涪州、貴州、鬱林、蒼梧、零陵、長沙,並由蒼梧、鬱林發展至海南島;一支南下而建立南詔帝國,都于大理。自後得長足的發展,東至昆明、馬龍;西至緬甸的瓦城、普羅姆,印度的吉大港、高哈提;南至今之暹羅,越南的一部份,更南至馬來半島之宋卡」(見泰族分佈圖)。換句話說:就是暹羅改國號為「泰」之後,將要收復北至科布多,西至東印度,東至長沙、瓊州這一大片土地。而其最得意之作則謂泰族曾在中國西南建立過南詔大帝國。暹羅古代史考(暹文本)曰;「細農(舍龍)王朝,共傳五代君主,至佛曆一二七三年(西元七三○年),坤瑪隆王(皮邏閣)者,為一英勇善戰之君主,使南詔疆域,大為廣濶。王嘗遠征中國及西藏,勝利多次,使中國不得不與之和議,而妻以公主焉。至佛曆一二七四年(唐開元十九年,西元七三一年),王更擴展南詔疆域至十二版納、十二詔泰、東京。又建立天國(HO)。由王子坤猜蓬統轄此泰南三邦」云云。
南詔蒙氏自細奴邏於唐高宗永徽四年(西元六五三年),遣使朝唐起,至今已一二八五年。自其第十三世主舜化貞於唐昭宗元復二年(西元九○二年)卒,國被篡,至今已一○三六年。吾人今日要確切考定南詔蒙氏是不是屬於暹羅的泰族,最好的辦法,莫如找來南詔王室及當時泰族人的屍骨,如莊周所說:使司命復生其形,為其骨肉肌膚,以作生物性的觀察及量度,看看他們的身材、頭型、面型、鼻型、血羣以及身體的一般狀態,如顏面、耳、目、口、鼻的形狀和輪廓,毛髮的特性、皮膚、眼睛的色澤等等,是不是相同?可惜現代的科學,無能達到生死肉骨的要求。最好的辦法既不可能,那只有退而求其次,由歷史上的記載及現存滇境以及可能與南詔王族有關的近似族類的文化特質,來比較推敲,加以研究了。
我國最古一部對於雲南六詔始末,稱族名類,風俗制度,山川城鎮,交通途程,土宜物產及其毘鄰諸國概略情形,作有系統的紀錄的書,應推唐安南從事樊綽於咸通四年春正月,在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節度押衙張守忠進獻之蠻志一十卷。此書異名有蠻書、雲南誌、雲南記、雲南史記、南蠻記及南夷志之不同。四庫館臣依新唐書藝文志,題曰蠻書。這一部書,可以說是雲南古代民族和地理的一部重要典籍。我們由這一部書表面,可以考知唐代六詔和其他民族的概略,尤其南詔的風土人情,制度條教及語言片斷。再參照其他有關書籍的紀錄,來和現在的泰族及可能與南詔有關的近似種類,作一比對的研究,則南詔是不是由泰族所建,便可得到一個概略的結論了。
蠻書六詔第三:「蒙舍,一詔也。居蒙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姓蒙。貞元年中,獻書於劍南節度使韋臯,自言本永昌沙壺之源也。」舊唐書謂其「自言哀牢之後」。新唐書謂:「本哀牢夷後」。探討南詔族屬者,大都先探討哀牢的族類。後漢書哀牢夷傳曰:「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主。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注引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雖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主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由柳貌至禁高共七代,由禁高再上推至九隆,應不少於三代,否則應可記知。即以三代計,已共有十代。每代平均以三十年計算,十代已三百年,當在周秦之際。元張道宗記古滇說云:「哀牢國,永昌郡也。其先有郡人蒙迦獨妻摩梨羌,名沙壹,居於哀牢山。蒙迦獨常捕魚為業,後死哀牢山水中,不獲其屍,妻沙壹往哭於此,忽見一木浮觸而來,旁邊漂沈,雖水面少許,婦坐其上,平穩不動,明日視之,見木觸沈如舊,尋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懷妊,十月孕生九子,後產一子,共男十人,同母一日行往池邊,詢問其父,母指曰:『死此池中矣』。語未畢,見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與子忽聞龍語曰:『汝為我生子,今俱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一小子不能去,母因留止。子背龍而坐,因舐之,就喚其名曰習農樂。母因見子背龍而坐,乃夷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其地曰九隆。習農樂後長成,有神異,每有天樂奏於其家,鳳凰棲於其樹,有五色花開,四時常有神衛護相隨。諸兄見有此奇異,又能為父所舐而與名,遂共推以為王,主哀牢」。又曰:「唐有張仁果三十三代孫張樂進求,改建寧為雲南。唐冊樂進求為首領大將軍雲南王。樂進求因祭鐵柱,見習農樂有金鑄鳳鳳飛上左肩,樂進求等驚異之,遂遜位其哀牢山王孫,王以蒙號國,王曰奇嘉。社稷之剙於斯,改稱蒙社,乃售高宗永徽四年……也」。元李京雲南志略曰:「初蠻酋張氏名仁果,時當漢末,居蒙舍川,為在諸部之南,故曰南詔。詔,漢語國君也。傳三十三主,至樂進求,乃為蒙氏所滅。蒙氏名細奴邏」。據記古滇說,後漢書之九隆,即繼張樂進求為雲南王的哀牢王習農樂。此習農樂亦即蠻書及雲南志略的細奴邏。一在周秦之際,一在唐初,相隔千年。且禁高、吸、建非、哀牢、桑藕、柳承、柳貌、扈栗、類牢等名,與南詔以名相屬之制不類。同時也和擺夷族的酋長土司以及平民,喜以金銀珠玉、琉璃寶石、幸福吉祥,官稱佛號等為名的習俗懸殊,不似泰族。其先世雖居哀牢,但亦非哀牢夷也。
南詔傳世風俗中,最特殊的一點,是父子以名相屬,子名的首一字,大致為父名的末一字,即父子連名制。南詔蒙氏立國第一世祖細奴邏,邏傳子邏盛,盛傳子盛邏皮,皮傳子皮邏閣,閣傳子閣羅鳳,鳳傳子鳳伽異,異傳子異牟尋,尋傳子尋閣勸,勸傳子勸龍晟,晟傳弟勸利,利傳弟豐佑,豐佑傳子世隆,隆傳子隆舜,舜傳子舜化貞而亡。凡十四主。除豐佑因慕中國之風,獨不肯連父名而外,餘均為父子連名。其他諸詔亦同。如邆賧詔立國主豐咩,咩傳子咩羅皮,皮傳子皮羅邆,邆傳子邆羅顛,顛傳子顛之託。浪穹詔立國主豐時,時傳子時羅鐸,鐸傳子鐸羅望,望傳子望偏,偏傳子偏羅矣,矣傳子矣羅君。蒙雋詔立國主雋輔首,無子,傳弟怯陽照,照傳子照原,原傳子原羅。施浪詔立國主施望欠,欠弟施望千,千子千傍,千傍子傍羅顛等是。南詔傳世諸王名中之一字,常有羅字或邏字,疑羅字或邏字,乃諸詔共用之姓,亦即其族名。南詔地望蒙舍,以蒙為氏。蒙乃氏而非姓也。此種見於烏蠻的父子連名制,亦見於白蠻所建的後理國,如第六世段智祥,祥傳子祥興,興傳子興智是。白蠻命名,往往在姓與名的中間,夾入一個佛號,如李觀音得之類。又緬甸蒲甘主驃苴低,低子低蒙直,也是父子連名的。近今屬於羅羅緬甸系的羅羅、麼些、阿卡、攸羅、窩泥等部族,現仍保存此種父子連名制未變。至於泰撣系裏面,則尚未發現有父子連名的事例。除國內擺夷上司冠用漢姓而外,一般平民,只有名而無姓。近今暹羅及老撾,由政府通令人民各自選擇兩個以上的語詞,報請政府核定其一,置於名後,以為姓氏,乃是受了西方文化以後的產物,原來也是沒有姓的。在滇境未受漢文化影響的擺夷。即所謂「原始泰」及在緬境的撣族,都只有名而無姓。由這一點來觀察,南詔和泰族是有所不同的。在「原始泰」的原文文獻裏,他們稱南詔為「和」族,自稱為「歹」,亦即泰族,並不自認與南詔為同族。
語言也是探討民族類別的一種線索。蠻書蠻夷風俗第八:「言語音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與漢不同,及四聲訛重。大事多不與面言,必使人往來達其詞意,以此取定,謂之行諾。大蟲謂之波羅密(亦名草羅),犀謂之矣(讀如咸),帶謂之佉苴(雲南備徵志本此處作佉苴,茲參本卷首節曹長以下『得繫金佉苴』,次節『謂腰帶曰佉苴』及管內物產第七:『未得繫金佉苴者,悉用犀革為佉苴,智朱漆之』,及新唐書:「佉苴韋帶也。」等改。)飯謂之喻,鹽謂之賓,鹿謂之識,牛謂之舍,川謂之赕,谷謂之浪,山謂之和,山頂謂之葱路,舞謂之伽傍。加,富也。閣,高也。諾,深也。苴,俊也。東爨謂城為弄,謂竹為翦,謂鹽為眗,謂地為渘,謂請為數,謂酸為制。言語並與白蠻不同」。所舉南詔二十二語中,經指明為東爨烏蠻語的有六個。未經指明,而言外之意為白蠻語的十六個。六個東爨烏蠻語中,有五語和現在的羅羅語相似。只有地為「渘」一語不符。十六個白蠻語中,犀謂之矣,原注「矣」讀如咸。如果將注語讀如咸三字刪除,矣讀本音,則與擺夷語之Riet(犀)相近。舞謂之伽傍,亦似擺夷語。山頂謂之葱路,似苗語。鹿謂之識,似倮黑語。川謂之賧,似藏語。鹽謂之賓,閣、高也等,為現在的民家語。又晉書卷一百十四載記十四苻堅傳下末尾,初堅疆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詔」又為晉時的氏族語。「氐」與擺夷族自稱為歹之「歹」字,乃一音之轉,如粵語之讀「地」為「代」六瞼之「瞼」,新唐書作「瞼」,駱賓王文集作儉,即中甸、右甸、巨甸、南甸、施甸、魯甸、小甸、大松甸之「甸」,為羅羅語。南詔計田曰雙,為唐之五畝。計帛曰冪,為唐之四尺五寸。律學新說謂:唐之大尺,即營造尺。暹羅計田曰萊,舊時之一萊,約合唐之一○○平方丈,合一‧六畝強。一雙等於暹羅的三萊。暹羅改遵法制後之一萊,為一六○○平方公尺,約合唐之二‧六○四一六畝強,一雙等於暹羅改遵法制後之一‧九二萊。南詔一冪之長,約等於營造尺制的一弓的九折,即四尺五寸,滇南漢語稱為「小拿」者。稱十足一弓之長為一拿,或一大拿。擺夷及暹羅計帛曰瓦,舊時一瓦之長,大體以我國一弓之長即五營造尺為依據,自西方勢力侵入中南半島、法併安南、英滅緬甸之後,滇省擺夷一瓦之長,改為六英尺。等於一‧八二七六公尺,合五‧四八二八市尺。暹羅一瓦之長,改為二公尺,合六市尺。冪與雙不是擺夷語,也不是暹羅語。此外,見於新唐書南詔傳的: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也。官曰坦綽、曰布爕,曰久贊,謂之清平官,猶唐宰相也。慕爽主兵,爽猶省也。金波羅,虎皮也。王母曰信麼,亦曰九麼。妃曰進武等官名,凡五六十語,也都不似擺夷語或暹羅語。而最大的差異,是文法上的不同。按照擺夷文或暹語文的文法,凡是由一個專有名字或名詞與一個普通名字或名詞組合為一個複合的專有名詞時,應將普通名字或名詞置於專有名字或名詞的前面。如「南詔」,應作「詔南」,「雲南瞼」、「蒙舍瞼」,應作「瞼雲南」、「瞼蒙舍」。凡是由一個形容字或詞與一個普通名字或名詞組合為一個複合的專有名詞或普通名詞時,應將形容字或詞,置於普通名字或詞的後面。如「南詔」(南字作形容詞解時),應作「詔南」。「白崖瞼」,應作「瞼崖白」之類。惜吾人所能獲知的南詔語無多,單辭隻字,不能作進一步的比較研究。同時南詔的語言,很為混雜,已略舉如上。但暹羅語成份所占的比例則絕少。蠻書說:言語音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所謂正者,似即指混有很多漢語,漢人聽來,有幾分了解而言也。又關於「行諾」之俗,今於羅羅緬甸語系的阿卡族中,仍有殘餘的痕跡可尋。阿卡遇有人詢問其名之時,尚須另倩一人代他轉答之類。就語言及其文法上的差異以及行諾的習俗觀察研究下來,南詔應屬於羅羅系部族,不是泰族。
南詔的條教,也甚為重要。據蠻書南蠻條教第九:南詔置有「清平官六人,每日(雲南備徵志『日』作『口』參『大軍將一十二人,與清平官同列,每日見南詔議事』節及新唐書『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日議事王所』句改。)與南詔參議境內大事。其中推量一人為內算官,凡有文書,便代南詔判押處置,有副兩員同勾當。又外算官兩人,或清平官或大軍將兼領之。六曹公事文書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與本曹出文牒行下,亦無商量裁製。又有同倫判官兩人,南詔有所處分,輒疏記之,轉付六曹」。又置「大軍將一十二人,與清平官同列。每日見南詔議事。出則領要害城鎮,稱節度。有事跡功勞殊尤者,得除授清平官」。「其六曹長即為主外司公務。六曹長六人、兵曹、戶曹、客曹、刑曹、工曹、倉曹,一如內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又有斷事曹長,推鞠盜賊;軍謀曹長,主陰陽占候,同倫長兩人,各有副都,主月終唱諸曹稽逋,如錄事之職。曹官文牒下諸城鎮,智呼主者。六曹長有功效明著,得遷補大軍將」。又置羽儀若干員,「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諸蠻不與焉。常在雲南王左右,羽儀長帳前管係之。羽儀長八人,如方內節度支衙官之屬。清平官已下,每入見南詔,皆不得佩劍,唯羽儀長得佩劍。出入臥外,雖不主公事,最為心腹親信」。「羅苴子皆於鄉兵中試入,故稱四軍苴子。戴光兜鍪,負犀皮銅股排,跣足歷險如飛。每百人羅苴佐一人管之。負排又從羅苴中揀入,無員數。南詔及諸鎮大軍將起坐不相離捍蔽者,皆負排也」。「戰鬪不分文武。無雜色役。每有徵發,但下文書與村邑理人處,尅往來月日而已。其兵仗人各自齎,更無官給。(武器有鐸鞘、鬱力、浪劍、縝弓、槍箭多用斑竹。)百家已上有總佐一,千人已上有理人官一,人約萬家以來,即制都督,遞相管轄。上官授與(新唐書作『授田』)四十雙,漢二頃也。上戶三十雙,漢一頃五十畝。中戶下戶各有差降。每家有丁壯,皆定為馬軍(新唐書作『壯者皆為戰卒,有馬為騎軍』),各據邑居遠近,分為四軍。以旗旙色別其東南西北,每面置一將,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如有賊盜入界,即罪在所入處面將」。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詔傳曰;「官曰坦綽,曰布爕,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曰爽酋,曰彌勤,曰勤齊,掌賦稅。曰兵獳司,掌機密。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撝,副曰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大抵如此」。又曰:「以清平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為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日議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算官代王裁處,外算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瞼、夷語瞼若州,曰雲南瞼、白崖瞼亦曰勃弄瞼、品澹瞼、邆川瞼、蒙舍瞼、大釐瞼曰史瞼、苴咩瞼亦曰陽瞼、蒙秦瞼、矣和瞼、趙川瞼」。云云。近今在國內的泰撣語系部族,以廣西的撞人為數最多,其次為貴州的仲家、洞家及水家,均巳漢化。聚居於雲南東南部的儂人及西部的漢擺夷,漢化的程度亦不淺。如南甸宣撫使司,宣撫使之下,置護印、護理、總理、司爺等人員。再其下有千夫長、百夫長、門房、書房、庫房、差房、軍裝房、堂房、內幕、外幕及團練局等人員。地方制度分為兩級,即撮、畈與村寨。撮設鄉約,畈設頭人。撮、畈之下有村寨,外有撫夷。干崖宣撫使司宣撫使之下,設有參議處,有司務會議。下轄總務處、軍務處、團務處、財務處、建設處、內處、外處、文書處、教育處、保路處等十處。處之下設組及科,如財務處轄徵收、預算及會計三組。內處之下轄監務、傳達、庶務三科是。地方制度分為畈、街與村寨兩級。各設頭人。外有大山官、小山官等之設置。芒市安撫使司安撫使之下、置護印、護理、署官、師爺、門房、庫房、差房、書房與土練等人員。地方制度分練、畈與村寨兩級。練、畈置頭人,村寨各置「老幸」(正頭人)火頭(副頭人)各一人,分管地方事務。他如隴川宣撫,猛卯安撫等土司,所設置亦大體相同。尤其干崖宣撫使司之組織,漢化的程度很深。只有聚居在滇南十二版納及瀾滄縣屬孟連一帶的水擺夷,尚保存其原來的政治形態、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因此暹羅稱之為原始泰。生在二十世紀之吾人,以文獻無徵,現已無法獲知九世紀中,蠻書成書時代即唐懿宗咸通間,居住在滇境的擺夷情況以及其條教如何?只有就滇境現有泰撣語系部族中,尚未接受漢化或漢化甚微,一切比較原始的車里土司的政治形態來和蠻書所載的南詔條教,作一比較研究,不唯因為車里土司的政治形態比較原始,並且車里宣慰使的品級,較滇西各司為高。車里宣慰使的品級為從三品,南甸、干崖、隴川、耿馬等各宣撫使為從四品,芒市、猛卯等各安撫使為從五品。車里宣慰使司宣慰使之下,設有副宜慰使等三十二大員,其官稱及職司如次:(1)曰烏巴邏閣,義為副王,吾人稱為副宣慰使。處理全境政務,則有類似國會的「司廊」制度,由各大頭目組成之。(2)曰詔景哈為司廊的首席,即各大頭目之領袖頭目,稱巴他馬阿戞摩訶些那,譯言首相,亦相當於內閣總理。(3)曰都竜稿,司內政,亦稱懷郎曼臥。(4)曰懷郎曼空,司樞要。(5)曰懷郎莊網,司賦稅,與詔景哈、都竜稿、懷郎曼空,為負責行政的四大丞相,即四大頭目。(6)曰都竜帕廈,司庫。(7)曰都竜那幹,司軍械。(8)曰都竜那夸,亦譯都竜納花,司軍政,即右將軍。(9)曰都竜掌,司大象。(10)曰叭竜那矱,司儀隊。(11)曰叭竜那禀,司諫。(12)曰叭竜過,司侍從。(13)曰叭竜那麻,司馬匹,兼御醫。(14)曰叭竜那倭,司輿乘。(15)曰叭竜榭養,宣慰使巡狩,司檢隊。(16)曰叭竜榭曩,司罿。(17)曰叭竜賽,司兵馬,即左將軍,位次於右將軍。(18)曰叭竜哈懷,司賧佛。(19)曰叭竜詔戞,司市政。(20)曰叭竜欵,司翊衛。(21)曰叭真漢,先鋒,位次於左將軍。與都竜那夸、叭竜賽,為負責軍事之三大臣。(22)曰叭榭網雷,司巡捕。(23)曰叭莊稟,宣慰使疾,司祈禱。(24)曰叭那廣,司儀禮。(25)曰叭那瓦,司船舶。(26)曰叭那郢,司刑。(27)曰叭興勒,司行舟及架橋。(28)日叭般若,司新年競舟。(29)曰叭那雷,司祈年。(30)曰叭那徽,司魚罟。(31)曰叭波猛莽,司接待緬賓。(32)曰叭波猛和,司接待漢賓等。除烏巴邏闍外,共三十一員,以詔景哈為領導,采合議制,會議處理全十二版納大事。此外尚有負責史事及文書的官員,在中樞者,稱都竜獻,或叭竜獻。在各土司地者,稱為叭獻,下一級曰鮓獻。成年丁壯,皆為戰卒。每年農隙之時,由軍頭稱為昆漢者,分區召集各家丁壯,教以征戰攻守。各家並須從事於軍備軍需的製造及供應。武器之利者:有長刀、斧、矛、弩箭之屬,近今則有鎗。有事則由昆漢率領戰卒受右將軍都竜那夸之統率指揮,從事征戰。戰事結束,與戰卒同歸於農。經過軍訓的各家丁壯,並須輪流宿衛於宣慰使司。分全境為十二州曰十二版納,以子弟分封之。領土擴展或蹙減,大都仍照十二州之數為區劃。南詔以行政區劃之名,其訓為州之「瞼」,置於地名之後,如雲南瞼、白崖瞼。擺夷以行政區劃之名,其訓為州或府之「版納」,其訓為縣之「猛」,置於地名之前,如版納景曨、版納整董、猛海、猛烏得,即景嚨州、整董州、海縣、烏得縣之謂、暹羅與十二版納同,亦以行政區劃之名,其訓為府之「章娃」,其訓為縣之「安坡」,置於地名之前,如安坡芳章娃清邁,安坡夜柿章娃清萊,即清邁府芳縣,清萊府夜柿縣之謂。車里地方制度,分為版納、猛、蠻(即村寨)等三級。每一版納轄若干猛,每一猛轄若干蠻。版納及部份猛,領以王族,稱為詔,吾人稱為土司,有土千總土把總土便委等之分。部份猛及蠻之頭目,由人民推選,有叭、鲊、線之分,受土司之監督,採合議制辦理地方自治事務。暹羅地方制度,有區域、府及縣之分,集若干府為一區域,置區督察專員一人,或增副督察專員一人,受內務部節制,處理區域政務。府置正副府尹,縣置正副縣長。分別處理府、縣政務。縣以下分區、鎮、市等三級,治理較密。已現代化,不是原始的政情了。吾人根據南詔的條教和原始泰的條教作一比較,覺差異極大,無一相似之處。由條教方面來說,南詔和泰族是大不相同的。
「南俗務田農菜圃」。稻、麥、麻、豆、黍、稷皆種之。「上官授田四十雙(唐五畝為一雙),上戶三十雙,中戶下戶各有差降」,「無貴賤皆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長丈餘,兩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牽犂,一佃人持按犁轅,一佃人秉耒」。並善治山田、澆田用源泉,水旱無損。收刈已畢,蠻官據佃人家口數目,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南詔傳云:不繇役,人歲輸米二斗,與此異)。「蠻地無桑,悉養柘蠶遶樹……三月中繭出。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為紡絲綾,亦識為綿及絹。其紡絲入朱紫以為上服。錦文頗有密緻奇采。俗不解織綾羅」。大和三年,南詔弄棟節度使寇西川,虜掠成都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歸,遂亦解織綾羅,精緻與蜀錦相埒。亦有刺綉,並產氈。自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不養蠶,以婆羅樹絮,組織為方幅,裁之籠頭,男子婦女通服之。原始泰亦務田農,唯尠蓻菜圃,大都採野蓛佐餐,水田種水稻,旱地種麻豆、黍、稷。不種麥。田為村有制,按戶均分,貴族有公田,但不親耕,例由人民代耕代種,公田所穫悉輸官,私田所穫,概屬私有,不輸官。耕田用水牛一頭,如用黃牛,則須二頭,僅一農人在後秉犁而耕,不須牽牛及持按犁轅之人。水田靠天雨,天旱則歉收。亦有溝渠的灌溉。十二版納野生桑柘均多,但無人養蠶。概種草棉,而以其絮紡紗織布為衣被之用。布幅濶一肘(稱為一索,約十八英寸),每疋約長五拿(三十英尺上下)。稱為娑羅布。十二版納尠畜綿羊,不產氈。吾人根據南詔的耕織情況和原始泰的耕織情況作一比較,差異亦大。南詔務田農菜圃,原始泰務田農而不蓻園蔬。南詔種麥,原始泰不種麥。南詔之田概由公家按上中下授予,無貴賤皆耕。所穫除由蠻官據佃人家口數目,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原始泰之田土為村公有,由村自治機構按戶均分,貴族不親耕,其田由所管人民代耕代種。官田所穫輸官,私田所穫,概屬私有。有繇役。南詔養柘蠶,抽絲織綾絹,有刺銹,並畜綿羊製氈,原始泰不養蠶,以草棉絮紡紗織布,亦有刺綉。尠畜綿羊,不產氈種種。南詔與泰族是不相同的。
蠻書蠻夷風俗第八:「其蠻,丈夫一切披氈,其餘衣服,略與漢同,唯頭囊特異耳。南詔以紅綾,其餘向下皆以皂綾絹。其制度取一幅物,近邊撮縫為角,刻木如樗蒲頭,實角中,總髮於腦後為一髻,即取頭囊都包裹頭髻上結之。羽儀以下及諸動有一切房甄別者,然後得頭囊,若子弟及四軍羅苴以下,則當額絡為一髻,不得戴囊角。當頂撮髽髻,並披氈皮。俗皆跣足,雖清平官大軍將亦不以為恥。曹長以下,得繫金佉苴。或有等第戰功褒獎得繫者,不限常例。貴徘紫兩色。得紫後有大功則得錦。又有超等殊功者,則得全披波羅皮。其次功則胸前背後得披,而闕其袖。又以次功,則胸前得披,並闕其背。謂之大蟲皮,亦曰波羅皮。謂腰帶曰佉苴。婦人一切不施粉黛。貴者以綾錦為裙襦,其上仍披錦方幅為飾。兩股辮其髮為髻。髻上及耳,多綴真珠、金貝、瑟瑟、琥珀。貴家僕女亦有裙杉。常披氈及以繒帛韜其髮,亦謂之頭囊」。管內物產第七:「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為紡絲綾,亦織為錦及絹。其紡絲入朱紫以為上服。錦文頗有密緻奇采。蠻及家口,悉不許為衣服。其絹極麤,原細入色,製如衾被。庶賤男女,許以披之,亦有刺繡。蠻王並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綴波羅皮」。「負排羅苴已下,未得繫金佉苴者,悉用犀革為佉苴,告朱漆之」。十二版納之原始泰的男子上衣短襦,冬加短棉襖,下服大檔長褲,均用深藍色棉織物縫製。挽髻於頂,或加包頭巾,佩長力,挂揹袋,袋中儲檳榔盒,菸草匣及飯簞等物。婦女上衣方領窄袖緊身短襦,衣四角作銳角形而外翹。交衽,可左右衽互換,不用紐扣,而緊以布帶,用白色或深藍色棉織物裁製,城市婦女上衣,喜用白色,鄉間喜用深藍色,下裳作筒狀,稱為筒裙或桶裙,裙長及地,分為三段,上段以紅、紫、黃、綠等色棉紗或絲、麻相間織成,作橫條子花,約佔裙長三分之一;中段最長,普通用深綠色棉、毛織物,或用織花緞料,約佔裙長二分之一;最下一段,則用白色棉織物,並鑲花緶一二周,佔全裙十分一二之長度。不御內褲。頂挽鳳髻,貴族婦女飾髻以金銀釵或金銀花朵或珠串。耳飾鐻鍝。平民耳飾多數為紅綠色通草或銅質鐻鍝,御手鐲。貴族婦女施脂粉。宣慰使及各地土司之衣褲及包頭巾,多購用漢地出產之絲織品,平民概用自紡自織自染之棉織品。清時宣慰使得穿黃馬掛。官民男婦,通無束帶,大都將褲裙最上端;摺疊緊別時臍部,工作或行路,均易鬆脫,時須重整。貴族或飾金銀質褲裙束帶,但並非為固定下裳目的而御,不過供妝飾耳。宣慰使及各地土司履用尖頭皮鞋,平民用木屐或拖鞋。入室或登樓,必須將鞋屐脫置於門外或樓梯之下,室內跣足,室外不跣足。(自稱由大理遷居十二版納、緬屬景棟以及暹羅北部山區之阿卡族人,今猶銑足,腳板粗厚如革,履荊棘如平地)。概不披氈。被褥枕幛智為棉製品。貴族與城市平民之衣飾,差距不大。統兵官與戰卒的衣著,均無特別之規定。南詔與原始泰的衣飾,並不相同。又蠻夷風俗第八:「南詔家食用金銀,其餘官將則用竹簞,貴者飯以筋,不匙,賤者搏之而食」。「取生鵝治如膾法,方寸切之,和生胡瓜及椒榝啗之,謂之鵝闕,土俗以為上味」。醞酒以稻米,「每飲酒雖闌,即起前席奉觴相勸,有性所不能者,乃至起前席扼腕的顙,或挽或推,情禮之中,以此為重」。又管內物產第七:「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採造法。蒙舍蠻以椒薑桂和烹而飲之」。宣慰使及各地土司家食具多銀製,頭目平民家食具有瓷器陶器或竹器。大都搏飯而食,亦用匙著。以糯米為主食,副食為鳥、獸、魚肉、蜂蛹、竹蟲、青蛙、蚱猛、瓜、果、青苔、酸乾筍絲及野蓛之類。嗜牛肉剁生,將生牛肉剁細,加牛血、牛尿腸羹、鹽、辣椒等拌而和食,視為上味,稱之曰「臘」,滇人通稱剁生。釀酒以糯米。貴族宴會,大都召良家女子善飲者席側侑酒,有不能勝者、侑酒女郎,須代客乾杯。無起前席扼腕的顙,或推或挽,以重情禮之俗。原始泰地區盛產茶,土入採摘嫩芽或嫩葉,用日光或蒸氣或炒使凋萎,然後揉捻,置日光下曝乾,即為成茶。食時大都先以小型瓦罐納入三腳灶火灰中燒紅,取乾茶葉一撮,投入瓦罐,不斷搖動,使茶葉烤有焦香味時,急冲入沸水,聲隆隆不絕,俟其出味,傾出飲用,別具風味,稱為雷響茶,與南詔以椒薑桂和烹而飲之的方法不類,南詔與原始泰的飲食及勸酒的情形,亦大有不同。南詔「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棟下宇,悉與漢同,惟東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別置倉舍,有欄檻,腳高數丈,云避田鼠也。上閣如車蓋狀」。原始泰的房屋,居多臨水,分上下兩層,上層住人,下層高約五六尺,畜牛馬雞豬,堆柴薪,置杵臼。貴族建屋用磚瓦木材,以多柱為貴。(車里宣慰使官邸,有柱約一百二十)格式與中土不類。平民以木或竹為屋架,屋頂覆茅草或樹葉或木片,旁建穀倉,與住宅同高度,穀倉下堆放柴薪雜物,均不得覆瓦。南詔與原始泰的房屋建築,亦有所不同。
蠻書:蠻夷風俗第八:南詔「本土不用錢。凡交易繒帛、氈罽、金、銀、瑟瑟、牛、羊之屬,以繒帛冪數計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冪」。繒帛以四尺五寸為一冪。亦用貝、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為一冪。產顆鹽之地,則交易即以鹽之顆數計之,顆鹽每顆約一兩二兩不等。十二版納之原始泰,古時行以物易物之法,繼用貝,後用鍋片銀。民國以來用銀元,鋪以銅幣。其古代載籍中,尚未發現以帛計值的記載。不無差異。
蠻書:蠻夷風俗第八:「南詔有妻妾數百人,總謂之詔佐。清平官大軍將有妻妾數十人。俗法處子孀婦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遊行閭巷,吹壺盧笙,或吹樹葉。聲韻之中,告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來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殺無罪,婦人亦死。或有強家富室責齊財贖命者,則遷麗水瘴地,法不得再合」。原始泰之車里宣慰使,一妻數妾,其第十二世始祖奢隴法,妻妾最多,然亦不過十餘人(南詔野史載,明代瀾滄江外擺夷頭目有妻數百人)。至各地土司,或一夫一妻,或一妻一二妾。男女社交公開,婦女出入不禁。少年子弟,可自由探訪任何婦女,勿論閨女孀婦或有夫之婦。有夫之婦大都能嚴守婦道,不幸有姦情敗露,最嚴重不過離婚,離婚極簡易,離婚後即可自由改嫁,不受法律限制。又「蒙舍及諸烏蠻不墓葬,凡死後三日焚屍,其餘灰燼,掩以土壤,唯收兩耳。南詔家則貯以金瓶,又重以銀函盛之,深藏別室,四時將出祭之。其餘家或銅瓶鐵瓶盛耳藏之也」。暹羅人及原始泰之水擺夷,則有火葬、土葬、水葬及天葬之不同。暹羅多數用火葬,水擺夷多數用土葬,無收兩耳貯瓶,深藏別室,四時將出祭之的風俗。白蠻死後三日內埋殯,依漢法為墓。婚喪亦互不相同。
蠻書:蠻夷風俗第八;南詔「每年十一月一日盛會客,造酒醴,殺牛羊,親族鄰里,更相宴樂,三月內作樂相慶,惟務追歡。戶外設桃茢,如歲旦然,改年即用建寅之月。其餘節日,麤與漢同。唯不知有寒食清明耳」。每年十一月一日之盛會客,相宴樂,戶外設桃茢如歲旦等,應即為南詔的新年舊俗。有類於周時之子正,改年用建寅之月,則為倣自唐曆,不為民間採用,因無所舉行。亦猶吾國改行陽曆,陽曆元旦僅機關學校有紀念。民間仍重舊曆歲旦,換桃符,燃爆仗,新年期間,互相邀宴,歡慶往返,備極熱烈的情形。原始泰之水擺夷的新年,大都在清明後十日,亦即陽曆的四月十五日,擺夷語曰「卑邁」,譯言新年。至日,勿論貴族平民,均須沐浴,更換新衣,詣佛寺賧佛,為佛像潔淨金身,然後男男女女,互相灑水祝福,並堆沙。吾人因稱之為潑水節,亦稱為堆沙節。擺夷小曆的一月,相當於我國舊曆的十月,有類於秦時的亥正。暹羅北部清邁一帶,則自陽曆四月十三日起,至十六日止為新年,暹羅語曰「宋干蘭」,俗稱宋干節。家家戶戶,打掃清潔,燃放爆竹(國內擺夷及暹羅北部清邁的爆竹,製以長尺餘,徑一二寸之竹筒,與近今國人卷紙為之稱為爆伏者不同。荊楚歲時記曰「元旦爆竹於庭」。通俗編曰「古時爆竹,智以真竹為之」是也),沐浴華裝,諸佛寺拜佛後,紅男綠女,數十萬人,遊行街巷,互相潑水為戲,其盛況遠為我國之新年所不及。清邁一帶所行小曆的一月,相當於我國舊曆的九月,行戍正。擺夷及暹羅人的新年習俗,均與南詔有所不同。
南詔的宗教信仰,有佛教、道教及汎靈。據元張道宗的紀古滇說,南詔第一世立國之主細奴邏,即已勤供自天竺前來乞食的梵僧。唐開元二年,盛邏皮遣其相張建成朝唐,玄宗賜浮屠像,南詔始有中國之佛書。其後閣邏鳳叛唐歸附吐蕃,又傳入吐蕃之密宗。異牟尋與唐使崔佐時盟於玷蒼山時,誓文中有「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管川谷諸神靈,同時降臨,永為證據」之語,則又信奉天師道,亦稱五斗米道。細奴邏封十二聖賢為十二山神。盛邏皮立土主廟,異牟尋封五嶽四潰,立三皇廟等,則又信仰汎靈。南詔的宗教信仰是頗為龐雜的。擺夷及暹羅人普遍信仰小乘佛教。十二版納的泐文載籍中累言及蒲甘王阿奴律陀事,其信仰之小乘佛教,似即傳自蒲甘,與中土無關。觀其佛寺佛塔的構造,與緬甸、暹羅的佛寺佛塔為同一型式,而與大理一帶佛寺佛塔之為中國作風者不同。暹羅的佛教宗派,則比較複雜,大約七世紀時,有由印度摩揭陀傳入之小乘佛教;八世紀時,有經由室利佛逝傳播之大乘佛教;十一世紀時,有由蒲甘傳入之小乘佛教;十三世紀時,有由錫蘭傳入之楞伽宗派。南詔與擺夷暹羅人等,雖同奉佛教,但佛教傳入的源流不盡相同。觀唐開元初遣大匠恭韜徽義至南詔建造之三塔及崇聖寺與十二版納及緬暹等地的古今佛寺佛塔的構造型式相比較,其作風完全不同。且南詔家無貧富,告有佛堂,人無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擺夷及暹羅民戶,均無佛堂之設,即僧人亦不茹素。由宗教方面觀察,南詔與滇境擺夷以及暹羅,雖同奉佛教,但差異仍是很大的。
就上舉㈠源流,㈡父子連名制,㈢語言,㈣條教,㈤耕織,㈥衣食住,㈦交易,㈧婚喪,㈨年節,㈩宗教等十項探討觀察比較下來,南詔不似泰族。
最後,吾人再來看看蠻書,新舊兩唐書及其他載籍,對南詔的族類怎麼說:蠻書六詔第三,一開始便說:「六詔並烏蠻。」又說:「蒙舍,一詔也,居蒙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姓蒙」。同書名類第四:西爨,白蠻也。東爨,烏蠻也。……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具威脅西爨,徙二十餘萬房於永昌城。烏蠻以言。語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最值得注意的是「烏蠻以言語不通……故得不徙么。「多散林谷」,雖亦為構成得以不徙的一個原因,然尚非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應為東爨烏蠻的言語與南詔不通,所以才把它列為構成不徙的第一原因,而多散林谷尚在其次。蠻書在六詔第三雖說「六詔並烏蠻」,但六詔之一的南詔的言語,與東爨烏蠻的言語並不相通。由不脅徙烏蠻的藉口推測下來,似乎南詔與西爨白蠻的言語,反而較諸與東爨烏蠻的言語為接近。證以同書名類第四「青蛉蠻,亦白蠻苗裔也……衣服言語與蒙舍略同」的記載,可以得其消息。是則蠻書六詔第三雖言。「六詔並烏蠻」,然就其與東爨烏蠻言語不通一層看來,南詔與東爨烏蠻,不無有所差別,舊新兩唐書均言南詔為烏蠻之別種者,當即以此。西爨白蠻被徙後,烏蠻種遂徙居西爨故地,與南詔為婚姻之家。新唐書:「烏蠻與南詔婚姻,其種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斂;七曰勿鄧」。唐時烏蠻仲弁田之裔烏蒙,號烏蒙部,宋封烏蒙王,元初置為烏蒙路,明改為烏蒙軍民府。明太祖謂烏蒙及附近諸部告屬羅羅族,烏蒙等名不過其支派云。南詔野史稱「黑羅羅即東爨烏蠻」。蠻書名類第四著錄南詔部族三十餘種,敘明為烏蠻苗裔種類者,有獨錦蠻、長褲蠻、施蠻、順蠻、磨蠻、栗粟兩姓蠻、雷蠻、夢蠻等。敘明為白蠻苗裔者,有弄棟蠻,青蛉蠻等。敘明本漢人者,有裳人一種。未敘明所屬者,有磨些蠻、河蠻、撲子蠻、尋傳蠻、裸形蠻、望苴子蠻、望蠻外喻部落、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綉腳蠻、綉面蠻、僧耆、穿鼻蠻、長鬃蠻、棟峯蠻、茫蠻部落、豐巴蠻、祟魔蠻、桃花人等多種。其中磨些蠻一種,雖未敘明其所屬,而置於烏蠻種類的磨蠻之後,栗粟兩姓蠻之前,南詔野史作摩些,著錄為烏蠻別種,亦即烏蠻之類。但未敘明南詔在此三十餘種部族中,屬於何種部族,抑在此三十餘種之外的一種烏蠻。不過南詔為烏蠻部族中,言語與白蠻苗裔的青蛉蠻略同的別種,則是可以肯定的。南詔野史列有南詔各種蠻夷六十條,包括南詔部族七八十種,亦未透露此烏蠻之別種的南詔大蒙國王族蒙氏之所屬。宋樂史在其所著太平寰宇記中說:「南平蠻北與涪州接,部落四千餘戶,山有毒草及沙蝨蝮蛇,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為干蘭。其王姓周(唐書作朱)氏,號劍荔王。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以其地隸渝州。按即南詔蠻是也。……其人美髮為椎髻,土多女少男。為婚之法,女氏必先以貨求男族。貧人無以嫁女,多賣與富人為婢,俗皆婦人執役」。所記蓋採自舊唐書,惟易南平僚作南平蠻耳。新舊兩唐書均作南平僚,別有南詔傳,無南平僚即南詔蠻之說,不知樂氏所本?僚始見於晉人記載。雲南通志卷一八四引皇清職貢圖曰:「相傳為鳩僚種,亦滇中烏蠻之一」。分佈甚廣,貴州、四川、湖南、湖北、陝西、廣西、雲南等省皆有之,雲南境內之僚,來自川黔桂之交。據魏書列傳第八十九僚傳曰:「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則頗似車里攸羅族之命名,而攸羅為窩泥的一個支派。清代若干紀載,且直稱攸羅為窩泥。但古籍中所紀載的僚族文化要素,如生子置水中驗浮況以定棄取,產翁坐月,豎棺而葬、鼻飲、貴壯賤老、食人、祀人頭、拔牙齒各一以為身飾等,與南詔的風俗是很不相同的,亦不同於攸羅,更不同於泰族。樂史南平僚即南詔蠻之說,殊難令人贊同。又曹樹翹在其所著滇南雜志中,則認為南詔王族是哀牢之蒲種。其言曰:「永昌城東哀牢山下,有二廟,俗名大官小官廟。每正月十六日,蒲僰會祭,城中亦往。凡水旱,官亦往禱。題神位大官則曰:大定戎方天下靈帝;小官則曰:大聖信苴利物靈帝。此必蒙氏世隆潛號改國曰大禮時,故即其始祖生長之地而祠之也。按蒙氏出自永昌直篤之裔,哀牢山其所產也。及細奴邏由哀牢避難於蒙認(按:應作蒙舍川),遂代張氏立國稱王。傳邏晟、晟傳羅皮閣(按:當作晟傳晟邏皮,皮傳皮羅閣),盡滅五詔,從蒙舍詔徙居大理、傳閣羅鳳、鳳傳異牟尋、尋都苴咩(即大理),別都鄯闡(即雲南),傳尋閣勸,勸傳勸龍晟、勸利晟、利晟傳豐佑,豐佑傳世隆,世隆追封其十世之祖曰大定戎方,蓋指創有南方之祖也。曰大聖利物,蓋指其安輯哀牢之祖也。皆本細奴邏以上而祠祀哀牢山下,以不志本始之意耳。僰人相傳:大官為叔,小官為姪,則不可考。今以小官塑像觀之,其衣服之制,俱與蒲蠻同。兩廟皆被火更建,皆易以禮服耳。惟小廟像未焚,故可考。今府縣官上任,謁城隍即謁二廟,了不知為蒙氏上祖,哀牢山土主,蒙世隆所立,故略記之。然則神故蒲而文飾則僰也。蒙段僭竊五百餘年,其本在此,蓋哀牢之蒲種也」。曹氏依據小官塑像之衣服之制與蒲蠻相同,又認為大官小官二廟,必為蒙氏世隆僭號改國曰大禮時,「故即其始祖生長之地而祠之」。遂推斷南詔王室為蒲種。其觀察研考之處,是值得注意的,惟僅憑塑像衣服之制一項而論斷,證據似嫌不足,蓋蠻書名類,言其衣服,與白蠻苗裔之青蛤蠻略同也。同時南詔傳世風俗,文化特質,與蒲蠻差異很大,尚難據為定論。至於建立大長和國的鄭氏買嗣,乃唐雋州西瀘令鄭回之七世孫,屬漢族。建立大天興國的趙氏,大義寧國的楊氏,大理國與後理國的段氏及大中國的高氏等五朝,皆屬白蠻族類。計自蒙氏細奴邏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已酉(西元六四九年)建立大蒙國起,至宋理宗寶祐元年癸丑(西元一二五三年)南詔後理國主段氏興智為蒙古所俘,南詔國亡止。凡七朝六百零五年。此七朝六氏的建國者,都不是泰族。
(按)暹羅國務院已於翌年(民國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之五月二十一日之國務會議決議,改暹羅國為泰國,並於是年之六月二十四日,正式公佈。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七期;民國66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