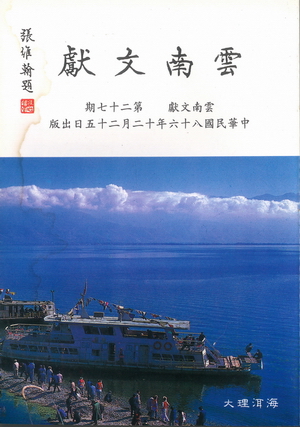張與仁將軍傳略
作者/陶任之、胡以時
抗日愛國將領張與仁(一八九二──一九六一),雲南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歷任黃埔軍校第二、三、四期學生隊長、大隊長、團長、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一師師長,第九軍參謀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昆明分校副主任,新編第三軍副軍長兼新編第十二師師長等職。為北伐、抗日訓練了大批軍事人材。抗日戰爭中,率師參加湘、贛等戰役,守備贛北,功勛卓著。抗日勝利後退役,賦閑回鄉,一九五一年被誣陷,因冤案而身陷縲紲,一九五七年始無罪釋放。一九五九年被聘為雲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迄壽終。
某些史料誤將其與張興仁(河南人,字奇峰,一九四九年去台灣)①混為一談,兩人事蹟混淆,實為大謬。
張與仁字友曾,雲南姚安馬草地村人,祖上原籍南京大壩,明洪武年間隨沐英入滇,落籍姚州。傳至乃父廷竹公,育三子三女。與公居長,自幼吃苦耐勞,勤奮好學。地方人氏乃於一九一○年保送其至雲南府第一模範中學堂就讀。時清廷腐敗,外侮內煎。與公視救國不容緩,即投筆從戎,於一九一三年考入南京陸軍第三預校,先在雲南講武學校受訓三月。期滿途經上海時,值「二次革命」(贛寧討袁之役)發生。入校不成,返雲南講武學校繼續學習。次年被保送至湖北陸軍第二預校,至畢業。又考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深造,一九一九年以優績畢業。
其時,軍閥紛爭,竟以高職厚俸延聘保定生,擴充實力。與公不為所動,認定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國民革命為唯一正確道路,遂至廣東投身革命。先後在駐粵滇軍、粵軍第一統領部(後改為軍政府大本營拱衛軍、中央直轄第一軍)任排、連長和作戰參謀等職。其間,因品學兼優,勤奮英勇,深得廖仲凱賞識,親自介紹其參加國民黨(一九二○年)。一九二二年與公任少校營長參加北伐,所部率先攻入江西。繼又加入東路討賊軍、回師討伐陳炯明。一九二三年在駐粵滇軍總部幹部學校任主任教官。
一九二四年六月,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創建後,與公由校黨代表廖仲凱向蔣介石推薦,被任命為該校第二期步科第一隊少校隊長。一九二五年一月升任第三期第三大隊中校大隊長。一九二六年一月升任第四期步科第二團上校團長(該期入伍生二三一四人,初為兩個入伍生團,三月一日入伍生升學後編為步科第一、第二兩個團和工、炮、經理、政治等科四個大隊)。在職期間,與黨代表廖仲凱、教育長鄧演達(保定軍校同學),總教官嚴重、教授部主任葉劍英等相善,多有過從。
同年冬,奉命率第四期畢業生至南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與第二次北伐。與公旋被任命為新編第一師師長,駐贛州(同時發佈的任命為任命新編第二師師長葉劍英,駐吉安)。②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寧漢分裂。由於張、葉兩師「新兵多,部份是農民講習所骨幹、黃埔學生和共產黨員,蔣介石命令遣散。葉部回廣州後於十二月發生廣州事件,張則到南昌」。③與公繼奉鄧演達電,赴黃埔武漢分校任教官。未及三月,武漢政府解體,分校停辦,乃應第五路軍總指揮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之邀,出任朱部第九軍參謀長(軍長金漢鼎)。次年冬,蔣以整編軍隊為名,將朱部第三、九軍縮編為第七、十二師,金漢鼎任第十二師師長,與公任參謀長,第卅五旅旅長,駐防海州。
一九三○年秋,與公調任軍事參議院參議。其自任軍職以來,處事剛正,操守清廉,惜將愛兵,深受部下擁戴。赴任履新時,火車經過新安鎮,駐防該地之所屬第六十九團全體官兵列隊車站,名為歡送,實為反對師長,索求積月欠餉,高呼「擁護張旅長」等口號,事態頗為嚴重。與公顧全大局,耐心撫慰,始未釀成嘩變。此即所謂「海州事件」。朱只得將金調走,以曾萬鍾替任,並函慰與公。④與公鑒於軍參院既無所參,亦無所議,未就職。當時,民眾反日情緒高漲,乃應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等將領之邀,赴該軍第六十一師任幹部教導總隊(後適應抗日作戰需要,改為新兵訓練處)主任。為後來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一九三二年)輸送了大批幹部和戰士。
一九三三年,收編訓練黃埔軍校編餘軍官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研究班(後稱特別訓練班)於江西成立,與公被聘為該班少將副主任,負責軍事訓練。某次,蔣介石視察,見其親率學生清晨跑步,爬五老峰,繼又進行術科訓練,不禁脫口贊嘆:「張與仁真是個鐵牛!」一時廣為傳誦。
一九三五年,與公回鄉奔父喪,途經昆明。雲南省主席龍雲以地方建軍需要,再三挽其留滇工作,並報經蔣介石批准;與公亦願服務地方,以報桑梓,遂於一九三六年調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昆明分校(亦第五分校)少將副主任。與公嘗言:軍校畢業生今後都是抗日骨幹,國防棟樑,軍事學、術各科均須築下穩固基礎,方堪重任。故不僅要求教官和帶隊官佐從嚴施教,更身體力行。常親自帶隊清晨長跑,深夜又演練緊急集合,作戰備急行軍,風雨不避。對野外戰術訓練及實彈射擊亦常親臨示範指導。故學生曾戲稱其為「大排長」。另方面,與公對學生關懷愛護備至,曾告誡全校官佐:帶兵愛兵,對待在校學生必須如同對待自己子弟。明令不准剋扣伙食,並常往大廚房檢查。深夜又常巡視宿舍,為貪涼學生蓋好棉被。某次在醫務所檢查時,發現一被校醫診為感冒高燒之學生病情異常,即派車送往慈群療養院(當時昆明最好的私立醫院),診斷出係傷寒症,經搶救治療月餘始痊癒。幸是送該院及時才救了這條性命。學生既畏其嚴,又敬其正。該校當年畢業生,大多分配在第六十軍、五十八軍、新三軍等雲南部隊。抗日期間,其中許多人榮立戰功,或為國壯烈捐生。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龍雲赴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議,許諾雲南出兵廿萬抗日,回省即設立雲南總動員委員會。與公被任命為該會委員並滇黔綏靖公署幹部訓練總隊總隊長,承擔為雲南出兵抗日訓練和輸送軍事幹部之重任。
一九三九年九月,與公被任命為新編第十二師師長(先屬第五十八軍,後與第六十軍之一八三師合編為新三軍)。與公是見報紙上發表始知任命,事前未與所聞。其人之不善鑽營,於此可見。十一月率師開赴前線,在湖南攸縣經軍政部點驗,獲優績好評。旋駐守江西萬載,再調防湖南平江。自此直至抗日戰爭勝利,率部投入日日夜夜之守備戰難以數計,更多次參與日我第九戰區組織的重大戰役,比如:
一九四○年十二月,九嶺戰役。日寇進攻我五十八軍守備之九嶺陣地,進窺平江、瀏陽、威脅長沙。與公率部參與激戰,協同新十一師、新十師將敵擊潰。
一九四一年三月新十二師歸屬新三軍建制,調防贛北,扼守高安、奉新第一線陣地。與公以戰功晉升中將副軍長兼新十二師師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第三次長沙會戰開始。新三軍守備贛北錦江北岸高安縣東馬形山、馬奇嶺至角湖里吳之第一線陣地,正面寬約五十公里。一八三師為左翼,新十二師為右翼。南昌日寇第卅四師團為策應進犯長沙之敵,於二十五日九點開始,向新十二師據守之前進據點和馬奇嶺、姑婆大坵主陣地猛攻。另一小部則向一八三師陣地作牽制性佯攻。新十二師激戰至十五點將敵擊退。入暮,敵繞襲我主陣地並施放毒氣。我將士雖中毒氣,仍苦戰與敵相持竟夜。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戰鬥更為猛烈,全師將士浴血奮戰,多次展開肉博,擊退敵人輪番猛撲。二十九日總部電令反攻。次晨七點,與公親赴第一線指揮,官兵士氣大振,向敵猛衝。戰至十點,我官兵雖斃敵過半,自己傷亡亦已過半,攻擊期進展,乃一面抗擊,一面轉移至湖城圩,余家之線,阻擊西進之敵。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全軍開始反攻,來犯之敵向奉新、南昌方向退卻。四日,湘北之敵被友軍擊退。六日,策應湘北作戰而向我贛北進犯之敵遭受重大傷亡後,亦退返原陣地。是役,新十二師奮戰抗敵,不畏犧牲,認真執行了九戰區長官司令部關於「逐次抵抗,以消耗遲滯敵軍,後退決戰,反攻殲滅」之作戰方針。全軍共斃傷日寇大隊長以下官兵一六○○餘名,俘獲敵軍槍械裝備、戰馬軍刀無算,粉碎了日寇打通贛湘公路,會合湘北之敵的夢想。我新十二師營以下幹部多人英勇為國捐軀,除預備的一個團外,參戰兩個團壯烈犧牲,負傷的士兵亦近半數⑤。
「滇軍史(稿)」「第一集團軍第三次長沙會戰」一章中評曰:「斯役也,青山浸透英雄血,溝壑填滿倭奴屍」。「贛北方面,主要是新三軍作戰。而新三軍這次作戰,主要又是新十二師一個師作戰。」「新十二師死傷最為慘重,第一八三師則甚輕微。……由此可判明敵軍主攻指向。新十二師遭受如此重大傷亡,與上述各級(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第一集團軍副總司令)指揮不當有關。但一八三師師長李文彬心存觀望,奉令援助亦多敷衍塞責;有意保存自己實力,犧牲友軍有以致之。」⑥
此戰結束後,與公不因此戰代價慘重諉過責人,而是念念不忘「青山埋忠骨,豐碑寄忠魂」。將收集所得陣亡將士忠骸,在高安龍潭鄉老虎山建國殤公墓營葬,立碑銘文誌忠烈,慰英靈,教後人。未意數十載滄桑,今見該公墓碑竟已被當地之人拆作橋板。幸當年親歷該役並受命手書該碑文之陶任之將軍,數年前重臨該地,尋得殘碑,磨洗辨認,尚抄得部份碑文如下:
「日寇侵占武漢、南昌、廣州後,恒思打通粵漢線,以達其縱貫南北之目的。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下旬,南昌之敵向我發動進攻,狼奔豕突,猖狂若無阻。本師健兒咸抱必死決心,在蓮花山、米峰一帶地區與敵週旋,前仆後繼,勢不兩立。戰十餘晝夜,卒將頑敵擊潰,斃其大隊長以下千餘人,使不能與湖南岳陽方面敵會合,完成空前大捷。是役我官兵殉國者六百七十三人,即今累累在墓者也。嗚呼,諸烈士為國家民族生存,離鄉萬里,在艱苦環境中鏖戰旬餘,卒獲勝利,忠勇壯烈,直可驚天地、泣鬼神矣!與仁忝膺師長,未能與諸烈士痛飲東瀛,以慰素志,其豐功偉績,寧忍湮沒而不彰耶?爰收忠骨,葬於老虎山,立貞泯,以利後人之景仰雲爾,是為序銘曰:懿歟烈士,氣薄穹蒼。疾彼醜虜,殺伐用張。未飲三島,齋志雲亡。匡山贛水,萬古流芳。……」⑦
長沙第三次會戰結束不久,日寇意圖打通浙贛線,進窺吉安,側擊長沙、衡陽、又於一九四二年五月集結滬杭日軍企圖夾擊我衢縣,鷹潭、進賢。二十七日敵三十四師團自南昌進駐蓮塘,進犯三賢湖等處。敵第三師團沿撫河東岸分向東鄉、臨川急進。敵第六、十三、卅九、四十、一一六等師團和第十四旅團亦均有支隊參戰,另加偽軍五千餘人,分別向我贛東南城、臨川、三江口之線進犯。我九戰區長官司令部為策應第三戰區浙境我軍作戰,除已令贛北、鄂南、湘北前線我軍適時出擊,牽制敵人外,組織了此次贛東會戰。先後調動第七十九、第四、五十八軍,新三軍新十二師,新二十師和保安縱隊,分別在臨川、宜黃之間和撫河、贛江之間進行反擊。與公奉命率新十二師以主力固守清江。對一部竄樟樹、西渡贛江、進犯蛟湖之敵給予了迎頭痛擊,敵死傷數百,不支,潰退回東岸返南昌。八月下旬會戰結束,我方十個師、一個保安縱隊,徹底粉碎了敵人企圖,共斃傷敵軍一萬三千餘人,斃敵馬三千餘匹,俘敵軍官十餘名,奪獲槍械甚多。⑧
不久,龍雲疑忌出戰滇軍為蔣介石所收買,撤換了一批被其疑為親蔣的將領,在龍的心目中,與公與中央淵源較深,乃撤去其新十二師師長兼職。⑨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眼見國共爭端又啓,內戰危機日重,與公深感國民亟待休生養息,不願再同室操戈,重開內戰;加之,秉性剛直不阿,自信身為職業軍人,只知保國衛民,對軍隊中之派系爭奪、人事紛爭,深感心力交瘁,極為厭惡,即退役賦閑。
一九四七年,與公被故里選為國大代表,南京參會。其後,第十五綏靖區成立,欲任其該區副司令,堅辭不就,爾後返鄉。
一九四二年,與公夫人在家鄉出資建啓明小學一所,自任校長,教師大多自昆明延聘。與公返鄉後,更悉心辦學,發展地方初級教育。又常為鄉人施約治病,修築鄉林道路,鄉人普遍稱贊。
一九五一年二月,姚安發生「滇西反共救國軍」案,株連三百餘人。與公被誣為「首領」,被捕入獄,關押在昆明。一九五七年始經查明並無此事,無罪而釋。⑩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病逝於昆明,享年六十九歲。
楚雄彝族自始州地方誌辦公室於「楚雄人物」一書中為之立傳,讚曰:「張與仁為人正直,重然諾,好勤儉,惡鑽營,為時人尊重」。
註釋
①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劉國銘編:「中國國民黨九千將領」,第三七六頁。
②雲南大學出版社,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誌辦公室編:「楚雄人物」,第一七四頁。(一九九○年)
③雲南省政協編:「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始末」(一九八二年油印本)
④同②,第一七五頁。
⑤雲南文史研究館:「雲南文史叢刊」一九九一年第三期,「滇軍史(稿)」編委會編「陸軍第一集團軍第三次長沙會戰」
⑥同上。
⑦上海書店,雲南文史研究館編:「雲嶺拾穗」,陶松撰:「揮淚讀殘碑」。第四八頁,(一九九四年)
⑧江西省政協編:「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總第十六輯,第八九──九一頁,五七頁,宋瑞珂撰:「贛東會戰」。(一九八五年)
⑨雲南省政協編:「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第二十三──二十四頁,胡俊撰:「近二十年來雲南地方軍隊概述」。(一九六二年)
⑩同②,第一七七頁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7期;民國86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