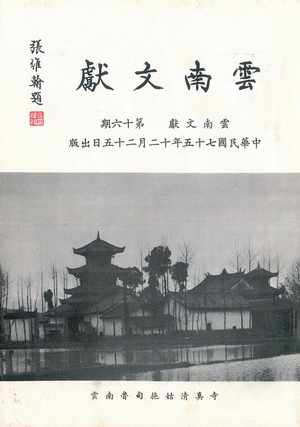迤東各屬沿革誌略
作者/廖位育
國人皆知我雲南亦稱三迤,即迤東、迤西、迤南。
迤東地形,如巨麟一臂,向東北伸展,地扼雲、貴、川、康四省之樞紐,形勢險要,崇山峻嶺,金沙江由西南而來,向東北走向,流入四川,形成與川、康二省間之天然省界;東亙烏蒙山脈,與貴州接壞。境內計有綏江(原名靖江)、鹽津(原名老鴉灘)、永善、大關、彝良、威信、鎮雄、昭通、巧家、魯甸、會澤(原名東川)、宣威等十二個縣,毓秀鍾靈,可謂人文蔚起,民國以還,如唐公繼堯、龍公志舟、張公蒓漚,……等人物,皆籍屬迤東。
其實,迤東早在漢代即已開發,西漢元帝時代,就出過大學問家孟孝琚,仁聲孝譽,學識品德,遐邇皆傳,其墓就在昭通城南,史書上即有明確的記載,墳墓至今猶存。那時,這一廣袤的區域,漢帝特置朱提(讀時)縣治理;東漢末年,改朱提縣為朱提郡,兩晉因之。南北朝之際,中國四分五裂,北朝有所五胡十六國,南朝則為宋、齊、梁、陳。迤東區域,一直屬於南朝疆土,南宋仍為朱提郡,劉公南齊,將朱提郡分為南、北二郡,北名朱提郡,郡治設今四川省宜賓縣,南名南朱提郡,郡治未動,就是今日之昭通,至今昭通小西門之城門題額,就是「朱提古縣」四字。今天,許多書籍,甚而包括流行最廣之工具書「辭海」,都將「朱提」解說是四川省宜賓縣,那是錯誤的。原因是朱提郡改為南朱提郡之後,史書上記載說「後沒於蠻」│即被原住民土著彝族佔據統治了,改而將後來之朱提郡變成為原始之朱提郡,反而使原來之朱提郡為之湮沒不彰。
隋、唐三四百年間,也許地處西南,中央力量鞭長莫及;也許彝族統治,承平無事,故史書上鮮有記載迤東境內之大事。而地勢重心,似乎也隨之東移。
據讀史方輿紀要第七十三卷記載,北宋神宗熙寧末年,朝廷為羈糜蠻族(實即彝族,稱彝為蠻,可謂由來已久,至今迤東一帶,漢人稱彝人為蠻族,彝族同胞也認為當然,從不以為怪。)就在鎮雄設置「西南番部都大巡簡使」,作為政府官署,顯彰王化。自此以後,迤東區域之隸屬,即代有變化,時屬雲南,時屬四川,直到清雍正初期,雲貴總督鄂爾泰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正式改隸雲南,二百餘年來,就未再變動了。
前言迤東地勢重心之東移,即據「西南番部都大巡簡使」而論。
元末,大約於元順帝至正年間,即以宋置之「西南番部都大巡簡使」為據,在鎮雄置「芒布路」,芒布,本為彝族一個部落首領之名字,統治鎮雄一帶,宋稱芒布部,元因而設置「芒布路」,下轄烏撒宣慰司(今宣威及貴州威寗一帶)及烏蒙宣慰司(今昭通、魯甸、巧家、永善一帶。)隱然成為迤東之政治中心了。
茲為便於敍述計,乃以明初先後於迤東設置之四大軍民府為綱,以誌其概略:
一、鎮雄軍民府│即宋初之「芒布部」,神宗朝之「西南番部都大巡簡使」,元末之「芒布路」,明初之「芒部府」,本屬雲南布政司,明太祖洪武十六年(西元一三八三年)升為「芒部軍民府」,改隸四川布政司,明世宗嘉靖三年(西元一五二四年),改為「鎮雄軍民府」,仍隸四川,下設長官司四:①懷德長官司(治地不詳)。②威信長官司(今威信縣)。③歸化長官司(今彝良縣)。④安靜長官司(治地不詳,以地望推側,可能為今之大關縣),可見有明一代,鎮雄在迤東地區,確佔有重要地位。
二、烏蒙軍民府│唐時號烏蒙部,宋封為烏蒙王,元代歸附朝廷。元順帝時置「烏蒙路」,明初改「烏蒙府」,明太祖洪武十六年改為「烏蒙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轄今明通、魯甸一部、巧家一部、永善、綏江等縣,治昭通。今昭通西北十餘里有「舊府」,郎其治所。
三、烏撒軍民府│今宣威及貴州威寗一帶,宋時號烏撒部,元順帝至正年間,設「烏撒路招討司」,後改為「烏撒軍民總管府」、「烏撒軍民宣撫司」,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西元一三八一年),改為「烏撒府」,屬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烏撒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
四、東川軍民府│為唐時南詔國所設之東川郡,後為彝族集據,元末設東川府,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得其地,仍名東川府,屬雲南布政司,洪武十六年,改為「東川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
由上可知,迤東各屬,自今日之霑益縣及尋甸縣以北這一廣大區域,明清以前之居民,彝族同胞的人數,可能居第一位,隸屬上雖時川時滇,但都以便於羈縻彝人為著眼,而三國之際,諸葛武侯的南征勁旅,就是經迤東而西指,渡瀘水直達今日之緬北的,在永善、巧家等縣,當年諸葛武侯南征之遺跡、遺物,仍所在多有,時有發現,並非耳食之人所謂的獉狉未啟之區。
迤東各屬之設縣分治,除幾個重要之縣名沿用舊時名稱之外,其他縣名,大多為雍正朝設縣分治時所賦予,如彝良寨之改名彝良縣,巧家營之改名巧家縣;至於靖江之改名綏江,則為民國時代的事情,蓋北伐統一以還,鑑於國內許多縣名有重複之處,易滋混淆困擾,故統一規劃改名,比如江蘇省有嘉定縣,四川省也有嘉定縣,於是將四川省之嘉定縣改為樂山縣;四川省有長寗縣,江西省也有長寧縣,於是將江西省之長寗縣改為尋鄔縣;而迤東有靖江縣,江蘇也有一個靖江縣,所以迤東的靖江縣就改為綏江縣了。還有鹽津縣,設縣更晚,原屬大關縣的老鴉灘,因為係四川磚鹽運入迤東的主要進口地之一,故名為鹽津,記得似是抗戰前後的事情。
迤東居民,漢、彝、苗雜處,漢民族已佔絕對的大多數,原住民的彝族同胞,除了一部份與漢人雜居之外,凡聚部落而居者,大都西渡金沙江伸入川、康、滇間的大、小涼山居住去了,是以沿金沙江各縣之間。幾乎沒有明確的省界縣界可循,人為的分界對他們也毫無意義。苗族同胞大多居於山區,人數雖不甚多,但內部分類卻不少。
迤東居民的語言,彝族同胞不但有其獨立的語系,也有他們自己的文字,不過,他們自己能識彝文的人反而很少很少,卻絕大多數會漢文、漢語;苗族同胞也有他們自己的語言文字,而識他們自己苗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這兩個民族,大多能說流利的漢話。漢民族之入居迤東,最早者已無從查考,明清間先後有大批的漢人湧入,一是明成祖征雲南時率往前去者,一是清雍正改土之際,由江西、湖北、湖南移往者,一是乾、嘉年間,散漫絡繹而入住者。大致說來,迤東漢民族的語言,綏江、鹽津、大關、威信、彝良、鎮雄六縣,幾乎完全說四川話,永善、昭通、魯甸、巧家、會澤等五縣,沿金沙江者說四川話,餘則說雲南話,宣威縣的口音,似乎介於雲南話和四川話之間乃是以上兩種口音之綜合與中和。
自清雍正時代雲貴總督鄂爾泰施行「改土歸流」以還,迤東各屬,不但又由四川改隸雲南,而且分疆析界,設縣治理,遂確立了迤東各屬的根基,土司勢力日削(實則並未絕滅),流官之制日固,昭通又成為迤東行政、軍事、商業等之中心,以迄今日。
「鳳凰啣荔枝,飛入龍洞;
八仙捧元寶,奉上天梯。」
這是昭通人引以自豪的昭通名勝,綴成佳聯,朗朗有聲。鳳凰山,荔枝河,八仙海,元寶山,這些地方,求學期間的遠足、郊遊,採訪過不止一二次,只有龍洞、天梯山距城稍遠,沒有去過。尤其明通城外的葡萄井,清潭一泓,水珠由井底冒出,如串串葡萄,晶瑩剔透,行人到此,必手扶井上石欄,頻呼「葡萄葡萄起」,於是,串串葡萄,如串串明珠,自井中升起,冉冉姍姍,到水面而散,真是嘆為觀止矣。據說,行人如到井邊喚不起葡萄,則當年必走霉運,諸事不宜云。
昭通城郊也有望海樓,古色古香,所望之海,乃八仙海。而今,山河易色,垂四十年,望海樓,不知能翹首以望東海王師否?藍關秦嶺雨茫茫,何時得賦歸去來?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六期;民國75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