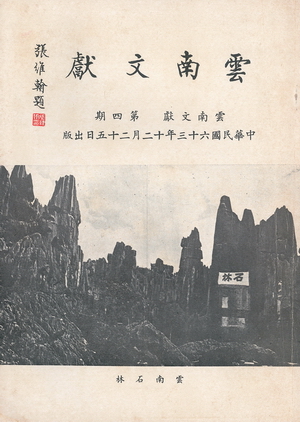昆明至臺灣
──紀述由昆明經緬甸泰國寮國及至臺灣的一些往事──
作者/朱心一
一、討逆未遂 奔向自由
溯自卅八年十二月九日,前滇省主席盧漢叛變通電附匪,適我由昆明回籍(宜良)掃墓,當茲遽變翌日,即與縣黨部書記長李濟蒼兄(陷匪區),駐軍部隊長田樂天(前廿六軍四八二團團長,現在臺)田茂林(前憲兵十八團團長,在臺)兩上校,及宜邑民眾自衛總隊長張匡侯,副總隊長王允中兩鄉長(均陷匪區),於城中湛園聚議,密商討逆大計,冀圖效唐蔡諸公,於民國四年在昆明歃血為盟──討袁──再創「護國起義」的光榮史蹟。
歲暮冬殘,風雲日亟,頓時昆宜間電訊交通均已中斷,滇越鐵路南段軍運則形頻繁;旋廿六軍軍部由滇南移駐宜邑,大軍雲集,民心浮動,軍方為謀求地方力量之適切配合支援,彭代軍長爰于十二日黃昏邀我地方紳首懇談,並出示中央所頒電令指示及其致盧漢電報,其電文委婉中肯,敦促立即釋放國軍前第六編練司令官兼八軍軍長李彌(在臺)及前廿六軍軍長余程萬(已故)兩將軍,俾資共策和戰大計。最後復再三嘉許我宜邑紳民之忠貞大義,尤盼羣策羣力,同挽狂瀾,共襄討逆護國義舉。
是夜(十二日)即由我執筆發出緊急通知,于十三日上午召開黨政軍聯席會議,決議改組縣政府(斯時縣長劉國舉已被廿六軍軍部軟禁停職),一致推舉議長段克明先生(已罹難)代理縣長,並徵召我任主任秘書,(時我任滇省黨部執委,兼昆明市黨部副書記長,青年館總幹事及宜良縣參議員等職)適段代縣長因事在省垣,而由我暫代行縣長職務,為籌集糧餉以應軍事緊急需求,日夜奔走呼號,確有廢寢忘餐之情;未及一週,計籌獲食米八十四萬餘千斤,滇鑄半開拾萬餘元(折銀元伍萬餘元),悉交廿六軍軍部統一分配。(含第八軍孫師及憲十八團)
十六日夜廿六軍彭代軍長再次邀我地方紳首晤談,由於籌欵未達他所指定的拾萬銀元(折半開貳拾萬元),他一開口竟把「弔媽娘」的廣東口語搬了出來,一面拍桌,一面責罵,由盧漢罵到全滇民眾,不分青紅皂白,並聲稱要扣押在場的紳首,槍斃我和張王等實際負責人。是以逼得我忍不住而坦率申辯:「報告軍長,雲南一千三百餘萬民眾,並非人人附從盧漢叛變,就以我們宜良的紳民來說,當聽到盧漢叛變之日,在尚未奉到任何令示以前,就主動與駐軍兩位田團長聯絡會商,縝密計議討逆義舉,假使軍長竟把我們也認為是叛徒,那麼這幾天我們日夜不歇的籌集糧餉是為什麼呢?」當他還要再次拍桌斥責的時候,幸承在座的田茂林團長起立仗義執言:「報告軍長,就部下所見,本團從湘南撤退到現在,尚未見遇有如宜良各界對國軍這樣主動支援合作的情形,我看這裏籌糧無問題,惟籌欵確有困難,請軍長再派員調查瞭解,並希對他們幾位多加鼓勵……」。至此彭方息怒,惟仍帶慍意地說:「現在中央已有命令給我,要本軍和八軍共同進攻昆明討伐叛逆,所以要請各位動員地方一切力量多多支援,將來我一定要報請中央好好的獎勵你們」。說罷復出示致盧逆最後通牒電稿略謂:「永衡先生大鑒:迭電未獲復示,茲決與八軍袍澤聯合向昆明進軍,若仍執迷不悟,屆時玉石俱焚,在所不惜」其電文義正詞嚴,當獲與會人員一致鼓掌贊應,將近戒嚴時間了,我們一行辭出後,鄉賢王香翁(前教育局長)段瓊翁(前文獻會副主委)相繼拍著我的肩膀說:「還是你這個青年敢為敢說,否則我們大家都成了叛徒,雲南好像就沒有一個忠義之士了」。又說:「官當大了,若不察情講理,國家何能有救?」撫今憶昔,這幾句話猶發人深省。
討逆部署就緒,廿六軍軍部率梁石兩師於十七日凌晨,次第自宜良沿滇越鐵路北上,葉師則仍留駐宜良以南地區戒備;是日聞李彌將軍已獲釋,旋立即在昆明東郊召集所屬重要幹部會議,並由適在滇中巡廻宣導之名學人丁作韶博士,專負與廿六軍逕行聯絡協調之責,以期步調一致,併肩進攻昆明。迨至十九日廿六軍首攻輕取巫家壩機場,廿日兩軍已進據昆明市東南北郊區形成緊縮包圍之際,盧逆見勢情急,再行釋放廿六軍軍長余程萬暨一九三師師長石補天,並準備率保安團突圍西竄。余石獲釋後分乘插有白旗之吉普車由南疾馳出金碧路,當經過得勝橋頭見哨兵乃所屬四八二團官兵,竟大聲呵斥「不准開槍」、「不准前進」、「趕快撤退至呈貢聽軍長訓話」、「軍長另有指示」……等語;余石沿途喊話甚為見效,所部不明究竟而被迫盲從後撤,時在昆明東北郊區之第八軍所部,見狀亦不知所措而跟隨南撤,情勢混亂,撲朔迷離;兩軍官兵莫不頹喪咒罵,有者並痛哭流涕,斯時由呈貢至宜良道上,偶見「槍斃余程萬」「擁護彭佐熙」「把余程萬押解臺灣審訊」等標語。
廿四日午後廿六軍軍部南撤復返抵宜良,聞余彭兩將軍為和戰主張而沿途齟齬,其所屬亦形成主和與主戰的兩派,斯時軍心渙散,士氣空前低落,與一週前北上進伐昆明時,慷慨激昂的義憤,實形成一強烈的對比。是夜(廿四)該軍政工處長郭璞少將及經理處區代處長又來縣府看我,除告知上述情況及張岳公、裴存藩(前滇省黨部代主委,現任立法委員,在臺)兩先生已脫險赴臺等消息外,並懇切的要我繼續籌補糧餉。聽罷我不禁深為太息的說:我原準備籌組一致敬團,于明白「護國」紀念去昆明五華山向你們祝捷致敬的,萬想不到今天還要我替貴軍籌辦撤退的糧餉,對不起,我實在無能為力了。話畢他兩似甚尷尬並也無可奈何的說:好吧,我們已多日沒有睡覺了,也深知你的困難,那就明天再談罷。
廿五日是「雲南護國起義」的光榮紀念節日,原擬擴大慶祝一番的;惟處此風雲亟變,軍民紛亂的狀態下,自然無法集會紀念,只有繕貼幾張緬懷革命先烈激勵士氣,安定民心的標語罷了。是日軍方意外地無人來催索糧餉,幾經探聽,據悉為盧漢派人送了大批慰勞品及相當數字(不詳)的現欵交廿六軍軍部用示懷柔;又軍部曾召集營級以上的主官舉行決策會議,傳為和戰的關鍵問題又爭吵不休,最後決定迅即南撤至蒙自與第八軍會合,聽候中央派大員來滇統一指揮。是夜張匡侯、王允中兩鄉長突然不知去向,李濟蒼兄亦倉促決定要隨廿六軍軍部行動,斯時我已形成孤家寡人,真正陷入臨深履薄,進退(其實是留或逃的選擇)失據的艱危境況了。由於多雨乍寒,室內已燃起爐火,為研商今後變局及個人出處,爰再邀地方紳首至縣府共策良圖,彼此開誠相商,一致決定要我再為苦撐維持,萬不可遽爾遁離,否則地方將糜濫不堪。在與會人員的一致勸勉下,我這個向來不計個人利害得失,也不諳官場世故的傻瓜,只有憑其青年具有的血性與勇氣,再事忍辱負重的苦撐危局;午夜送別他們後,剩下的只有我和一位趙姓的衛兵兩人,徹夜團爐閒敍,是為生平最長的一夜。
廿六日天方黎明,先後接聽了田茂林、田樂天兩位團長的告辭電話,皆謂馬上就要登車南下了,連聲「無顏回見……」並互道勿忘這段患難中的情感道義;話畢我又派人立即各送上半開參百元,藉作他們旅途應急之需;迨至四十一年五月我回臺受訓晤及田茂林上校時(時任憲部副參謀長),他對此猶念念不忘。是日午後又有前中統局的李紹寬、劉琦、彭學勤等六位同志來訪,一見他們那套布商小販的打扮,我已知道他們是剛由昆明逃出來的,沿途歷盡艱險;其中李同志(即現在臺的知交李紹寬大哥,也是卅九年夏在緬北邂逅,曾勸留我在緬共同從事游擊工作的初期領導人)能言善道,見解深遠,相談頗為投契。記得我當時的應答曾有這麼幾句:「我不是縣長,更不想過這份官癮,惟處此大難當頭的時候,我僅本國民黨一個忠貞黨員的立場,竭盡我對黨、對國家、對地方應盡和能盡的責任,其得失生死已置之度外矣」。是夜我復親往悅來旅社回拜他們,並代他們結付了房錢,翌晨又請他們吃了一餐早米線,並致送少許旅費,分手時祝福他們好運。旋未及半年,這幾位烽火中的志士,竟在緬北臘戍又邂逅了三位。「人生何處不相逢」,這一句話正是我與上述幾位同志散而復聚的寫照。我想:假使當年我們都做了愧對黨國或有虧天理良心的事,今天在臺灣怎麼還好見面呢?所以說做人處事總是要厚重一點的好,並須從長遠方面著想,萬不可勢利現實。
廿七日郭璞少將又來催索糧餉了,寒暄後他們曾坦率的說:「老弟:我也是雲南人,我絕不致做出昧心或忘本的事,你若堅拒不給糧餉,部隊當會自行動作,屆時吃虧的還是地方民眾呀!」接著又對我作了一番耳語,證實了廿六軍軍部決于明日(廿八)移駐蒙自的傳聞;送離了這位大理籍的少將處長後,又連忙邀請地方紳首集議,決定再籌食米拾萬斤,半開貳萬元支援他們以應南移所需。嗣將此一決議以電話告知郭處長,幸獲他滿意的答謝,並告知彭佐熙將軍已奉中央電令,正式真除軍長;石師仍留駐宜良,將來若有行動盼我與之同行,這番話算是有點人情味。
卅八年畢竟在天昏地暗,兵慌馬亂中過去了;除夕夜我深感局勢日非,似不可能再從「好轉」的方面打算了,爰親電匡遠鎮王鎮長、請鳴鑼通知城區居民,明晨(卅九年元旦)各家戶均須一律懸掛國旗誌慶,俾縣民能再觀青天白日的國旗。元月二日凌晨,詎料石師竟不辭而全員南移,並炸燬了滇越鐵路南下的狗街大鐵橋;斯時我真氣憤填膺,頓感欲行無路了。是夜復邀地方紳首話別,申述我不宜再留的苦衷,當承一致同情促行;三日凌晨趁土共董剛部入城忙於竊收混亂之際,我即與會者隨帶旅費半開壹百陸拾元,化裝潛離縣府,並承莊霞飛(前一八四師副師長)先生自願陪伴逕赴昆明期由滇西逃出虎口。嗟乎!臨危受命,暫代縣長廿一日,由於時勢所迫竟狼狽逃離,真所謂「掛印封金」是也,這當是宜良縣政府有史以來任期最短其處境最為艱危,而對國軍支援最多的一任也可能是全中國大陸淪陷前,最後苦撐危局的縣長之一。於今思之,匪偽份子對我之「通緝」「清算」乃理所當然,想我對地方父老之毀家紓難,及其仗義信任與大力支援,而未及作一清楚的交代,不無「棄職不顧」之嫌,或有「懸案待究」之責;言念及此,衷心益增愧作惶悚。
卅九年春節甫過,匪軍陳賡部已進踞昆垣,時代理滇省偽臨時「人民政府」主席楊文清(已故)會邀我晤談,囑我與劉××兄(陷匪區)出名召集在省垣之黨(中國國民黨)團(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同志會餐,屆時他將親來參加,並願代同志們一轉組織關係,保證加入尾巴黨派「民革」。辭出後,××兄很得意的問我:「怎麼樣,鏡老(鏡涵為楊之別號)對我們還是很愛護的,老弟!別頑固了,明天就發通知吧」我當即毫不考慮的回答:「對的,鏡老是位忠厚長者,他的好意我們敢不從命,但轉變組織關係,必須先搞通思想,否則別人一問三不知,我們將被人譏為盲從依附」。這話承他勉強的同意,連稱:「好好,稍緩再說」。
記得是三月中旬的某日午後,我的秘密住所,突然來了一位久未見面的女訪客(時任偽職),承她過譽的送了我幾頂高帽,並非常委婉動人的勸說:「你是國民黨的開明份子,地方的有為青年,過去我們道雖異,但志尚相同;今天全中國大陸都已解放了,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需要你貢獻緻你的智慧和力量,讓我們緊密的攜手,共同完成偉大的世界革命……祖國需要你,人民需要你……」。說罷,順手從布背袋裏取出幾本小冊(新民主主義、新經濟政策、論人民民主專政、如何自我改造、現階段革命應有的認識和主張等)懇切的要我加緊學習;於此,我自知已受匪偽份子的注目了;若再猶豫觀望,當無脫離魔掌的機會,是以遂即下定決心逃離鐵幕。
經半月策劃摒擋就緒,猶不敢回籍與家人告辭,旋于卅九年四月一日隻身遁離昆明沿滇緬公路西行,七日夜過滇西重鎮保山,兼程偷渡怒江惠通大橋,九日午正幸達南疆國門──畹町,未及用餐即步行越過中緬交界之小河而安抵緬北九谷鎮;歷經艱險,卒獲自由,深慶虎口餘生,爰拙成五言一闋誌後,藉以自省自勵。
我年二十許,渡江四月七;
揮淚別故土,報國跨海去。
(第一節完──六十二年元月二日寫于基隆)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四期;民國63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