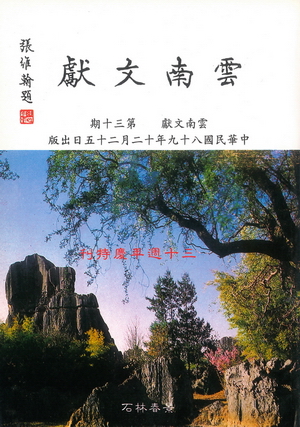西南絲道話唐碑
楊鵬
著名的西南絲道,是中西方人民共同開闢聯繫友誼的紐帶。通過絲道的密切交往,促進中西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形成絲路文化的多姿多采,多少年來,為眾多學者醉心探索的課題。
西南絲道,人們美稱為「絲道之路」。經西南(川、黔、滇)出國境,走向緬印的一條陸上國際交通線。她早於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率先走出國門,面向世界,創建了中華民族悠久文明的歷史豐碑而載入史冊。這是西南各族人民值得引以自豪和驕傲的。
翻開歷史,可以看到:從戰國末期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了第一個中央極權王朝,為了開發西南夷地區(今川、滇、黔及廣西部分疆域)便把目光投向西南道路(絲道)的開拓。
公元前三一六年,秦惠文王採用司馬錯的建議,「先滅蜀,後取巴」。設置了巴、蜀、漢中三郡,便開始築路以開發雲南。
公元前二五○年,秦孝文王委任李冰為蜀郡太守,繼續實施開發雲南的政策。由僰道(古僰侯國。蜀歸秦後改建的縣級政權,今宜賓市。)向南沿關河修築通往滇東北的道路。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全國,續派常頞修築由蜀入滇的道路,經朱堤(今昭通)至建寧(今曲靖),全長二千餘里。道寬五尺,史稱「五尺道」。她就是著名的西南絲綢之路主軸道。秦在沿線派遣官吏進行治理。對滇東北地區的農業發展、商貿往來、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漢滅秦後,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漢武帝派唐蒙為中郎將,通西南夷,設置犍為郡。唐蒙發巴、蜀萬餘人治道,自僰道指牂牁(北盤江)。《水經注》載:「唐蒙……乃鑿山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史稱「南夷道」。在修道期間,建朱堤(今昭通)、堂狼(今巧家)、郁鄢(今宣威)、漢陽(今威寧)、南廣(今鹽津)等縣,屬犍為郡遙領。與此同時,採取「募豪民,田南夷」的措施。歲月悠悠,歷史的發展,証明了漢武帝所實行的開拓政策,是以通路、置縣、遣吏、移民這一系列的和平手段來實現其統治的。難怪史學家贊美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是他進一步地使中原文化溶入西南民族文化而促進西南的進步與文明。
元朔三年(前一二○年),漢武帝遣漢中張騫出使西域,了解到西域各國的民情民俗,言其在大夏(今阿富汗)時,見市上有邛竹杖、蜀布。詢知大夏人說:「吾賈人往市之身毒(今印度)」。漢武帝聽後,亟欲遂其「威德遍於四海」的雄心。乃令「出馳、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道……始通滇國」。這是一條在民間早已形成的中外交通線上而開通的官道。其在蜀境內稱「西夷道」,入滇後,連接古博南道出境,通往緬、印東南亞各國,時稱「蜀身毒道」。她和「五尺道」、「南夷道」兩條幹道經滇池至大理(古葉榆)合路西行,直接進入緬、印、暹羅(今泰國)、越南各國。通過絲綢、琉璃、黃金、寶石和其它生產資料、生活用品的交易,展現出南方絲綢古道的風貌。出現了「內和諸夷」「威德及於四海」的民族和睦、中外文化及經濟溝通新局面。
幾年前雲南廣播電視台專題拍攝出一部南方絲路的影片在全國播放;一九九八年,川滇黔十一地州市聯合編輯出版了一部《今古生輝南絲路》,生動形象,求真務實地記載了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過去和今天。兩千多年來,西南各族人民,生活在偉大祖國的大家庭中,開創和發展為今古生輝的絲綢文化區域。今天,在中央西部大閒發的偉大戰略決策指引下,西南各族人民有決心、有信心把正在突飛猛進的雲南,帶入新世紀,向著現代化的目標邁進!
不可否認,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西南絲道上不知發生過多少次關係國家統一的大事。屹立在今噸津豆沙關石壁上的一塊唐碑│也稱《唐袁滋摩崖石刻》,就鐫刻著七世紀時期的南詔地方政權,在嚐夠戰爭的苦難後,從民族利益出發,從分裂走向統一,向唐王朝輸誠歸順,受到冊封的歷史文物見証。碑文共」二二字,直式,左行七行楷書,第八行篆書「袁滋題」三字。文曰:
「大唐貞元十年,九月廿日,雲南宣慰使內給事俱文珍,判官劉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節冊南詔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尹龐願,判官監察御史崔佐時,同奉恩命赴雲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其時,節度使尚書右僕射成都尹御史大夫韋臬,差巡官監察御史馬益,統行營兵馬開路置驛,故刊石記之。袁滋題。」
以袁滋為首的欽差大臣們持節前往大理冊封異牟尋為南詔,來到這「途經五尺險」的豆沙關,也許想到了肩負國家重任,不知前面還有幾多艱難險阻,才能不辱君命呢?所幸有劍南節度使麾下的行營兵馬「開道置驛」,今天總算進入了南詔領地。於是,精神為之一振,便揮毫寫下了這一塊標志「和平」的碑記。不想竟成了千古美談的歷史見証。
「以史為境,可以知興替」。南詔是怎樣從戰爭走向和平、從分裂走向統一的呢?
唐開元廿六年(公元七三八年),皮羅閣統一南詔,破吐蕃,以功受唐王朝封為雲南王。天寶九年(公元七五○年),閣樓鳳妻往成都,途經姚安,雲南太守張虔陀公然侮辱其妻,兼之平日一貫欺壓南詔,因而被迫反唐,爆發了天寶戰爭。閣邏鳳遂附吐蕃,受封「贊普鐘南國大詔」。形成了地方政權與中央政權猶如水火的對立局面,長達四十餘年之久。
到了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異牟尋繼承南詔王位,他以遠大的胸懷,拋棄前嫌,立圖改善與唐王朝的關係,派遣求和使者,三道並出,到達成都,向劍南節度使韋臬獻上文書,並賚生金丹砂(生金表示堅定、丹砂表示赤心)表示歸唐誠意。經過輾轉上奏朝廷,受到唐德宗皇帝的嘉勉。
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唐德宗下旨派遣御史中丞袁滋為持節冊南詔使,率領一班使臣沿著南絲古道向著大理城緩緩前進。那時的古道,當然沒有今天的高速公路好走,沿途的艱苦自不必說,但所經城鎮,必然受到文武百官和各族人民的熱烈歡迎,一直到達羊苴咩(大理)城,會盟於點倉神祠。約定保持和好,臣屬唐王朝。並隆重地舉行了持節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的儀式,頒賜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時為貞元十年,十月廿七日。至此,結束了天寶戰爭以來南詔與唐廷對抗四十餘年的不幸局面,雲南又統一在多民族的祖國大家庭中。
南詔歸唐,以國家統一、民族和好、文化勃興、經濟發展為標誌的《唐碑》,是雲南發展史上的一樁重要里程碑。千餘年來,受到史學界和廣大愛國人士的珍視。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國務院正式宣布列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異牟尋是雲南歷史上的一位夷族首領,他沒有受過什麼高等教育,而能作為一個炎皇子孫,胸懷大度,不訓較前輩帶來戰爭的恩怨,真誠地以民族利益為重,毅然率眾歸唐,成為奠定國家統一的大功臣、大英雄。千百年來,受到世人的景仰,真可謂留芳千古矣!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0期;民國89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