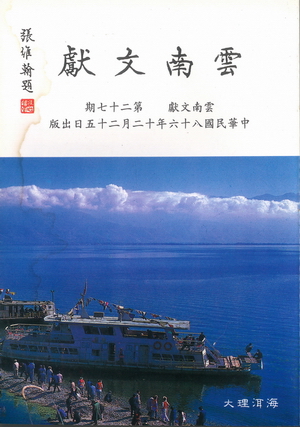慟慈母
(民國八十四年農曆八月十六日)
作者/李達人
人生永難忘懷的是父母,乃天性人性。蓋嬰孩離母體後,在母懷吮吸母乳時,睜眼看到的是母親的面孔。此時母親已自然的忘卻十月懷胎的辛勞苦痛,頓生心愛的喜悅;更從茲對之乳哺、撫養、教導、希望等意念,激盪在整個的腦裡,也掙扎在辛勤勞苦之中。
達人於民國前一年辛亥,陰曆八月十六日生,以干支作記,今日已過一甲子又二輪生肖,是我走過了八十四歲的路程,隨著時輪的轉動,明日要走八十五歲的道路了。吁!年歲愈長,思親愈切;當幼壯時,有事業前途的期望,職務責任的羈糜,對親情的思念,並不時刻在心;退役後,事無專責,空餘時間較多,母親的身影行動,常常填充腦際。猶自今年二月來,患心肌梗塞,初自誤為感冒而延遲就醫,已臨死亡邊緣,醫囑家人速詢身後事。余妻延璧及遠兒在床側,雖燕兒鴒兒遠在紐約,余均能對全體略有囑咐交代,並囑身後行宗教儀式,火化暫寄骨塔,若中國不能統一,視環境拋棄亦可。說至此,精神恍惚,昏沉不知若干時後,開眼見遠兒及媳偉珍穿醫院特備衣服在床側,病室僅容余一床,聞室外聲音:「時間已到,請家屬離開。」又昏沉睡去,醒來,見居住紐約兩女燕兒鴒兒及數位親友在病室;余已知前在加護病房,今在一般病房。主治醫師謂:「狀況之佳,超出預料,數日後即可出院。」探視者離開後,又浮動著母親的身影:母親未讀詩書,但對事理的見解處置,比飽讀詩書者通明允當。其對人對事,懷一顆忍讓誠厚的心,好處讓給人,自己吃虧受損,僅報以一笑。她關愛藏於心,不出於口,常關懷、濟助別人;有困難的鄰居,常向母親告貸生活必需品,如食米、麵粉或少量金錢,母親必不讓其失望而去。彼等也知我家非富有,僅稍寬裕而已;若告貸多了,必無力無助。母親也絕不以小恩小惠博人好感,全以一片善意濟人之急!看到對方真實窘困情況,不待對方開口,便自動使對方滿意。貸後並不望還,一年半載對方償還時,僅說「我把這事早忘了,你還記心上。」
母親對我們姐弟妹等,除照顧溫飽外,也極重教育。在封閉的鄉村社會,一個未曾讀過書的婦道,對子女教與灑掃、應對、進退、待人接物外,還要子女讀書識字,向上發展,是不多見的。當我們幼小時,農村女孩,還沒有進學校念書的風氣,母親能背誦三字經、百家姓;因其能背誦,便能教大姐,並督導二弟背誦。時久,一些淺顯句子,也能瞭解其中涵意。二弟宗雷,同我在一個學校受教,資不如我,母親便把希望寄託於我;我報考中學,以及爾後隻身徒步數百里,到省會昆明投考軍事學校,都是母親全力支助承擔的。當我讀中學時,未曾事先稟明父親,父親責我不知孝順!便不准註冊。經母親多方說服,我才得以入校。中學畢業後,我準備到昆明投考軍事學校,父親堅主我在家鄉教小學或習中醫。母親則主張隨我志向,對父親說:「我家有三個男孩,老二欠聰明,沒多大出息,老三還小,看不出能力如何;女兒又不能讀書求出頭機會,且遲早是人家的媳婦;將來能有點成就,為我們李家爭點面子的,祇有老大達人了。並且男兒志在四方,就讓他闖一闖吧!」固然,父母各有其希望與主張,父親則堅持其意,母親則暗對我說:「你放心,我會資助你的,你離家後,那時木已成舟,你父的堅持還有何用!」母親為我暗籌旅費,值父親為全鄉爭取水利涉訟,去大姚處理,我便得順利離家到昆明進了軍事學校。這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從此,與母幾成永別。
民國二十三年底,軍事學校畢業後,即在軍中任隊職官,追剿由江西突圍的共軍,清剿華寧、彌勒、開遠間土匪,在湘、鄂、贛血戰日軍。二十八年,由第九戰區轉滇黔戰區任職。在整整九年中,雖時思家中一切,然也僅以家書報平安以慰父母,反少問候語句,此乃自幼受母親愛不出口的誠厚性格影響吧。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奉命查辦祿豐、廣通、鹽興、牟定、姚安、大姚、鹽豐、鎮南、楚雄九縣徵兵事,七月某日十二時,將牟定查辦清楚,下站為姚安。牟、姚間路線有二:一為官商公務往來正道,中經前場關,程途一百二十里;一為馬幫慣走之路,中經險阻崎嶇的白沙河,途程一百里,我急欲見到父母,故採此險道提前趕抵家中,僅見十一歲之么妹,彼不識余為其長兄而欲逐我離去。俄而父親由田莊回,相下之下,悲喜交集。詢母親情況,父云:「你母生命,正熟睡中,稍緩再去見她。」我急趨母榻,緊抱母身,未發二日而放聲大哭,母亦飲泣。父親說:「多年不見,有這難得機會,是件喜事,還哭甚麼?別孩子氣。」父親那知兒千言萬語,難吐一字的痛楚。知我回家的緊鄰齊來看我,數人幫忙弟媳做飯,菜餚雖豐,我憂母病,甚難下嚥。鄰人走後,我趨母榻陪伴,惟以離別過久,不能述說自身情況,更不敢問家中事務以繁母心;母親亦不詳述病況,僅說:「你放心,慢慢會好的。」我欲多陪一時,母親說:「你趕路太疲勞了,早點去睡吧!」我又何能安寢。
翌日,即趕至縣城,與縣長霍士廉、總務科長陳光州查詢徵兵情況,正談間,父親亦至。霍縣長說:「姚安應徵兵額已驗足,昨日起身趕赴昆明了;夜宿前場關,今日抵牟定。」父親說:「達人昨日自白沙河來,故未遇。」我說:「兵額已起身,姚安事務已結束,我明日即離姚;在徵驗中,所派徵員有否刁難情況?」陳科長將該徵員之刁難意圖未逞情況詳述,我說:「你們不使其意圖得逞是救了他,否則他的前途也完了。不過,我應發個電報給盧濬泉將軍。」返家,見姐丈王得基來,我與他談明晨起程赴鎮南事。是夜憂心母病,一夜未能合眼,早餐更難下嚥。六時半,縣府代僱之滑竿(便轎)及武裝護兵四人至,我欲將護兵遣返,姐丈說:「你離家數年,地方情況不明,縣長派兵護送,這是他的責任,不可遣返。」我急欲見母告別,父云:「你前天引你母傷感飲泣,昨夜陪她數小時,她現正熟睡未醒,且不知你要走,最好不要驚動她。」姐丈也如是主張,我傷心至極,淚涔涔下,面前一片模糊,兩腳不知所之的由姐丈與勤務兵杜朝旺將余扶上滑竿,他二人也跨上馬背,離開了家庭。
我此次查辦徵兵,十八天即結束六縣事,以時少事繁,留家短暫,尤其母病不能侍俸湯藥,傷心哀慟,淚珠常落難禁,姐丈多方安慰;也責我由牟定至姚安不經前場關而經白沙河實為不當。他說:「你是負有重要任務的,應顧慮安全完成任務;經前場關是正路,安全無問題,首先進城住下,再通知家中。你由白沙河,安全不無顧慮!且突然抵家,父親一切未備,有失他老人家的面子。你想急速見到親人,不顧安全任務,不覺得是因私忘公,輕重倒置嗎?我讀書不多,所說不無道理吧!」經姐丈指責,我真不明事理,重私情而輕責任。但事已成過去,惟默禱上蒼,佑我母早沾勿藥,速復健康。
查辦徵兵結束後,返昆訓練部隊三月,移防滇南蒙自新現。蓋因日寇於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佔我海南島,二十九年佔越南,進迫滇省,原為抗戰後方,今已變為前線,中央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昆明行營,部署防務,第一、第九兩集團軍嚴密防守滇南戰區。
三十三年七月,父親千里迢迢,蒞新現防地,父子不見,又已四整年。在此抗日戰爭中,日夕置身戰壕營壘,為國忘家、忘親、忘身者,豈我一人!慟念我二十九年最後離母親時,父阻我勿驚動熟睡中的母親,免生離別痛楚;惟繫念皆自好處,認為母親必早已康復。請父示以情況,父云:「你母於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病故,因你身在敵對的前線,軍情緊急,而距家千數百里,想你很難如期奔喪,也為你母早日入土為安,所以就沒有通知你了。」聞語震驚心肺,哀慟至極,暈眩無語,淚珠奪眶而出,妻廷璧將懷中遠兒置我膝上,以安我情緒,並免勾起父親傷感。並云:「在這抗日戰爭中,軍民無辜傷亡難以勝數,母親西歸,也不必過分哀傷,我們身在前線,也衹有節哀順便了。」母親是光緒十二年(民國前二十五年)二月生,享年僅五十六歲,何竟撒手人寰。
抗戰勝利後,大局逆轉,清算鬥爭,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冤死慘死,數逾萬億。民國七十年到美探女,與大陸取得連絡,得知三弟正昌被迫投井身亡,父親冤逝監牢之慘禍!母親早日因病不起,免遭爾後之慘烈毒害,是其平日量力助人,誠厚忍讓之心感動上蒼,接引其早日西歸耶!然而為人子者,病不能侍奉湯藥,歿不能殯殮送葬,子道全虧,又豈終身遺憾一語,能代罪愆萬萬乎!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7期;民國86年12月25日出版】